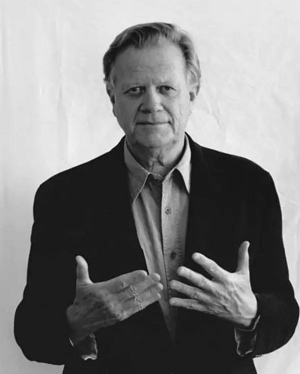|
编号:S29·2210207·1734 |
| 作者:吕德安 著 | |
|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 |
| 版本:2020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68.00元当当34.00元 | |
| ISBN:9787521712162 | |
| 页数:416页 |
于坚说他“具有明确的风格和石头一样沉重的文本的诗人”,韩东认为他是一个“向后寻找理想的人”,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把“年度诗人”的桂冠给他,并称他是“中国的弗罗斯特”。吕德安身上贴着“理想主义”的标签:他深居简出,如一位隐士;他的诗淳朴自然,始终亲近土地;除此之外、他还画画、在家乡山里筑居,过着隐逸的古人般的日子。从纽约回国后,吕德安返回老家的山上筑居。“有一次在山里,与石匠们一起撬石头,想用来铺台阶,石头赖着不动,因而偶得一句:一块石头,当你搬动它,它就成了顽石——这是在一次角力中蹦出的,没有道理可言,只能心领神会。诗可以与我们的知行有着天然内在的契合。”吕德安如是说。“有谁像我这样躺卧在天空下,起伏着,像尘土。”《傍晚降雨》收录了吕德安从1979到2019四十年间的诗作,按创作年代分为四辑,另收录其长诗若干结为一辑,这是吕德安唯一一部较完整的诗集。
《傍晚降雨》:山顶上石头在繁殖
然而我们得从头开始
那是草,那是石头
那是天空
——《除草》
草上面是石头,石头上面是天空,或者,天空下面是石头,石头下面是草。空间的不同顺序,并不意指向上仰视或向下俯视的态度,草不是柔弱,石头不是静止,天空也不是空阔——在去除了一切的象征和隐喻之后,草就是草,石头就是石头,天空就是天空,“让我们回到/简单又简单的/事物中”,然后,“我们得从头开始”,而且就从草开始——它生长于此,就像“我来了”。
一切回到“简单又简单”,一切从头开始,因为父亲死了。这是吕德安写于1990年的诗歌,从头开始,就是从草开始,从“我来了”的生命开始,而这种开始意味着一个简单的动作:除草——草下面是土,土里埋着父亲。从自己的生回到父亲的死,吕德安寻找着生命的某种轨迹,而关于父亲死亡的1990年,在吕德安的诗歌履历中一定占据着重要成分,除了“悼父亲”的《除草》之外,还有《回忆》:半躺着看见镜子里站着一个女人,高过镜子一倍的她露出“腰,和一半的乳房”,从未显露全部的她是美的,“如果她低下身看自己/乌亮的头发,悄无声息地再看看我//我就会死亡,或起身叹息/像先人留在坟墓里的/一把梳子”;还有《致母亲》:我带回了父亲生前最爱读的《红楼梦》,于是想起了父亲患病倒下的那一幕,“现在读来,才知道那是他/晚年的催眠术。坚持了很久/直到一天晨跑回家/突然心脏不适,躺倒在/床上,甚至来不及把目光/从天花板移开/回到昨天那一页”,而现在回来,我劝母亲搬出那房间,以为“那是面对现实的/一个法宝”,但是发现母亲在变小,但是却“像瓶子中的瓶子/又无限可能地大”,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变小,却又无限可能地大,那是因为“你在父亲灵魂里的灵魂/一时间很难走出来”,再次回来,“看见你堆着杂物,表情平静”,于是在感谢琐屑的生活的同时,“目光投向你膝旁/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移开”。
镜子里女人的美,反衬着我如留在坟墓里一把梳子的叹息,堆着杂物表情平静的母亲,依旧吸引着我不能移开的目光,一种是我的“死亡”,一种是母亲的平静,它们在1990年的诗歌意象中,构成的是对于父亲的怀念,而我也像母亲一样在变小,却也是在父亲灵魂里的灵魂中,一时难以走出来。而这种难以走出的感情更强烈地表现在《那是他还小》这首诗里:“一个孩子那么小,小到起皱/小到可以放进口袋里/小到可以是每一个父亲/头顶上的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母亲腋下的每一个孩子”,甚至小的不需要回到“关于生死的问题”,无知的小,固执的小,当现在回忆起来,那些小,那个小小的孩子,“他曾经是我”。小小的孩子,小小的无知,小小的固执,小小的原谅,“他曾经是我”的指认和回归中,当然是放大了对父亲和母亲的感情。这首最初写于1989年的诗歌,吕德安一直修改到2020年,曾经的旧作一直在时间里呈现出最新鲜的温度,最浓烈的感情,横跨三十一年,这是如何一种不愿走出来的“小小”?这又是如何强烈地想要“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草是草,石头是石头,天空是天空,而这者仿佛就构成了吕德安关于生命、亲情、诗歌的永恒意象。回到开头,是1979年至1983年的《纸蛇》,第一辑第一首收录的诗歌便是1979年的《澳角的夜和女人》,这是一个偏僻的渔村,这是一个渔村的夜,这是夜的安宁,“澳角,这个小小的夜已不再啼哭,/一切都在幸福中做浪沫的微笑,/这是最美梦的时刻”,连女人也不再推着身边的男人说:“要出海了。”闪耀着美梦时刻的澳角,是吕德安的故乡,第一首诗歌也成为他开头的地方,成为他出发的起点。在《纸蛇》构筑的世界里,有轻声细语的母亲,爱流泪的母亲,为一只蚊子而发怒的母亲,当然也是用扇子说话的母亲;有是郊外镇上小小税务官的父亲,吩咐母亲照菜谱做菜的父亲,把一个家庭说成是一个国家的父亲,最后是躺在病床上“像火山一样动弹不得”的父亲;有孤独的女邻居,有爬下楼梯的农夫,有早早回家的姑娘,当然,镇上也总是有雨。
但是澳角这个靠海的渔村,注定铺展开一条向外的水路,注定会把人带向更远的地方,从这个起点出发,便是和我有关的漂泊:不是马是蛇一样的出发,“这是一条我生来没有见过的蛇/我们的小镇也没有见过/可是在雾蒙蒙的傍晚/它那金灿灿的自由的身体/多么像我漂泊的生涯”,一方面,我渴望像蛇一样在流浪中成为有福的人,它将“叙说一个流浪者的全部心事(《纸蛇》)”但是另一方面,蛇和迷失的月亮、游子一样,“祈求上岸”。向外和上岸,构筑了吕德安离开的两种状态,“新的一天开始了/马戏团对着静水装扮/一条献媚的鱼/跃上了岸(《马戏团小曲》”但毕竟是出发了,远道而来的是游唱诗人,写给父亲的信里说:“日子把我领进城市/虚度时光,一片茫茫/父亲啊,但愿你安详的双肩/攀绕的春藤永远枝叶茂密(《寄给父亲》)”,这是一种怀念更是向外的坚定,就像在《残疾的女邻居》里所说,“她还要长大,直到找到她的痛苦/而我一抬腿就能跨过篱笆”,而我一旦跨过篱笆,“兴许永远不再回来:消失在远方”。
跨过了篱笆,消失在远方,游吟诗人开始了“南方以北”的生活,对于吕德安来说,离开那个小渔村,离开小镇,离开父母,却并非是唯一的方向,它呈现出的是某种复数的状态。复数是“三个男孩”,一个带回了爱的苦恼和额头上的皱纹,一个手持杏花,“双脚不停地一块砖头上轮流站稳”,而最后一个去了海上,经历的是“一次永久性的疼痛”;复数是“三个女孩”,一个女孩消失了一半的脸,一个女孩退出了海洋,最后一个“仍悬在最简单的媒介上”;复数是“三个泥瓦匠”,“三个泥瓦匠会心地干着/两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那神气倒也像一年的活儿/叫他们一天时间就干完(《三个泥瓦匠》)”;复数是不同的诗人,睡眠的诗人有一个睡眠的母亲和每一个幸福的夜晚,快乐的诗人听见有人劳动有人歌唱,谦恭的诗人回到家“日子像串串春藤爬满”,骄傲的诗人推辞掉了最后一餐,而逃亡的诗人无处不在,未来的诗人则胸前扎着花,“所有的真理都听从他”。虽然“三个男孩”还会一起手掌反转,三个女孩被我爱着,“仍然是一个整体”,但是已成为记忆成为过去,“村庄也已经在/炊烟中睡死/只吐出半个月亮”,剩下的我“穿过树林/带着黑暗的火焰/和睡眠的预感/很可能不再回“(《散步》)”
这是“南方以北”的漂泊,南方的雨“粗暴地干涉到我的生活”,很多人的名字“我已好久不用”,我像一只“在影子里生存”的蟋蟀,“我唱着,唱出那岁月的空洞/人世的转瞬间即过(《蟋蟀之王》”,于是1987年的《南方》在吕德安的眼中已经不再有曾经的童年,“大海无所不在/它有着疯子的掌力/它拍打岸边的房子/再把它灰尘一样从指间吹跑”。在这样一种境遇里,吕德安的诗歌中出现了“石头”,这不过它是沉默的,“沉默是否就是这样一种黑暗/在它的阴影下,我尝试着说话/或者,我终于能拾起那块石头/远远地扔出它的肩头(《沉默》)”,沉默在石头的后面,沉默就是石头本身,但是吕德安还是拾起来,还是扔出去,沉默会变成一种回响吗?1987年的石头,1987年的沉默,在吕德安看来,那拾起的动作,那扔出的欲望,构成了他诗歌生活的开始——在《后记》中,吕德安写道:“我写诗就像在沉默背后拾取石头,那么画画,就像我换一块石头,并将它扔向世界——或许还是扔向一个遮蔽着同样大的经验的世界。当然,我是认真的。”这一句话完全是《沉默》这首诗的变奏,他把画画看成是扔出石头的比喻,其实写诗也是从拾起到扔出的过程。对于吕德安来说,把沉默的石头拾起扔出,就是希望透过诗歌,“去应证某种朴素的写作,去抵达生活。”
|
|
| 吕德安:去爱一些不能爱的事物 |
他如何拾起石头,如何扔出石头,如何让沉默的石头抵达生活?1990至1998年的《纽约诗抄》,吕德安开启了更远的漂泊,穿过那片海抵达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抵达是《一月》中的在场,“从低沉的天空偶尔可以看见/鸟儿在努力飞高,双翅愈变愈小/但分辨得出,那是它在那里/一上一下地拍打,它在那里/游向更高处,它在那里飞过/并证实了你以为是云的,并不是云”,是《在另一个冬天》中感受到的自由,“一生的自由是什么,无非是/一场漂亮的雪。”是《时间之差》中水和大海的融合,“我决定把足够喝一杯/水的时间出让给大海/如果可能,我还可以一天/守候两场日出”。但是纽约是水泄不通的纽约,曼哈顿是孤独的曼哈顿,是被自己的黑暗完全笼罩的雪天,是不断让人想到流浪的“街头音乐”,于是吕德安在在场的纽约,在飞翔的鸟中对自己说:“鸟儿已飞过天空,我迟早/也得从这里离开。”为什么强烈地想要离开,在这个父亲已经去世的时间里,吕德安却总是想到父亲,“说来奇怪:/父亲只稍轻轻一站,你就立即现身”,想到自己和父亲一样‘总是先学会失去/然后才开始珍惜’。甚至在“继父”相关的生活中,想到了离城二十公里的荒山,荒山上的房子,院子里堆着的顽石,“不过在我的有关家庭的梦里/它倒更像一个石头遗址(《继父》”
现实中的继父,诗歌中的继父,和石头有关的继父,在纽约的漂泊和孤独中,吕德安想起这些,其实就是想起那个永远不变的存在:父亲,“每一首诗都应该有其形象,能令人联想到生活。而且,生活可以在别处,现实可以像一个继父,但诗从未变换过居所。”而父亲就是沉默的石头,坚硬的石头,顽固的石头,以及拾起扔出抵达生活的石头。吕德安在父亲和石头之间建立了关系,而这种关系更是变成了“应证某种朴素的写作”的诗歌:父亲-石头-诗歌连接在一起,它的上面是天空,它的下面是草,天空和大地之间的存在,是吕德安“从未变换过居所”的诗意世界,而这个诗意世界却又不是静止的:天使的翅膀熔化之后,“滴落在乱石堆中”,于是听见了“山顶上石头在繁殖”,它在变化,在歌唱,在祈祷,最后终于变成了一种滚动的动作,爆发出力量,让世界开始解冻。
写于1992年的《解冻》是纪念古城是一首诗,但是在吕德安看来,他不是在评判着他的死,而是回忆其他们关于石头的对话,“未自杀之前,他在岛上亲自动手建造了一所房子。盖这所房子的过程中,他聊到一个细节,一块巨石从山上向房子滚了过来。这个细节,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我跟伙伴们从山顶往山下滚石头的情景,后来触动我写下了《解冻》这首诗。”一块石头呆在山上被认为不会滚下来,这是谎言,春天,它慢慢移动,它向那些蜥蜴发出咒语,它带着斑斑点点的光和残雪开始呼叫,它甚至在滚下来是会碎成两半,但是,这是石头的生活,在上顶上繁殖的石头需要带来更多生命的气息,带来更多诗歌的力量,“它们只是滚动着。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一会儿在我们的梦中/在我们的上面画着眼睛的屋顶——/而正是这些,我们才得知山坡/正在解冻,并避免了一场灾难(《解冻》”
顶上的石头在繁殖,山上的石头滚下来,繁殖和滚动,都构成了一种非静止的生命状态,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石头回到了开始的部分,它是被建造的房子,它是存放记忆的家,它是诗歌抵达生活的证明,它当然也是“父亲”一般从未变过居所的坚定。石头是可以被举起的石头,“我曾经渴望放弃/手臂却依旧高举沉重的石头”,在石头中展开的劳动让自己成为一个农民,“我劳动的肌腿在臂膊上闪耀(《台阶》)”;石头区分了留下和离开,“也许那时候我们也像石头/一些人留下,另一些继续向前/那留下的成了心灵的禁忌/那消失的却坚定了生活的信念(《冒犯》)”;石头会跳舞,“啊,原原本本的一堆乱石/我想先挑出一块,不论它/是圆是缺,或是高兴或是孤独/我们真心真意,它就会手舞足蹈(《晨曲》)”;享用石头就是享用写作,“我写作,/键盘的声音伴着垒石升高,/我说的也正是脱口而出的。(《无题》)”石头在迁徙,石头在滚落,石头堆成一堆,石头一块压着一块,石头制造影子,石头也导引方向,每一块石头都从顽固、坚硬和沉默中诞生新的自己。
石头的意象连接着父亲和房子,其实连接着生和死,是从父亲身上体会“从未变换过居所”的永恒,是从“除草”的死亡而回到开头时看见了生命的本质。“我甚至也喜欢那乱石累累/好似在大自然的荒芜里/存在着一个父亲,依旧和蔼可亲/而我必须听从这样一个死者”,三十年前的父亲从裤袋里摸出一把钞票,告诉我不要去偷去抢,要学会成家立业,后来远走他乡,后来奔波各地,后来便开始盖起自己的房子,“耸立在山岩上,让你一边盖/一边想,却很少去想过孤独(《草坪》)”现在也总是下雨,“傍晚下雨”,雨落在石头上,下在山谷间,“当我疯子似的跑进雨幕/脚踩着滚烫的石头,发现自己竟如此/原始和容易受惊,几乎身不由己(《傍晚下雨》)”而这雨正是生命的象征,“雨依然是雨/雨的确切存在创造了三月//而三月是我的出生月(《曼凯托》)”。
草在生长,草是蓬勃的生命,它用石头的滚动证明生命的力量,草的下面是泥土,是埋葬了父亲的地方,它也是从未变换过的居所,在生和死之间,在雨和石头之间,在父亲和我之间,拾起又扔出去总是回带来回响,它是诗歌,是生活,是生存,是记忆,是爱,是心灵的信仰:
它引导我们不得不穷尽一生
去爱一些不能爱的事物
去属于它们,然后才去属于自已
——《可爱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