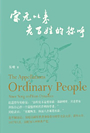|
编号:Z21·2200521·1654 |
| 作者:【法】罗曼·罗兰 著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版本:2018年07月第1版 |
| 定价:22.00元当当10.80元 |
| ISBN:9787020131266 |
| 页数:305页 |
《名人传》是罗曼·罗兰为三位举世闻名的文学艺术大师谱写的英雄史诗:第一位是身患残疾,孤独贫困,从未享受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的作曲家贝多芬;第二位是生于忧患,受尽磨难,给人类留下不朽艺术品的雕塑绘画大师米开朗琪罗;第三位是不肯安于富贵,愿为天下黎民献身的俄罗斯小说家托尔斯泰。较之常人,社会和自然并未给予伟人们更多惠顾,生活对他们而言往往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凭着坚强的毅力,他们勇于承受磨难,勇于挑战困难,终于攀登上生命的高峰,“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他们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历经苦难与颠踬,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路历程,从而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阕“英雄交响曲”。罗曼·罗兰试图通过伟人们的故事,向读者传送英雄的气息,鼓起人们对生活的信念和自强不息的勇气,努力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名人传》: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贝多芬传》
他经历了凄惨的童年,他遭受耳聋的酷刑,他神圣的爱情被破灭,他被众人所隔绝……种种之种种的困苦和磨难,对于贝多芬来说,或者可以称之为多舛的命运,但是他却用艺术,用音乐创造了另一个属于自己,属于人类的新世界,“牺牲,永远把一切人生底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当艺术成为上帝,创造艺术的人也变成了脱离于众人的神,“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艺术是高于一切的上帝,自己是为人类酿造醇醪的酒神,这是一种超脱,但是对于贝多芬来说,何以能完成这样的超脱?童年时,母亲因为肺病而死,没有享受过家庭温情的他对于人生的注解便是痛楚和犹豫,虽然并没有染上和母亲相同的病症,但是他却遭受了耳聋的酷刑,最后几乎已经没有了听力。虽然艰苦的童年和残酷的病魔,造成了贝多芬忧郁的性格,但是在一七九六年的时候,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廿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二十五岁他发现了自己身上具有的天才特性,即使从这一年开始,耳朵的疾病开始折磨他,但是他也从此开始了和命运的挑战,“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其实是一种矛盾,挑战却隐忍,隐忍却逃避,而对于贝多芬来说,肉体痛苦之外,还有精神的折磨。他曾经爱着自己的故乡,他把莱茵河兰城市“庄严的父亲”,不仅“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河边的故乡篷恩,在贝多芬看来,是“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存在:“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故乡的河流给了他一种生命的动力,“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而大革命正在爆发,对于贝多芬来说更是改变现实的力量。但是他的神圣爱情破灭了,美好岁月消失了,当贝多芬独自一人在维也纳,太残酷的“现在”成为他无法躲避的现实;即使他在一八〇六年和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订了婚,后来的婚约还是毁了,即使没有结婚的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医生都没有忘却这段爱情,但是他还是走到了绝望的边缘;而在社会事务中,一八一四年的维也纳会议中,亲王们向他致敬,他被人追逐,但是当这些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贝多芬成了他们口中迂腐的人,他的朋友和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最后,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
隐忍和逃避,他开始活在所谓的纯纯自然中,他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丹兰士·勃仑斯维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自然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而生活。但是这些都无法解答贝多芬关于命运的难题,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最终这样一种渴望转变成了艺术的力量:在痛苦的生命里,他创作了《月光曲》、《第二交响乐》、《克莱采朔拿大》,在病魔的折磨中,他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即使被社会所隔离,他内心的艺术之火仍在燃烧,他讴歌欢乐,他书写伟大,他战胜平庸,他挑战命运——对于贝多芬来说,用艺术抗击的不仅仅是自我的命运,更是人类的命运,用音乐书写的不仅仅是单一的作品,而是人类的作品,“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
这一种站在人类之上的创造力,就是对于爱和真理的探求,就是对于自由的渴望,他在一七九二年的手册中就高喊:“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尽管从个体意义上来说,他在童年就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他的回忆里充满了凄凉的感觉;他失去的爱情一半是因为自己暴烈的性格,“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他和人的不和也也因为自己憎恨人类的性侵,可以说,贝多芬不是完美的,当然更是不幸的,但是当罗曼·罗兰将他定义为“巨人”,将他看成是德国的象征,“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就是因为他超越了个体的命运,超越了自我的悲剧,“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底最英勇的力。”他用自己的痛苦换来了世界的欢乐,他用自己的苦难带来了人类的希望,“用痛苦换来的欢乐。”不仅仅是罗兰·罗兰对于贝多芬的评价,更是对贝多芬式的英雄所唱的赞歌。
罗曼·罗兰崇尚英雄主义,但是当他把目光聚集到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时候,他对于英雄主义的注解其实是多元的,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他对于英雄的定义是:“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的确,贝多芬曾经逃避,贝多芬性侵暴烈,贝多芬多疑,他不是靠思想和强力称雄的人,他扼住命运的咽喉也失去了很多,但是他用音乐打开了自己的心灵,也打开了人类的心灵,那是渴望自由而追求自由的心灵,那是挑战命运而主宰命运的心灵,那是抗拒平庸而战胜平庸的心灵——从个体到集体,再到人类,贝多芬用这样一种英雄主义命名了人的意义,就像他对朋友说的那样:“噢,人啊,你当自助!”
而对于米开朗基罗呢?在个体意义上,米开朗基罗当然也不是完人,他甚至就如他自己雕刻在弗洛伦莎国家美术馆中的“胜利者”白石雕像一样,是折了翅翼的胜利之神:他是自傲的人,“对于家族抱有宗教般的,古代的,几乎是野蛮的观念。他为它牺牲一切,而且要别人和他一样牺牲。”他不把自己看成是雕塑家米开朗基罗,而要让人们称他是“米开朗琪罗·鲍那洛蒂”,他的血液里有着对于家族血统天生的自傲;他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一种遗传病,让他被生活的痛苦所奴役,在博洛尼亚进行于勒二世的铜像创作时,他和三个助手睡在一张床上,睡觉时衣服不脱皮靴也不卸,当他的脚肿起来之后,只能割掉皮靴,而皮靴被脱下时脚皮也剥了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宿苦行为,用不惜的行动让自己打败悲观主义,成为天才,而这种苦役生活更突显了他的悲观主义;他天生喜欢猜忌,猜忌朋友,猜忌家族,猜忌兄弟,猜忌嗣子,“他猜疑他们不耐烦地等待他的死。”
他孤独,他也懦弱,在宿命中他看到自己的不幸,在孤独中感受着人生的悲剧,而对于这一切,他甚至只想到逃离,一五二七年佛罗伦萨爆发的革命让他陷入到漩涡里,“危险临到时,他的第一个动作是逃避,但经过一番磨难之后,他反而更要强制他的肉体与精神去忍受危险。”而当逃避无法解决自身的困境,他便想要彻底的离开,那就是死,“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己!逃出万物底桎梏!逃出自己的幻想!”他渴望死,因为在米开朗基罗看来,死是可怕的奴隶生活的终极,所以他讲起已死的人时真是多么艳羡!他品尝到了一切苦难,他目击故乡的沦陷,他悲悯于自由的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地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颗一颗地熄灭……这一切只能让他选择去死,罗曼·罗兰说:“他对于‘死’患着相思病,他热望终于能逃避‘生存与欲念底变化’‘时间底暴行’和‘必须与偶然的专制’。”八十二岁时,“多么想望而来得多么迟缓的死——”终于来了。
这样一个不是完人的个体,和贝多芬一样陷在自我命运的悲苦世界里,为什么也是英雄?罗曼·罗兰注解贝多芬身上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是“心灵的伟大”,而在米开朗基罗身上,发现的是一种爱:“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底真面目——并且爱世界。”在罗曼·罗兰看来,米开朗基罗是痛苦的代表,他的痛苦不是因为灾难,不是因为疾病,不是因为人类的恶意,而是蕴藏在人内心的痛苦,“因为人不能自己选择他的人生,人既不要求生,也不要求成为他所成为的样子。”正是因为米开朗基罗有着这样的不可选择性,所以在遭受了命运的苦痛中,他更容易深入内心发现爱的价值:他爱雕塑,认为雕塑是比绘画更能表现英雄的艺术,一四九五年的《耶稣死像》是他这种爱的艺术呈现:“永生了一般的年轻,死了的基督躺在圣母底膝上,似乎睡熟了。”当家庭的全部负担压在他一个人肩上的时候,他没有拒绝他们,他甚至可以把自己卖掉,只要能为家庭提供钱财;他为于勒二世的陵墓、圣彼得大教堂和西斯廷工程创作雕像,即使被放逐,米开朗基罗的内心里依然是对于艺术不灭的爱;他爱着加伐丽丽,几乎以崇拜的方式去除了自私和肉感,他爱着维多利亚·高龙那,他在她身上看见了圣洁的影子,“没有一颗灵魂比米开朗琪罗底更纯洁。没有一个人对于爱情底观念有那么虔敬。”他是从她们的爱上斫炼出崇高的思想;他也爱上帝,他的雕塑与其说是为了艺术不如说是为了信仰,他逝世的那一刻,遗嘱上说:“他的灵魂赠予上帝,他的肉体遗给尘土”,他要求“至少死后要回到”他的亲爱的佛罗伦萨,然后,他“从骇人的暴风雨中转入甘美平和的静寂”。
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苦痛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是怯懦的一生,也是充满爱的一生,在罗曼·罗兰看来,这正是英雄主义的最伟大意义,因为从来没有脱离现实的英雄,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英雄主义,它们是理想,却是英雄的谎言,只有像米开朗基罗那样,在战斗中征服,敢于正视自己的痛苦并尊敬痛苦,才能得到对欢乐的赞颂,“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痛苦和欢乐相伴,人和神合一,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无论是贝多芬还是米开朗基罗,他们都是用伟大的爱、伟大的心灵创造了伟大的英雄。
而托尔斯泰呢?这个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这个探寻人类命运的伟大灵魂,“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他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他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底心魂。”他身上的英雄主义到底是什么?罗曼·罗兰认为,“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艺术家底特征,在于他的生命底气息。”也是童年失怙,一种死亡的到来让他的“心魂中充满了绝望”;也是在孤独中寻找解脱的办法,从斯多葛主义到伊壁鸠鲁主义,从轮回之说到虚无主义,托尔斯泰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信仰,而十六岁他不再去教堂似乎对上帝本身也开始怀疑;他也有着不安和暴烈的性格,一八六〇当亲爱的哥哥尼古拉患肺病死去,托尔斯泰“摇动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甚至他开始唾弃艺术:“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他是孤独者,他的妻子在他进行创作中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底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但是在最后的隔阂中,他找不到解救的力量,在覆灭的痛苦中,他甚至无法把信心感染给最亲爱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儿女似乎都在他之外,他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
“他是弱者。他是人。”罗兰·罗兰如此写道,一个弱者何以具有英雄的伟大?因为他是人,“为了这,我们才爱他。”作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绝望的人,以及一个弱者,托尔斯泰在他的创作中实践着一个人的意义:《童年》让他在自然中得到神启,《哥萨克》让他唱出了青春的颂歌,《三个死者》中他看到了死亡的孤独,《战争与和平》中他书写了时代的史诗,“《战争与和平》一书底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底复活,民族移植与国家争战底追怀。”而《忏悔录》中,他自问绝望如何拯救?在这里那个大写的人似乎出现在他面前,“他把他当作何等人呢?当作是圣贤中最高的一个,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查洛斯德(琐罗亚斯德),依撒(以塞亚)——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圭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由此他开始探望生命的意义,追寻民族和国家的出路,《我们应当做什么?》他以英雄的逻辑面对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底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旋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底第一程。”而在《艺术论》中,他找到了“艺术宗教”的表达方式,“每个社会有一种对于人生底宗教观:这是整个社会都向往的一种幸福底理想。”从《民间故事与童话》《黑暗底力量》到《伊凡·伊列区之死》 《克莱采朔拿大》,托尔斯泰一直沿着这个理想前进,而《复活》则如书名一样,在托尔斯泰的内心世界里复活了一种神,复活了信仰,复活了人。
“唯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他的理智底逻辑,他的信仰底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当然,托尔斯泰选择的是离开别人而得到真理,他痛恨自由的幻想,他预言了社会的变革,他以艺术的方式成为“唯一的额上戴有金光的人”——“要长成一个森林必须要许多树;而托尔斯泰只是一个人。光荣的,但是孤独的。”他就是在这样的孤独而光荣的状态中,和悲剧宣战,用自己的生命力量,让爱深入真理。所以罗曼·罗兰将他定义为一个人,一个爱着人而已被人爱着的人,“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个,——‘我们的弟兄’。”当托尔斯泰成为我们的“弟兄”,那一种共鸣和契合也让罗曼·罗兰体会到了内心激荡着的英雄主义气息:
但为我们,单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作品中间,他的作品已成为我们的作品了。我们的,由于他热烈的生命,由于他的心底青春。我们的,由于他苦笑的幻灭,由于他毫无怜惜的明察,由于他与死底纠缠。我们的,由于他对于博爱与和平底梦想。我们的,由于他对于文明底谎骗,加以剧烈的攻击。且也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由于他的神秘主义。由于他具有大自然底气息,由于他对于无形的力底感觉,由于他对于无穷底眩惑。
托尔斯泰生活的是怎样一个时代?“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底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底叛变,屠杀,农村底暴动,似乎是‘世纪末’底征兆……”而对于罗曼·罗兰来说,托尔斯泰的这个世界无比接近自己的世界,接近“我们”的世界,“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所以在《托尔斯泰传》里,罗兰·罗兰再一次定义了英雄:“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
实际上,不管是“靠心灵而伟大”的贝多芬,还是“注视世界底真面目——并且爱世界”的米开朗基罗,或者是“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的托尔斯泰,英雄其实都指向一种精神:那就是“超乎一切个人的与普动的利害观念之性格”,那就是具有“人类必向统一之途迈进”的信念和实践,所以在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自身遭遇命运的不公时,都能用这样一种精神给人类带来力量和希望,而当罗兰·罗兰写作《名人传》,就是希望英雄能改变悲苦的现实,“一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英雄到来,力量和希望同在,伟大和爱同在,他们和我们同在,于是一九四二年三月翻译了此书的傅雷也成为了呼吸到了英雄气息的“我们”:“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