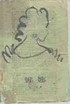 |
编号:C33·1950609·0131 |
| 作者:(法)左拉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5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6.60元 | |
| 页数:505页 |
《卢贡—马卡尔家族》第9卷,左拉体验生活的提炼。这位痴迷于“自然主义”理论的小说家,却把娜娜放进了一个充满堕落,呼唤良知的社会里,左拉最大的贡献在于继承了巴尔扎式对大环境的描写,这位如医生一样的作家把娜娜当成了另一个试验品,看着她如何逐渐被环境社会所泯灭,却永远无能为力,除了不尽的谴责与憧憬。这位哲学家的逻辑思想却已经相当成熟。
娜娜梦想有一张从来没有见过的床,那张床就是王座,就是神坛,叫整个巴黎都到这儿来崇拜她的至高无上的裸体。
———-第十三章
她是《金发爱神》里的爱神,她是小路易的母亲,而这种艺人或者慈母的定位对于娜娜来说完全是巴黎病态社会中的一个讽喻,她是“第一流的风流娘们儿”,她是抚爱别墅里的“女神”,她是公馆里的时髦女人,她是荡妇中的佼佼者,她是“一个驯良的畜生”,而对于巴黎第二帝国时代的一个符号,那张从没有见过的床上,陈列着她的肉体,而这种肉体既腐烂着那些跪拜在地上的男人,也腐烂着自己的脸庞,而最后天花无非是一个时代堕落和解体的隐喻,即使之前有过让巴黎翻滚的激情,有过对男人膜拜的报复,但最后也只是一种亵渎,至高无上的裸体深处是从来无法逃避的死亡。
“这一切让人一望而知她是一个过早就被她的第一个正经男人拋弃的姑娘,而后又落到一些下流的姘头手中;可以想象得出她初出茅庐十分困难,第一次下海就没有得到成功,因为她遇到了层层困难,既被人拒绝通融贷款,又被人威胁要驱逐出住房。”这是《金发爱神》第三幕肆无忌惮的裸体之后的现实背景,在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里她就是一个被抛弃、被拒绝的女人,《小酒馆》为她设置了悲剧的起点,作为绮尔维丝·马卡尔和白铁工古波的女儿,娜娜在六岁时,就“已经显得是个女无赖”;而到了十岁时,这“坏孩子竟像一个妇人一摇三摆地在他的跟前走路,并且斜眼瞅着他,眼光里充满了邪气”;十三岁到花店老板娘那里当学徒;“娜娜长大了……只十五岁便长得像一只小牛似的肥胖,皮肤十分洁白……嘴唇很红,两眼像两盏明灯,所有的男子都希望在她这盏明灯上点烟斗”……洁白的皮肤,肥胖的身材,对于娜娜来说,是堕落生活的开始,马车上她虽然穿着盛装,但是已经沦为了下等妓女,她的人生就如在下流歌剧《金发爱神》中的演出一样,难以阻挡堕落的肉欲:“这时候,舞台底部的云彩散开了,爱神出现了。以十八岁而论,娜娜长得十分高大和肥壮,她穿着一件女神的白内衣,金黄色的头发自然地披在肩膀上,她泰然自若地走向台口,向观众莞尔一笑。然后她开始唱起主题歌来。”
那白色内衣,那金黄头发,那莞尔一笑,以及那扯着破嗓子的唱歌,只不过是掩盖在肉体上的道具而已,当第三幕开始的时候,对于全场观众来说是战栗,是震撼:“原来娜娜是裸体的。她肆无忌惮,赤身裸体地出现在舞台上,对于自己肉体的无限魔力,有着十分把握。” 从海里诞生的是爱神,而娜娜除了头发以外,没有别的什么来遮盖身体,这是对宗教意义的神话的亵渎,而这种亵渎在娜娜那里只有肉体,只有欲念,只有狂热:“娜娜始终微笑着,可是她的微笑十分凶恶,仿佛要把男人吞下去。”
欲念的不可知大门打开了,弥漫在那些观众,那些男人身边的是“禽兽身上发出”的纯情,然后扩散,然后布满全场。而这小小的剧院里的一切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次纵欲演出,也是对于巴黎糜烂生活的见证,就像游艺剧院经理博尔德纳夫直言不讳地让别人不要叫剧院,“管它叫我的妓院”。从剧院到妓院,是默认,是自甘堕落,而巴黎无非是另一个更大的妓院。
在这个社会里,充斥着各种的交易,“从街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有一堆一堆的女人在进行这种肉的交易,她们直截了当地讨价还价,仿佛这里是一家妓院的露天走廊。”这是肉体的交易;“他的赛马马厩是巴黎最有名的,他耗费了难以想象的巨资去维持这个马厩;他在帝国俱乐部每月赌输的钱,总数令人震惊;他的情妇不管年成好坏,每年总要吃掉他一个农场,或者几顷地,或者一座森林,把他在庇卡底广阔的产业割去一部分。”在旺德夫尔这个名门望族的最后一代子孙建立起来的财富帝国里,充斥着各种和金钱有关的交易,无法抑制的花钱欲望将一切变成私有的统治力,而这种统治力对于巴黎社会的解构是赤裸裸的。而这种交易和解构看起来是男人的统治,是男人的挥霍,而实际上,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剧院经理、伯爵和侯爵,还是诉讼代理人,甚至是理发师,都在情欲的世界里被女人的肉体吞噬,而这具让男人走向亵渎、腐烂和死亡的肉体,便是娜娜,“她是荡妇中的佼佼者,她既目空一切又充满叛逆精神,象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女主人,把巴黎踩在脚下。”
《金发爱神》第三幕之后的娜娜住处,是拥挤的男人,“太太,我再也不愿意去开门了……楼梯上排了长队。”这是贴身女仆佐爱的抱怨,“老吝啬鬼”和“黑鬼”、情郎达盖内、德·舒阿尔侯爵、米法·德·伯维尔伯爵和银行家斯泰内先生,以及十七岁的孩子乔治,男人们用各种理由找到娜娜,他们有着金钱,有着权力,而一切的目的只为了娜娜,就如勒拉太太所说,“所有的男人在腿肚里都有魔鬼”,所以男人们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也就是带着自己的身体,带着魔鬼的欲望,所以在排队的盲从中,“午夜十二点,娜娜家。”成为男人们再次追逐的一个暗号,而三十八个人组成的强大宵夜队伍让夜晚充满了荒唐的味道,喝酒、争吵、赌博、将香槟倒进钢琴,而对于娜娜来说,她或许只是为了“不愿意人家瞧不起我”,但是在这种疯狂的追逐中,娜娜想到的是从前“既被人拒绝通融贷款,又被人威胁要驱逐出住房”的困境,而她正是可以利用男人手中的权力和金钱为自己打开摆脱困境的方法。所以在男人的世界里,娜娜是肉体的展示者,也是俯视男人的怪兽,她出卖自己的肉体,也获得了摆脱贫穷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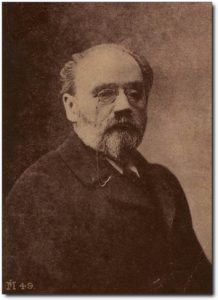 |
| 娜娜是左拉感官化世界里的一只金色怪兽 |
作为一个女人,娜娜从一开始是讨厌巴黎社会的,“面对着巴黎的这个哀伤的早晨,娜娜的心头突然涌上一股少女的感情,她突然向往乡村、田园,以及赏心悦目与洁白无瑕的东西。”所以银行家斯泰内为她购置的抚爱别墅就在巴黎之外,而其实这种向往更是一种逃避,对于乡村、田园以及洁白无暇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母性的表现,她有一个男孩小路易,这是她十六岁时生下的孩子,他不留在身边,只交给一个奶妈照管,而这个孩子对她来说是一种痛苦,作为生命的延续,她一方面要照顾她,另一方面也无时不刺激着父亲缺失的现实,当别人问“这孩子的爸爸是谁”的时候,娜娜的回答是“一个上等人”,上等人的虚拟性其实是娜娜希望摆脱自己作为妓女的身份属性,也在另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介入腐烂的生活,但是这种期望在肉欲的生活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讽刺,娜娜和男人的乱交生活中,竟然又一次怀孕:“她不断地感到惊异,因为她的性器官乱了套,原来是为别的目的而不是为怀孩子而用的器官,居然也能怀上孩子,这不是很奇怪吗?大自然的七颠八倒使她很恼火,她在享乐的时候,竟叫她当严肃的母亲,她把周围的男人一个个害死的时候,竟给她一个新的生命。”
娜娜身上的只不过是性器官,而乱了套的性器官又颠覆了仅仅作为性欲的功能,她或者又是一个母亲,而那个孩子也会像小路易一样成为父亲缺失的孩子,而那些父亲在娜娜日益膨胀的欲望面前,甚至连虚拟性的身份都不存在了,甚至成为她需要统治的对象,所以最后怀孕三个月小产是对生命的亵渎,更是对自身悲剧命运的一种预演,“把周围的男人一个个害死”,对于娜娜来说,男人的追求已经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去征服,主动将他们带入肉欲的陷阱,而她的目的是“象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女主人,把巴黎踩在脚下”。
在娜娜的征服的男人中,似乎只有乔治能激发她真正作为女人的感觉,那仿佛是巴黎之外的“乡村、田园,以及赏心悦目与洁白无瑕的东西”,十七岁的孩子使他的“宝宝”,“这以后的几天里,生活是愉快的。娜娜在小家伙的怀抱中,仿佛又回到十五岁的年纪。她早已习惯于男性的爱,而且已经感到厌倦,现在沉溺在童年的爱抚中,她的身上又重新开出了一朵爱情之花。”那些求爱的话她不当真,但是在童年的爱抚中,娜娜感受到的是某种难能可贵的纯真,是对于巴黎社会的颠覆,那里仿佛有广袤的原野,有芬芳馥郁的草,有房子和蔬菜,“一切都使得她神魂颠倒,弄得她竟认为自己离开巴黎已经有二十年了。”而这种逃避的生活状态,同样在与方堂的感情生活中被触动,蜜月的热恋,以及带着一万法郎远走高飞,像潜水或者逃亡,一点也不留痕迹,一方面这样的逃亡使她可以离开纠缠她的男人,另一方面一直在剧院里的方堂给她一种艺术般的享受:“在三个星期里,这一对恋人过着真正幸福的生活。娜娜仿佛又感到了当初她第一次穿上绸裙子时的那种无比快活。”
对于乔治的母性之爱,对于方堂的恋人之爱,在娜娜的生活中,似乎只是微弱的光芒,与乔治陷入的使他母亲对他的囚禁,而对于方堂,则是一次欺骗,不仅因为金钱发生的争吵时方堂打她巴掌,更有甚者,方堂也出去找女人,那个意大利剧院里的小演员就和方堂睡在一起,所以在娜娜的眼皮底下,这样的背叛也仅仅是对于娜娜自己的惩处,“第一次穿上绸裙子”时的快乐只是一个恶作剧,所以在娜娜心里萌生的是对于男人的报复,是情感的泯灭,对于她来说,肉体是她唯一的武器,是她让全世界腐烂的力量。
从逃跑到回来,对于娜娜来说,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她用金钱撵走了米尼翁的妻子罗丝,为自己获得了一个演公爵夫人的机会,虽然演出十分失败,但是娜娜的欲望从此不可收拾。她用米法伯爵的钱住进了公馆,这是她奢侈生活的开始,富丽堂皇的设备,家里服侍人员让她有了统治的感觉:“于是娜娜从此就变成了一个时髦妇女,专靠男人们的荒唐和:堕落来谋生的寄生虫,妓女中的花魁。她的崛起是突然的的和不可逆转的,她一跃而成了最有名望的风流女人,人人皆知的的最会挥霍金钱的入物,肆无忌惮地糟蹋东西的美人。”她的目的是统治,是糟蹋,男人和家具成为她王国里的臣民,在放纵的风流生活里成为男人们的女神,成为巴黎的女神。
而在这个计划里,米法伯爵无疑成了丢掉了信仰被肉欲侵占的男人,这个“一直都在奉行严格的教规,按照箴言和道德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伯爵甚至在老了的时候依然不知道肉欲的快乐,而娜娜启开了他被封闭的欲望,“她的笑声,她的乳房和她的屁股,都充满了罪恶。”朦胧中的魔鬼开始统治他,一开始米法伯爵是害怕的,甚至是奋起反抗,“使他想起他读到过的宗教书籍,使他回忆起他从儿童时就不断听到的魔鬼迷人的故事。”他虽然相信有魔鬼,但在罪恶的娜娜面前,他失去了抵抗,那化妆间后脖子上的一吻让他在性欲的冲动中滑入不可收拾的陷阱里:“青春活力终于在他的内心觉醒了,青少年时代的旺盛青春期,在他冷漠的天主教徒内心燃烧,在他庄重的中年人内心燃烧。”
燃烧的欲望不可遏制,甚至在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不轨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忠而无可奈何;甚至在他眼皮底下娜娜躺在另外的男人怀里,他也出于懦弱的需要和对生活的恐惧而继续着骗局。“他的肉体的欲望,他的灵魂的需要,已经混合起来,似乎从他的生命的模糊深处上升,在他的生命树上只开出一朵花朵。他任由爱情和信仰两种力量摆布,这两种力量建成的杠杆可以掀起全世界。无论他的理智怎样奋斗,娜娜的这间卧室永远能够使他疯狂,他只能在全能的性欲面前哆嗦着沉没,正如他在宽广天空的不可知面前昏迷一样。”在这样的肉欲面前,爱情也不是爱情,当然,信仰也绝非是信仰,他只是维持着身体的欲望,维持着对于生活的感官享受。而在娜娜的世界里,那些男人只不过是自己那张巴黎大床上的玩偶,是自己征服的一切,“她象一个驯良的畜生,生下来就不习惯穿衣,朋友要她的肉体她肯给,过路人要她的肉体她也肯给。”完全没有了所谓的爱,没有母性,“她在罪恶的领域里更加显得高大,她无耻地炫耀她的奢侈生活”,而这一切正如和米法伯爵的妻子不轨的福什里曾经写过的那篇文章一样,那只被命名的《金苍蝇》就是年轻妓女的写照:“她变成了自然界的一种力量,一种有破坏性的酵素,她自己虽然不自觉,但是她使巴黎在她两条雪白的大腿中间堕落,解体,她使巴黎翻腾,正如一些老大娘每月一次搅拌牛奶一样。”
她是荡妇,她是怪兽,她用一股意识不到的力量使世界腐烂,而对于娜娜来说,她的身体和欲望其实是被抽空了的,她对拉博德特说过:“我同他们干那事儿的时候,我一点乐趣也没有,真的没有丝毫乐趣。老实说,这只能叫我讨厌……”讨厌这样的社会?讨厌那些男人,还是讨厌自己无法摆脱的命运?所以那金色的怪兽是从贫民区的垃圾堆里飞起来,然后带着腐蚀社会的酵素,“落在这些男人身上,把这些男人一个个毒死了”。是的,死亡的悲剧在一幕幕的上演:旺德夫尔自焚;富卡尔蒙在中国海上过着凄凉岁月;斯泰内破产了,如今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拉·法卢瓦兹的痴想得到了满足;米法一家完全败落;乔治的白色尸体旁边,有昨天才出狱的菲利普坐着守灵……她的周围全是男人的灾祸,而“她独自一人站在她公馆的财宝中间,脚下躺着整整一代被击倒的男人”。
这是娜娜毁灭和死亡的工作,但是娜娜从来不是胜利者,她在失去灵魂的皈依之后,也失去了肉体的欲望,而最后的结局是自己无法逃脱的死亡。在经历了失踪和传闻之后,娜娜再次来到巴黎已经是一具腐烂的肉体,天花在她脸上开出丑陋的花,这是夺走她的孩子小路易生命的病症,没钱医治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表面的无奈,在刻着全裸体的美惠三女神雕塑面前,在豪华大饭店的凄凉里,在“进军柏林!进军柏林!进军柏林!”的街头口号声中,娜娜痛苦地死去,“啊!她的样子变了,她的样子变了,”最后一个留在屋子里罗丝·米尼翁说,而其实这种变化是腐烂,那激荡过肉体欲望,沾满了征服欲望的人生,最后也是腐烂:“看来好象她在阴沟和弃置路旁的腐烂尸体上所吸取的毒素,也就是她用来毒害了一大群人的酵素,现在已经升到她的脸庞上,把她的脸也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