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28 被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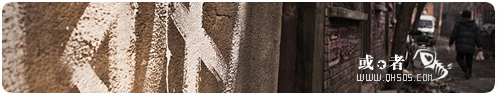
墙上一根钉子有什么可怕
可怕的是那
钉进去而且生锈的一半
——洛夫《绝句十三帖》
一个字,红色的字,写在墙上的字,被圈定的字,如此醒目,如此耀眼,在一个萧杀的季节里,不是被某种东西冷冷地覆盖,而是跳跃出来,变成关于村庄命运的最后注解。
两面墙上都写着“拆”字,甚至不是用手写上去的,而是涂抹着成为一种行为艺术,可以想象有人爬上废弃的砖石,搅拌了红漆的桶,用粗壮的笔画下这八画的字——尽管那重重的一点省略了,但是在斑驳的墙上,分明是一种不可省略的语气。但是,这似乎不是一种命令,不是一种强迫,反而变成了自愿,变成了渴望。
就是在村庄的路边,两层楼的房子还以固有的方式矗立着,可是人来人往,主人却早已搬走了,一处空房,在一个新春开始的纪年里,却以空廖的方式结束了居住的家的历史。据说是年前就提出了申请,然后进行了评估,最后是腾空了房子,没有了物品,没有了主人,空空荡荡中,只有一缕阳光很懒散地照射进来,仿佛无意中照见了被拆解的现实。这是村庄第一户被写上“拆”字的房子,而这也预示着作为一个起点,大规模的拆迁过程将在年后展开。
也是第一次在正月初一回到了村子里,对于我来说,“回家”不是一个迫切的词,而是呈现为一种浏览状态:从早几年就已经修好的通畅大路回来,从去年开学的大学校园经过,从挖掘机停止工作的二期工地穿过,从并未沉睡议论纷纷的村庄进入,我是一个过客,只是用一双眼睛打量它们,那些已经消失的和正在消失的,和最初的记忆一样,早已走进了历史深处。那些山,那些塘,那些田野,那些房子,像是和以前一样,但是在这沉寂的背后,却分明涌动着某种期盼:拆迁评估到底会有多少?悄悄地改变,总是在我预料之外,屋顶上加盖了棚子,外墙上涂上了涂料,墙壁上贴满墙纸,甚至敞开的庭院也都在覆盖和隔离中成为一间间屋子,在不停地添加中,早已透不出一丝的光。
本来村庄也是我浏览的一种景观,但那是“全景式”的小说,而现在,当一切都被改造之后,在新鲜而陌生的场景里,谁都渴望成为那个率先离开村庄的人。坐在火炉旁,大家激烈讨论着拆迁补偿标准,有人积极行动,有人等待和观望,但是,对于生活其中的人来说,对于未来改变的渴望超过了对于沉寂土地的坚守。几千人的大学将建设二期工程,山林都将变成生态农庄,在被各种项目包围的现实里,他们看起来像是被从土地上赶走的人。很多年前就在传说村子要被拆迁,但那时说话的时候,“拆”这个词带着明显的被动语态,带着明显的否定方式,甚至有一种保卫家园的味道,而在年复一年的传说之外,他们似乎更想成为喝头口水的人,都希望在获得拆迁款之后告别这一片土地。
沿着去年没有打通的路行走,那曾经是一片竹园,是一方山林,还有一个水库,而现在,在大型挖掘机、推土机面前,一切都不复存在,虽然泞泥的路还有着当初的影子,甚至还阻隔着最后的通衢,但是不远的一天,从东到西都将被连接,不再有断头路,那十多米的现代化道路会将整个村子都包裹在其中,然后一点一点吞噬,一点一点移除,最后会变成废墟。
还有炊烟袅袅,还有金鸡报晓,还有翠竹摇曳,却一定是最后的景致,它以残存的方式标注着村庄的最后命运,时间在不远处,故事就在眼前,当那个大大的红字,被圈定,被涂写,每一面墙上,似乎都会留下那“钉进去而且生锈的一半”,然后人去楼空,然后物是人非,然后变成最后的“绝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