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15 历史是什么玩意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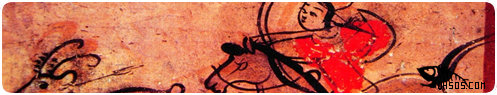
有两条消息,今日颇入耳目,一是历经16年编写的《中共党史》第二卷日前出版。据参与编撰的学者表示,这部党史记载了中共的历史错误,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该卷记载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8年12月中共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召开的历史。最重要的一点是,党史第二卷“实事求是地记载了中共失误”,包括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等,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做到“错误写透,评价公正”,等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该书的一句话是:“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第二则消息是,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而据作者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样的“良心和责任”体现在对列宁、对斯大林、对二战、对苏联革命的颠覆上,特别是对“十月革命”,提出了很多与之前相反的质疑:
- 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 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 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 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 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 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我们暂且把这本书的作者在释放“良心和责任”时包含着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愫,但是对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苏联,我们更能体会历史学家在共时性写作时的意识形态追求,因为1991年苏联解体时,我们还能记起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被掀倒,旁边的那个大牌子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
历史是不是应该原谅的?这一部《二十世纪俄国史》是不是就是客观反映了俄国的社会全貌?似乎必须回到那个起点:历史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历史是往事,往事首先必须依赖那些材料和笔记,但是再犯还原历史过程中,材料和笔记并不能等同于往事,当然更不会等同于历史。西方史学之祖希罗多德(Herodotus)于其《历史》(The History)一书中自称求真之谨慎:“我必须说出已经说过的(事),但我并不信其必真”。
汪荣祖在《论史学求真的疑惑与可能》中说:
常言道:史家著史必有所选择,而选择不免任意与主观。唯对训练有素的史家而言,选择乃汰芜存精、取精用宏。择其要亦是理性的判断,将重要的史事联而贯之,知其因果,并赋予意义,也是理性的作为,都有一定的客观性。不过,人事沧桑,沧海桑田,欲重现随风而逝的史事,无可避免要能用今日之语言叙述历史的变迁,古人非今人,古事亦不同于今事,如何设身处地,分享既往之意识与价值,重获完整的古人古事,即史家理性求真之道。
我们一直把历史作为一种学科进入教科书,但是其实对于过往的那些往事,我们都是在其外的“他者”,除去意识形态的控制,我们也是在历史之外的存在,而如《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的编者祖波夫,也只是用颠覆的观点覆盖另一种“他者”,宁可在《什么是历史》中也质疑了作为科学的历史:
历史学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认识史料,这是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是对认识了的史料作出理解和诠释,这里有对历史理性思想的思维,还要有体验能力,这是非科学和非理性的,需要有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的理解或精神贯穿其间,还要有史学家对人性的探微。这些本质上是思维构造过程,受到史学家个人思想的制约,因此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并非历史的本来面貌,而是史学家所企图传达给读者的那副面貌,然后再经读者去理解诠释,形成读者思想中的历史的面貌,这是历史学的最终结果。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478]
思前: 他说
顾后: 张枣:也许,我们会成为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