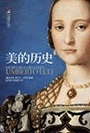 |
编号:Y92·2140120·1050 |
| 作者:【意】翁贝托·艾柯 著 | |
|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98.00元亚马逊71.10元 | |
| ISBN:9787020066698 | |
| 页数:440页 |
“美向来并非绝对、颠扑不破,而是随历史时期与国家之异而异,非仅身体之美如此,神,圣徒,观念之美亦然。” 美是和谐?美是魅力?美是平衡?美是节奏?从古希腊以降,直到今天,对于美的阐述一直没有停止,而作为艾柯第一本“有图为证”的著作,《美的历史》通过多层次布局,以主叙述带出源源不绝的绘画、雕刻作品,并长篇征引各时代的作家与哲学家,书前附上多页依时代顺序安排的图片对照表,使自古以来的对于“美”的观点之演变史一目了然。藉由本书,艾柯带我们一步步穿过许多历史时代,从古典以至当代,一路破除成见,打开新视角,来到今天的审美观:今天的审美世界是一个宽容、综纳百川的多神世界。《美的历史》是大师艾柯历时45年的巨献,已被译成28种语言,风靡全球。翁贝托·艾柯将美于时代洪流中抽丝剥茧,对美的发展历程做广博精辟的说明,广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呈现方式具独特的质感、美感,随处展现着美学大师的真知灼见,俨然一部不可多得的收藏宝典。
《美的历史》:神庙西侧的戴奥尼索斯
人发现自己丧失宇宙中心的地位,为之沮丧,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所怀和平、和谐世界的乌托邦憧憬亦趋式微。政治危机、经济革命、“铁的世纪”的战争、疾疫重返:诸事并发,使人更加惊觉宇宙并不是特别为人类量身打造的,人既非造物,亦非造物之主。
——第九章 从优雅到不安的美
并不是只有人类在丧失宇宙中心地位的时候,才会沮丧,宙斯在与忒拜公主塞墨勒私密幽会而现出雷神的原形时,那一场印证爱欲的大火也成为毁灭的象征,塞墨勒被宙斯的雷电烧死的时候,宙斯的心中是不是也有过类似沮丧的东西?只是他救出了不足月的婴儿狄俄尼索斯,把他缝在自己的大腿中,此种新生的救赎像是对宙斯的某种宽恕,但是那“宙斯的腐腿”含义的名字在象征新生的时候,也成为古希腊悲剧的起源。
狄俄尼索斯,在《美的历史》里译成戴奥尼索斯,作为酒神,他的像就刻在德尔斐神庙的西侧,那远离缪斯群像的西侧,远离阿波罗像的西侧,不受羁绊、破坏一切的混沌之神也在《美的历史》第55页的页码里。在这个克莱奥弗拉德斯画家的“红色人像双耳陶瓶”上,戴奥尼索斯手拿着葡萄,以一种祭祀的方式酿造着葡萄酒。他握有葡萄酒醉人的力量,也以布施欢乐与慈爱成为极有感召力的神,但是这样的力量、感召对于戴奥尼索斯来说,却是从出生开始就戴上了惩罚的魔咒,天生嫉妒的天后赫拉即使在戴奥尼索斯成年之后也没有放过,使他疯癫,使他流浪,所以在戴奥尼索斯成为酒神的历程中,实际上充满着悲剧,而这种悲剧对于太阳神阿波罗为代表的秩序与和谐来说,则是黑暗中的破坏力量。
阿波罗是德尔斐神庙的守护神,神庙的墙上刻着四条准则:至善即至美、遵守界限、毋骄傲、毋过度。这是希腊人审美意识的规则,也是宇宙和谐世界观的代表。而阿波罗与戴奥尼索斯,却在德尔斐神庙的两侧,他们以一种对立的方式表达着秩序与颠覆、和谐与破坏,甚至喜剧和悲剧的对立。这种并非巧合的对立是永远都在的“混沌扰乱和谐之美的可能性”,是希腊人审美观念中始终未曾解决的内在对立,“这些内在对立,希腊人的审美观念远比古典传统偏重的那种简化要更复杂,更具问题意识。”那么这种对立的问题意识包含哪些方面?
一是美的感官和感觉之间的对立,美有时候是感官的体验,有时候却是表象之外的感觉,赫拉克利特认为感官和感觉之间的间隔超过了艺术家弥合的努力,“世界的和谐之美其实是一种漫无秩序的流动。”第二种对立是声音与视像之间的对立,希腊人认为美的“可见的形式”正是阿波罗代表的能度量和数字次序表现的东西。而混沌和音乐却在阿波罗之美的黑暗面,也就“归为戴奥尼索斯领域”。而最后一种对立则是“远/近”,远是可听可看的美,是保持距离的美,而近则是可闻可触可嗅。三种对立,直到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才被放置在一起,才被纳入现代研究范畴。“我们伸手捕捉幻景的时候,大自然用你的幻觉达成它的目标”,人类的意志造就的美是一种艺术家的“胜利”,也即是阿波罗式的美,而戴奥尼索斯的美则是另一种悲剧的疾呼:“要像我这样!在没有止息的现象之流里,我是永恒创造力的原母,永远推向存在,永远在现在的变动不局里寻得满足。”所以阿波罗代表的是“静穆的和谐”:“在古希腊作‘秩序与节制’解,是一种美,尼采称之为阿波罗式的美。”但这种美也是一道障幕,用以掩盖一种破坏宁静的戴奥尼索斯式的美:“此美并无明显形式,而是超越表象。这是一种欢喜而危险的美,为理性之反,每每以着魔与疯狂见于描述。”
这是晴和雅典天空的阴暗面,这是神秘的启蒙仪式和晦暗的牺牲仪式,这是受和谐之美压抑之后的扰乱,这也是被当代人“频频汲用的一个幽秘又重要的美源”。这两种对立,两条道路构筑的美在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现代大众传媒时代,各自发展,又相互影响。而其实对于美来说,这种对立,这种互补就是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发展脉络,所以在《美的历史》的导论中说:“所以,我们必须花些工夫,看看不同的美的模式如何并于同一时期,以及其他模式如何穿越不同的时期彼此呼应。”这种不同模式,不同历史阶段的呼应正是为了寻找到美的意义,为了解答什么是美的本质问题。缪斯说:“唯有美的才受人爱,不美的,没有人爱。”美其实是一种爱,一种激发爱的心灵的感触,而这种爱在一定程度上是善,是超脱事物的一种态度,“美丽的事物,如果是我们的,会使我们快乐,但即使属于他人,也仍然美丽。”也就是说,美不美和占有不占有并没有必然关系,我们谈论美,是因为事物本身的缘故而享受它,而那种嗜欲、妒羡、占有欲、贪婪,都与美的情操了无关涉,所以美是一种独立状态,是一种享受的感觉,在那些绘画、雕刻和诗作面前,我们只是感受,只是享受,只是刺激我们的欲望。所以那系列的对照图中,我们感受的是美的发展变化,感受相距遥远的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如何重拾并发展(或许加以变化)纷繁多样的美的观念”,从公元前3万年威伦多夫的维纳斯,到1863马奈的奥休匹亚,再到1997莫妮卡·贝鲁奇的裸体,这是美丽的象征;从公元前6世纪的青年雕像,到1985年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电影《魔鬼司令》中的造型,这是力量的象征;从裸体的维纳斯到穿上衣服的维纳斯,再到维纳斯的脸与法;从裸体的阿多尼斯到穿上衣服的阿多尼斯,再到阿多尼斯的脸与发;从圣母、耶稣、君主和女王的形象演变,到各种比例有关的美的作品,这些纷繁多样的观念作品组成了“并非绝对、颠扑不破的”的美的历史。
但是,美并非是统一的意见集合,正像阿波罗和戴奥尼索斯的对立一样,美是一种观念的变化,正如色诺芬所讲的那样:“假使牛或马或狮子有手,能如人一般作画,假使禽兽画神,则马画之神将似马,牛画之神将似牛,神之状貌各如它们自己。”如果把古希腊作为美的历史的端点,他们的审美理想里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一切令人愉快,引起悦慕或吸引眼神的人或事物,皆谓之美。”即使海伦造成了特洛伊战争,她的无法抗拒的美也免除了她造成生灵涂炭的罪恶。而在这些缺乏真正的美学理论的古希腊,却开始了对于理想之美的探寻:肉体与灵魂圆谐的美,这是形态之美与灵魂之善的结合,也是最高的理想,而在颂神歌里,这样的理想之美逐渐使美具有了艺术特色:“在颂神歌里,美是宇宙的和谐;在诗,美是使人欢悦的魅力:在雕刻,美是作品成分的适当配置与平衡;在修辞,美是恰当的音节奏。”
和谐、欢愉、平衡、恰当,这些标签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最后变成了合比例的美:“美德是和谐、健康,一切美好的事,以及神性。因此,一切事物都是依照和谐而形成。”宇宙论、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美学结合在一起,成为毕达哥拉斯的贡献,而“美学/数学”宇宙观的诞生,则将“万物源于数学”的理论成型,四元体是完美的范例,奇数和偶数的对立体现着和谐,而“有限与无限、一与多、右与左、男与女、直与曲的对立”其实是导向一种“既善且美”的终点,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和谐其实是一种对立物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也逐步发展成为宇宙论,而在这万物之上却有一个共同的主宰,这个主宰是“神圣原理即灵魂、神意、命运”,所以到了中世纪,阿奎那说,美要存在的话,不但必须比例恰当,还必须完整,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必须具备属于它们才对的部分,残缺的身体因此是丑的,同时还要有光辉——“颜色清晰之物才是美的”。
从“上帝是一种弥满全宇宙的光流的光辉”的颜色之美,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宏大理论”,从风格主义的优雅美,到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之美,美其实都在这样一种和谐、秩序、规范中前行和演变,或者说这就是一种代表善的阿波罗式的美,但是正如德尔斐神庙的这种对立,阿波罗的背面永远是颠覆、破坏、着魔和疯狂的戴奥尼索斯,永远有着悲剧情怀的酒神,而美也在演变中走向了丑的一面。
康德说:“美的艺术,其优越性在于,它美丽地描写在自然里丑或令人不悦的东西。”美丽地描述丑的或不悦的东西,这是不是美的另一种阐释,这是艺术之美,“复仇女神、疾病、战争的蹂躏等等,虽是恶事,也能描述得非常美,甚至以图画表现。”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对于魔鬼的美丽再现,这便是“怪物之美”,“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些怪物。解法有二。一是将怪物纳入普遍象征的大传统之中。(一切世上之物,无论动物、植物或矿物,都有道德意义),或者,凡物皆有其寓意,亦即透过它的形态或成分来象征超自然理念。”在康德那里,便成为一种审美快感的表达:“只有一种丑能依照自然的样子来表现而不破坏一切审美快感,因而也不破坏艺术美。”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美被质疑为没有灵魂、空洞的表现,所以风格主义消解古典美,消解和谐的比例,消解理性,“比例与不合比例的区辨不复成立,形式与无形式、有形与无形的分别不复成立:没有形式、无形、模糊的呈现超越了美与丑、真与伪的对立。美的再现日趋复杂,艺术家诉诸想象多于智思,自创新规。”这是一种破坏,也是一种重建,将自我定义为小宇宙的人类开始感受到了“沮丧”,那种和谐的乌托邦开始式微,人已经不是主宰,也从优雅变成了忧郁——丢勒的那幅《忧郁》之画,将忧郁与几何相连,变成了一个象征。曾经的几何就代表着数字宇宙,代表着和谐比例,而现在成为忧郁的方式,成为丧失中心地位的一个隐喻。
18世纪虽然有理性世纪之称,但是,“18世纪是卢梭、康德与萨德侯爵的世纪,甜美人生与断头台的世纪,活力爆发的巴洛克极盛期与洛可可、新古典主义美学蓬勃的世纪,思考并呈现这么一个世纪,自当如是,方近真实。”多元的观念造就了多元的美,而18世纪下半叶发展出来的废墟美学,则将新古典主义的美导向暖昧,在大卫《马拉之死》里,似乎是尊重史实的创作,但是它的意义“不在于冷眼复制自然,而在于其中糅合了各种彼此矛盾的情愫”,这种矛盾体现在:“这位遇刺身亡的革命家,其坚忍的美德使他的肢体之美成为一种媒介,用以重新肯定对理性与大革命的信仰;然而那没有了生命的身体,也透露生命无常的沉哀,凡百事物一旦为时间与死亡吞噬,即永难挽回。”
这看似一种悖论,但身体之美和死亡所展现的悲剧之美却融合在一起,美慢慢变成康德所说的“不涉利害的快感”:快感的物体,我们界定为美,从而在理性之上中发展出了崇高之美:崇峻、壮观的绝崖、电闪雷惊的乌云、火山、暴风雨、汪洋大海,以及其余所有显示自然无限的现象。这些现象让人类的理性独立于自然,也使精神超越感官经验,而崇高在18世纪的时候,也含有对不成形状之物、痛苦、恐惧的偏见。崇高的悲剧性是不是被戴奥尼索斯的酒神精神所照耀?柏克在《崇高与美的观念起源之哲学探讨》中说:“以任何方式激起痛苦与危险之念,亦即,任何恐怖、富于恐怖之事物,或以类似恐怖的方式运作的事物,都是崇高之源,亦即,能产生人类所能感觉的最强烈情绪。”
这种最强烈的的情绪甚至有着产生快感的恐怖:“恐怖如何产生快感?里面蕴含一种对恐惧肇因的超脱,以及对恐惧的漠然。痛苦与恐惧只要其实无害,即成崇高之因。同理,与崇高相连的恐怖,是对不能为我们所拥有,但也无法伤害我们之物的恐怖。”不能为我们所拥有当然是一种美,不管是哥特小说中情色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对死亡的吟咏,不管是惊奇于自己一时满足的丹蒂主义,还是弥漫着腐烂、昏晕、倦怠、恹恹之感颓废主义,都在走向一种“丑的美学”,一种戴奥尼索斯的着魔与疯狂。而这种着魔和疯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丧失宇宙中心的一种沮丧,一种非主宰地位的悲剧。而到了新的时代,美甚至从精神、宗教层面而转向物质,玻璃、铁、铸铁的建筑革命带来的是机器之美,“美学体系重新重视物质,20世纪艺术家则每每独重物质,从新方向探索可能的形式。”而“碎形美学”的出现更将美带向物质化的工业时代。
从和谐之美到崇高之美,从宗教之美到物质之美,从抽象形式到物质的深度,这是美的发展,也是多元的体现,而在这个大众传媒时代,人的宇宙中心地位更加丧失,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工具,这也使人类陷入了真正的沮丧里:“我们的未来访客势将无从辨认大众媒体在20世纪与20世纪以降传播的审美理想是哪个理想。面对这全然的异同宽容、彻底的混合主义、绝对而莫之可遏的美的多神教,他也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