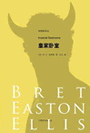 |
编号:C55·2181014·1503 |
| 作者:【美】B·E·埃利斯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42.00元亚马逊18.50元 | |
| ISBN:9787532767014 | |
| 页数:216页 |
埃利斯成名作《比零还少》的续篇。距离1985年25年后,社会已进入了莓手机与笔记本电脑的2010年,天使之城的堕落天使步入中年,当年的大学生克莱成长为好莱坞编剧,面对的却是比迷乱的青春更为残酷的人性遭际:不忠,冷血,贪婪,残暴。作为电影剧本创作者,克莱在演员是否与角色相符这个问题上享有天然的话语权,他将选角办公室变成猎艳场,上演了龌龊的“选角沙发”,他那套俯瞰好莱坞的高层公寓俨然成了可媲美苏丹后宫的“皇家卧室”。黑色悬疑的节奏,错综复杂几近令人毛骨悚然的娱乐圈黑幕,从另一个极端的角度,回归到了上篇的主题——我们依然拥有一切,但我们依然一无所有;这依然是最好的人生,但这依然也是最坏的人生。
《皇家卧室》:听上去像是旧日重现
“无条件的爱,”那男孩儿说,伴随着吉米的人物角色假装羞愧地转过身去,但男孩儿把台词读错了,重音放错了位置,而且在本应绝对严肃的时候洋洋自得地笑,把句话变成了一句抖包袱,而它原本绝不应该成为笑话的。
《比零还少》根本还没有焐热,就冷冰冰地成为了桌子上的一个物体,1个小时只是手翻阅书本发出的声音,机械而直接,没有揣摩,没有复读,合上就是一个简单事件的结束。这是年仅21岁的埃利斯发表的处女作,介绍说,当时这本书的发表“震惊了美国文坛”,所谓的震惊除了一种宣传式的夸大之外,也许是对于埃利斯那个年龄段的作者而言,掀开了一种残酷的青春。走马灯的情节和对话,其实和所谓的文学也差了很大的距离,杂碎而破败,埃利斯只不过复现了一个暴力的社会而已。
一样是撕开塑膜,一样是打开书页,一样是用手翻阅制造机械的声音,一样是对于社会的直击,或者一样是一个多小时的阅读,最后一样是冷冰冰地成为桌子上的一个物体。但是,距离《比零还少》已经过去了25年,埃利斯应该有46岁了,一个1985年就被冠以“著名小说家”的作者为什么在一个阅读者手中还是发现不了真正的文学?一切仿佛从那本处女作的题目开始就注定了这样一种阅读感受,“比零还少”就是在零度以下,它不仅仅是寒冷,而是一种从未探出头来被埋于地下的命运——读者是不是可以用忽略的目光经过?
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的裂隙?其实一开始翻阅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某种文学式的观感体验,而且是关于叙述和阅读、文本和影像,以及在场和虚构之间的诗学意义,“小说在1985年春季出版时,作者已经离开了洛杉矶。1982年他进了新汉普郡的那所小小的大学,正是我那时试图匿身其中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几乎没有交往。”埃利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作者,以及一个电影中的我,以及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本人”。如果按照一种分层的结构来分析,首先是一部小说,小说中有一个本人,也叫我,我是一个和布莱尔有过恋情的人,和朱利安有过经历的人,布莱克和朱利安构成了小说中和我有关的两个人物——而这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比零还少》。但是,在这里,埃利斯是退出了“作者”的位置,他设置了另一个作者,一个孤僻的金发男孩,1985年离开了洛杉矶,之后进入了新汉普郡的大学,当然,他写作了一部小说,小说里也到了那个叫克莱的“我”。
孤僻的金发男孩、离开洛杉矶、进入新汉普郡大学,这是《比零还少》里“克莱”的经历,也就是说,作者就是《比零还少》这部小说的人物,将这个埃利斯原本塑造的“我”变身为作者,其实变成了一种元小说,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个作者和现实中的“我”,也就是在《皇家卧室》里叫克莱的人,有一些纠葛。一方面,作者和克莱曾经恋爱的女孩有过关系,但因为他无法完整回馈她的爱,所以“陷入自身的被动性中无法自拔”,最后使得女孩又转向了我,而克莱认为这一切已经太迟了。也正因为女孩的转向,作者开始在文本中报复我,也就是说,在那部小说里,作者把我塑造成一个叙述者,而他因为无法给予别人爱和友善,变成了一个颓废的青年:“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那个垮掉的派对小子,蹒跚穿过汽车残骸,流着鼻血,问着那些永远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那个永远不懂怎么做对事情的男孩。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那个不能拯救朋友的男孩。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那个无法去爱一个姑娘的男孩。”
尤其是在小说中,作者写到了克莱和布莱克的分手,在可以俯瞰日落大道的餐馆露台上,两个人有过一段告别,而克莱对于布莱尔提出还爱不爱我的问题,直接给了“没有爱”的回答,这在我看来,是作者存心对我的伤害,不仅在小说中我成了一个没有爱的人,而且露台能看到的广告牌上写着“就此消失”,而且,“作者还添油加醋地写道,当我告诉布莱尔我从未爱过她时,我还戴着墨镜”。这些情节在《比零还少》小说里,而我对此的说法是:“我从没有向作者提起过那个痛苦的午后,但这一幕依然逐字逐句地出现在了书中,从那时起我不再同布莱尔说话,埃尔维斯·科斯特洛的那几首我们曾烂熟于心的歌谣我也再听不下去了。”
除了和布莱尔有关之外,小说中当然还提到了朱利安,而当朱利安看了这部小说之后,成为唯一对小说表达尴尬和憎恶的人,“但朱利安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自得的骄傲,接近于兴奋,哪怕作者不但揭露了他的海洛因毒瘾,而且挑明了他因欠债而委身成为一名毒贩的男妓,被皮条客卖给日落大道沿街两侧从贝弗利山到银湖的各家旅店里的男房客。”而这些情节无疑也出现在《比零还少》这部小说中。也就是说,无论是克莱和布莱尔的关系,还是朱利安的经历,都是《比零还少》的情节,这部小说的作者当然是埃利斯,但是埃利斯跳出25年前这部小说而制造出另一个作者,他的意图就是跳出曾经的文本,以个人恩怨的方式再造了作者这一身份,使得自己从文本中脱离出来——甚至,他还煞有介事地说:“小说在1985年春季出版时,作者已经离开了洛杉矶。1982年他进了新汉普郡的那所小小的大学,正是我那时试图匿身其中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几乎没有交往。”
小说中的我,写小说的作者,阅读小说的克莱,和作者有某种关系的我,一种分身的意义在于对于文本的解构,在于建立多重叙事的结构,无疑这个结构带来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书被贴上了小说的标签,但其实只是对事实做了几个细节上的变更,连我们的名字都没有改,里面的所有事情都真实发生过。”因为真实,所以“我多么害怕作者本人”成为了多重文本的一个线索。而且,在这个文本和现实、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的系统之外,埃利斯还增加了在一个文本,那就是电影,作者的小说在出版两年之后改编成了电影,一方面电影和小说大相径庭,电影中没有一点书中的内容,书里朱利安尽管受到了折磨,甚至猥亵,但他毕竟活着,但是在电影里朱利安“必须死”——“他必须为他犯下的所有罪责受罚。这正是这部影片所要的。”另外,影片中饰演“我”的那名演员比小说中的我更接近我本人,“我不是金发,没有古铜色的皮肤,那名演员也不是。”而另一方面,我是电影的一个观众,尽管电影和小说大相径庭,但是当我坐在放映室里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种种痛苦和背叛,“不得不承认原著的确包含了某种事实”——在某一方面,又承认小说中的描写是真实的。
所以,从小说到电影,再回到现实,其实就有了三重文本,而在这三个文本里,我是一样的,却也是不一样的,让作者成为小说中的叙述者,然后设置了另一个作者,然后让叙述者和作者产生矛盾从而影响文本的描写,再用电影的方式让叙述者脱离出来,在电影里又设置了另一个叙述者,让电影与小说大相径庭。埃利斯如此复杂的行动,不断地将“我”抽离出来,用另外的作者,另外的叙述者来代替,就是制造出文本的多重维度,就是编织故事的多重可能,就像已经成为编辑的克莱,在搜索引擎中发现《隐藏》中吉姆的那段台词,本来是回到“什么是你身上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吉米?”最后在演员的表演中,那个“无条件的爱”变成了一种错误,一个笑料,当然,也必将成为一种讽刺。
读错了台词,放错了重音,就像设置了作者,移植了叙述者一样,是一种计策,让严肃甚至带有痛苦结局的故事变成了戏谑,让爱的迷失变成了一种游戏。埃利斯别有用心,用这样一种开篇方式似乎证明了25年的磨练的确带来了文学意义上的惊喜。但是仅仅在开篇,当提到“真实的朱利安是在二十多年后被谋杀的,尸体被丢弃在卢斯费利斯的一栋废弃的公寓楼里,此前他已在另一处地点被折磨致死。”一种对于真实现实的描写又开始了,不再纠缠于文本的多重性,不再制造互文的效果,线性的叙事,大段的对话,破碎的情节,又成为文本的表达方式,似乎在回应题辞中引用埃尔维斯·科斯特洛《超越信仰》中的那句话:“历史重复着那些古老的自负,轻巧的回答,同样的失败……”也不管是和布莱尔之间缺失的爱,还是朱利安不断沉沦的人生,都回到了《比零还少》的固有模式中,就像我听到布莱尔说“朱利安最近在做什么?有人说他其实在经营皮肉生意,娼妓都是些十几岁的少年”时的感叹:“听上去像是旧日重现。”
无疑,和《比零还少》相比,《皇家卧室》明显已经从零度以下状态下坛探出了头,情节已经不再分散,所有的故事似乎都围绕着那个叫雷恩的女人展开。克莱回到洛杉矶是为了《聆听着》这部电影的选角,雷恩希望在电影中得到一个角色,于是直接进入到潜规则里,“我们在多希尼广场十五楼公寓的卧室里过了一个钟头。”一切似乎都完成了,女人的身体,男人的权力,“事后她说她觉得自己和现实脱节了。我告诉她,这没关系。”但是这个开端并没有交易这样简单,先是剧组的凯利出城去棕榈泉,后来失踪了,最后发现了他的尸体,而凯利曾经就是和雷恩一起,上演了如克莱和雷恩的交易;接着,随着我对雷恩的频繁接触,雷恩隐藏的线索越来越多地暴露,布莱尔和瑞普都告诉我雷恩其实一直和朱利安好,他们根本没有分开过,雷恩去看父母都是借口;而瑞普向我提供这样的线索,只不过他也喜欢雷恩,或者他也希望得到一笔交易;而布莱克和朱利安之间的经济纠葛,以及朱利安陷于的债务困境,又使得这个复杂关系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我说是“听上去像是旧日重现”,我说是“哀伤:哀伤无处不在”,但其实在这个“皇家卧室”里,克莱更像是一个捕猎者,他对于雷恩的喜欢或者并不同于朱利安和瑞普和她的关系,在雷恩不见的几天,他甚至说出了“我喜欢她”的表白,似乎一场交易要回到爱的本义上来,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雷恩从来就不属于他,在朱利安和瑞普之间,她也是一个牺牲品,但是正是我的参与成为了决定这个复杂关系的关键砝码,最后在朱利安和雷恩的逃亡中,克莱用卑鄙的手段将他交给了瑞普,“朱利安失踪后,或者说被绑架后——取决于你想要哪个剧本——差不多一周后,他的尸体被发现了。”
朱利安的死只不过是一个剧本,而克莱就是这个剧本的编剧,无疑朱利安之死来自于一个作者的安排,就像他在阐述电影和小说的不同点时说的那样:“但我早就应该想到这点了,因为正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把朱利安送上了这条路,我已经在另一部截然不同的电影里看到他的结局了。”结局无非是文本的一个设计,而想要有其中一个角色的雷恩是不是也自动进入到了剧本里?当朱利安消失的时候,“然后我把她推倒在地上,扒下了她的牛仔裤。”而当朱利安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我对丹尼尔说,雷恩就是一个婊子,“事实上我正在写一个关于她的剧本,名字就叫《小贱人》。”
编剧是作者,他安排了剧中人物的命运,而克莱也是小说中的编剧,也就是说,他的命运是被另一个作者安排的,“这间公寓外面有人在跟踪,艾拉瓦多街上有车在夜里监视这个地方。有人闯进屋来翻我的东西。我还接到过短信给我发狗屎警告,我都不知道他们的警告是为了什么狗屎,但我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有联系的……”连同“皇家卧室”,也成为这个复杂叙事链的一部分,这个公寓的卖家是西好莱坞富家子的父母,而那个男孩就是在这里死去的,“一天晚上夜总会归来后他意外地在睡梦中死去。”于是之后所有的警告短信都被认为是死去的男孩发来的,当台面上的镜子上用红色写着“从这里消失”的时候,一种关于命运的轮回就发生了——就像那个在第一部小说中“从此消失”的广告牌一样,是某种文本上的报复,也是爱和善良缺失的证明。
命运之轮回,死亡之重现,混乱之重复,是比迷乱的青春更为残酷的人性遭际:不忠,虐杀,贪婪,残暴,与光鲜亮丽、仪表堂堂的现实交相辉映,这是把“台词读错了”的现实,这是“把重音放错了位置”的时代,“无条件的爱”只是神话,活着永远不是幸福,因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从不喜欢任何人,我害怕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