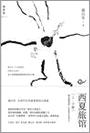 |
编号:C28·2120620·0901 |
| 作者:[台] 骆以军 著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6月 | |
| 定价:78.00元 亚马逊50.20元 | |
| ISBN:9787549502783 | |
| 页数:888页 |
从《乌力波》里读到《经验匮乏者笔记》,才认识骆以军的,作为台湾中生代最重要的小说家,阅读的邂逅对于我来说则是一个世界的展开,而《西夏旅馆》于我,则是完全状态的进入,上下册47万字的厚度里,夹着随书附赠的《经验匮乏者笔记》。“耗时四年倾力书写一部关于异族人、变形者的疯癫、妖艳、镜中幻城的恶魔之书”,腰封里的这句话将一种文本完全置于虚构的名义之下,“请入住二十五间房。以异乡人之名。进入迷离满溢神谕的重回原乡之旅。”这大约是骆以军对这个虚构的注解,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2010年,当《西夏旅馆》荣获华文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首奖时,在颁奖词中说:“以十一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历史托喻,以一座颓废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符号,写出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写作期间曾三度遭受忧郁症侵袭,骆以军的这部“疯癫、妖艳之书”的创作可以用《经验匮乏者笔记》里的那句话阐释:“当众人皆尴尬笑着,拍拍衣裤离去,等待者仍在疲惫的孤岛中,延续那种高烧的意志,一直等下去。”
《西夏旅馆》:时间针尖上的幻术帝国
决定了。他说:你们说要找一个人演儿子。那么是谁来演那个父亲呢?
——《西夏旅馆》(上册·第八节 那晚上)
疑问句打开了一个入口,他和你们,儿子和父亲,以及飘忽的意念,在某一个晚上某一间旅馆,都会变成线索,成为一部小说的出发点。可以只要有疑问,那个入口就可能随时关上,随时朝向相反的方向,儿子或者站在父亲的前面,甚至,儿子领着父亲走出迷宫般的岁月,在那个得不到答案的晚上颠覆一种秩序。就像图尼克的父亲说:“就是在那儿,我父亲将我遗弃了。”而遗弃最后也变成了一种秩序和规则,接着,图尼克被父亲遗弃,图尼克的儿子又遗弃了图尼克,如此循环,在逆反的人伦道路上,所有“决定了”的晚上,或许就是一个遗弃的开始,永劫不复。
那是一个青年的图尼克,一个杀妻的图尼克,一个剖腹自杀中国战神的图尼克,一个裸体摄影的图尼克,而在所有属性上,他必定是一个有遗弃自己的父亲和儿子,那出戏一直在上演,不管哪个晚上,不管在哪里,图尼克的隐喻是一串链接过去和未来,链接自我和他者的符号。而在伦理谱系中,父亲总是被打上某种印记,在儿子的仰望中完成命名,这是成长的必然仪式,这是一部小说打开的全部入口,他们首先不是演员,在自己的角色中维持伦理关系,维持自上而下的道德谱系,或者就是“必须是没有前科、身家清白、没有传染病或猝死危险之重症病历——最重要的,是必须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那些入住旅馆里秘密俱乐部的会员,其实就在在一种正常的谱系里抛却演员属性的人,只是颠倒才会变成一种正常的秩序,这种被彻底否定,从日昼转成晚上,从公开转为秘密,从父亲转为儿子的逆袭之旅,何尝不是另一种命名?所以,关于遗弃,终究成为一种维护秩序的鞭挞之举,内心的渴望无非是为了寻求父性的完满表达,而当“一群流亡者和一个被遗弃的男孩——刚好颠倒、相反、互为镜中之影”的时候,正常的秩序便由此进入了“一个乱针刺绣,一个南方的、离散的,因为彻底失去原乡而绝望妖幻长出的繁丽畸梦。”
梦何尝没有示人的入口?只是颠倒和反射,都让人看到了背后的那些光怪陆离,而谱系中的时间在这梦境之中,变成了一条背离现实的甬道。父亲在这头,儿子在那头,历史在这头,现实在那头,爱情在这头,乱伦在那头,或者,生命在这头,死亡在那头。这时间在哪里开启,在哪里关闭?或者只有在梦境中才能找到它必然的方向,大约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在那烟雾弥漫的夜车里”;或者是马戛尔尼勋爵前往中国的一七九三年,“编造出一个他们恐惧、憎恶、着迷、意淫的靡丽国度”;又或者是发现完整“迦陵频伽”琉璃瓦塑像的二〇〇〇年四月三十日,“这种人首鸟身的奇幻神物,马上取代了‘鱼身枭’与‘鎏金牛’。”而在时间针尖上,对于一个父性支撑的梦境里,必定是充满着征服和统治,充满着“权力伦谱系”,而作为一种历史事件的叙述,“父亲”成为一种书写方式,他停留在“公元一二二四至一二二七年里的第81条”,一本手抄稿的“散见资料编年辑录”,时间的叙述是:成吉思汗出征进兵围城灵州时驾崩。
书写的方式,停顿在某一个历史中,“父亲”这个词里到底含有多少虚构和传奇,含有时间之外的真实和梦幻?《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只是其中的一个入口,你或许还可以从另一种文本中进入那个有关“父性”的繁丽畸梦,比如《如烟消逝的两百年帝国》——真正的书名应正名为:《如烟消逝的致远舰》,关于幽灵船的小说,文本的命名就如谱系一样,也充满着对于秩序的维护,而从文本到文本,从历史到小说,那个叫做“西夏”的帝国或许就是一个时间针尖上的“父性”帝国,“刚好颠倒、相反、互为镜中之影”的无非就是这个进入谱系的入口。那81页停顿在历史之外,时间之外,文本之外,而在这个有关时间的“幻术帝国”里,有着不相容的互为梦中之境的生与死:“成吉思汗的死。夏主李睍的死。他们变成两个面孔僵硬分坐长桌两端的赌徒,等着对方叫牌。”西夏和蒙古,帝国和另一个帝国,互为迷宫,也互为镜中之影,当然,最终他们展现的就是父性的吞食和征服之欲。“在李元昊和成吉思汗互为迷宫的梦境里,不将我党项人全部灭族清洗,说不定历史上征服欧亚非大陆的庞大帝国,未必是他成吉思汗的后代,而是李元昊的子裔们。”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轮回?互为梦境的最后结果必然是一种时间序列,在历史的81页之后潺然流动,而戛然而止的无非是帝国梦境的幻灭,一个强大帝国的覆灭,有时却悄无声息,像是手抄在那个页码上的永久停留。
西夏帝国的最后一支骑兵终于没能冲出历史的包围,而在历史之上,帝国的版图曾经以一种“父性”的嗜血荣光而书写,“整个西夏王朝像海市蜃楼从幻影中矗立而起,那全是他嵬名元昊一人的意志。”李元昊,西夏历史上的帝王,创造了西夏帝国,不管是“从四面八方扑向任福和他穿着雪白纸铠甲的宋骑兵”的好水川之战,还是“以李元昊诡秘微笑的特写脸部作为淡出画面背景的”的夏辽大战,又或是惨败的“河湟之战”,李元昊用他的父性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但是,作为一个拥有王权一切的帝国首领,他同样是一个“杀妻瘾重症患者”。在一个“鲜血不断涌出的一张滑稽鬼脸作为结束”的悲剧里,七个妻子都是一种牺牲品,家族、色相或者其他的权势,都只是走向死亡的一个步骤而已。他的父性帝国就是为了完成自我的命名,完成秩序的永久遵从,“就像一个吞食着自己的人形之蛹而变态进化的未来人”。而站在父性对面的是女人和子嗣,作为一种存在,杀妻瘾其实就是一种对于男女规则的颠覆,“原该是媳妇的成了情敌,原该是枕边人的成了皇姨娘”,这种乱伦式的颠覆恰好在诠释着父性的盲从和恶毒,而李元昊作为西夏帝国的象征,走在极端的路上,而这也正是让帝国走向永劫不复的一个原因,这是父性的黑洞,当帝国的“所有战士皆在没有影子没有疼痛的魔术中死去之后”,所谓的西夏“幻术帝国”也成为了一种遥远的象征:“西夏终将成为一种在它自己的字典被归类与流沙、谎言、谜、午睡之梦……同性质的事物。”
这是不是意味着,解开了西夏帝国幻术之灭,或者说为那个历史湮灭的帝国覆灭找到了一条线索,但是所谓的“西夏”,所谓的“杀妻瘾重症患者”,所谓的梦境和战争,以及“变态进化的未来人”,都是一种时间针尖上的象征而已,都是有关父性的永劫不复的循环,如果回到起点,是一个种族、家族之间的覆灭和延续的选择,“简单告诉你吧,我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最后一个西夏人。”到底如何成为一个物种上的“西夏人”,或者是精神上的“西夏人”,而在实际上,覆灭的西夏帝国在“时间之界面乱窜互叠的末日场景”,根本没有“冲出蒙古人的灭绝网兜”,散乱在现实的“西夏人”无非是在寻求一种归宿,关于存在,关于身体,关于秩序,甚至关于“不在场的证明”,都将在现实之外找到“幻术帝国”,而那个象征意义上的“西夏旅馆”出现在梦境之侧,出现在迷宫的尽头,也出现在不可改变的“卵壳世界”里。
所有的过往,都在时间的叙述里,所以西夏早就成为“另一个国度”,那些考据和论文所指向的西夏只是“大量伪造、错误链接”,这是父亲书写中的错误,目的就是为了在人造的灾难中,用父性的虚构和梦境来消解父性的原始属性。这种自我毁灭的证据一直存在于“西夏旅馆”的象征中。“西夏旅馆”变成了疯人院,“一支盗用被他们秘密处死的旅人遗骸和毛发作为文字,因此被诅咒全族将在乱伦、血腥复仇、遭马匹践踏祖坟脉穴、且全族男子将被敌人骑兵自后抓住后发辫砍下头来的大屠杀场中集体灭族的部落。”无非是还原那个历史镜像,在非现实、非历史中寻找悲剧该有的归宿,但是“西夏旅馆”的象征不止于此,真正的西夏旅馆是为了摆脱历史的梦魇,从一个个体的归宿出发:“这幢旅馆的每一个房间里的住客,都以为自己有段离奇罕异的身世,其实他们全只是那其中一条螺旋体上寄的一小格基因密码,一颗记忆复制时活版印刷的铅字。”消灭历史,消灭时间属性是不是一种庇护?而对于西夏这种父性维护者的后代,一定要为自己重新寻找自我的定义。从李元昊的符号开始,“父性”的对面就必然站着两种身份:女性和子嗣,父/母、父/子的二元关系实际上是隐射着统治和被统治、延续和遗弃的对立。父性/母性在西夏历史中已经成为悲剧的起源,而这种悲剧直接成为性别阉割的一个历史原罪,当手指残存的记忆里“摸到一个类似喉结的硬物”,疑问是:“那个女体并不是他的妻子?”图尼克延续着一个杀妻的寓言,“你们知道,那墙上,十幅画有九幅是他老婆的脸。”而实际上,这种悬挂在墙上类似遗照的待遇并没有在现实中成为缅怀的一种,相反在“他和她”的故事里成为色情和乱伦的一部分,“爸,你弄得我好舒服”已经作为一个剧本在上演,“悲惨的乱伦金字塔之锥倒插在那父亲背脊的古怪处境”,这就是宿命,而更大的宿命并不在上演的剧本里,不再这撒娇里,而在我们礼仪的生活里,“即使最沦为嫖客和妓女打炮这种悲惨关系,仍是充满敬语、卷舌音、进退合宜的官话……”纯净的石化语言里暗含着一个被历史劫持的色情符号,而对于父性来说,这是沉溺在黑暗中,所有女性都变成了无生命的载体,死亡也了无意义,“某种赫莉变成了肉块”?或者在安金藏的“丧妻俱乐部”和图尼克的招妓生活里,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存在感,而作为极端的符号之一,图尼克的母亲作为“汉人”,异端文化的一种,也取消了作为女性的存在意义,“是在她的这一生,她的角色像暗哑人一般静默。”
而在另一个关系轴线上,父与子就显得多元,遗弃和继承的矛盾其实是一个家族的选择,而在一个“吞食着自己的人形之蛹而变态进化的未来人”面前,所谓的子嗣也只是一种虚妄,李元昊在七个妻子的悲剧后,也制造了儿子的另一个悲剧,只不过在那时,他的儿子宁令哥成为牺牲品:“在转身逃亡的一百米宫门外,被没藏讹庞埋伏的卫士剁成肉酱”。杀戮的背后绝不仅仅是权利的最大化,“儿子”成为一个可以演饰的角色,一个“变成”的人,甚至成为那个“长在他左脚膝盖上的‘人面疮’”。病态的肉体,病态的关系,是不是一定需要某种切割的疼痛?图尼克的父亲在最后扬起脖子看到的男孩,已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一只鸟,“不,一个人头鸟身的怪物”。怪物现身的背后是父/子关系的颠覆,而如《封神榜》里雷震子的现身是不是另一种暗喻?作为西伯侯姬昌的第一百个儿子,无非是一块“肉羹”,却能“生出四足,长上两耳,望西跑去了”,神话般的降生,“变成”的个体里是一种脱离父体的肉芽,而在这种被神话想象的子嗣继承其实是另一个幻梦,对于某种父性帝国来说,一定是带着谎言的历史,就如被遗弃的图尼克所说,“身世”变成一个迷,变成图尼克二号的一个巨大疑问。
没有身世,没有归宿,没有父性,在一座“西夏旅馆”里成为实实在在的“异乡人”,被遗弃的儿子,被演饰的儿子,或者是一个“他者”的儿子,“因为无父才得以让创造力任意窜走颠倒梦境。因为无父才得以随意下载各种盗版他人之梦境以拼装自自己之身世。因为无父才能自由进出道德承受极限边界外的禁区。”“无父”就是在“夏日旅馆”里“一切皆新鲜而无有客途陌生床铺之酸疼疲惫”,孤自一人、独卧一室,都是一种自由和身体的重植,在“一条断掉的染色体”的家族中,我们也成为一个陌生词,而那“西夏旅馆”终于可以成为”被驱赶出‘我们’之外的‘他们’的旅馆”,那些“脱汉人胡的可怜鬼”就是“无父”之人,就是那些找不到自我的“外省人”。
作为“外省”,陌生的旅馆是图尼克的“大量的隐喻”,而对于一个地域和文化指向的隐喻,实际上已经完全走到了现实主义的大道上,骆以军已经站在了旅馆的内部,还有什么比允许一个“外省人”入住来得更为直接?“请入住二十五间客房。以异乡人之名。进入迷离满溢神谕的重回原乡之旅。”“请入住十六间客房。此处长出繁丽畸梦。作为救赎交换来岁月静好。”两副对联一般,悬挂在文本的上下两册之上,二十五间和十六间,在数字化的演绎中,西夏旅馆其实完全变成了梦境,十七楼的高空?脱胡入汉的集中营?或者也是一个丧妻俱乐部,“以那房间为梦境入口”,在二十五和十六间的尽头,是骆以军满含笑容的欢迎仪式,入住旅馆就是寻求“无父”的庇护:“这里的人全是过路客、侵入他人土地者、无主之鬼,在时空暂时抛锚的漂浮感恓惶地寻求庇护。”
原乡的迷失,是不是历史的迷失?是不是那一种消失的帝国的幻灭?是不是权利谱系的颠覆?“西夏”永远是“一无限长的时间计量”,是文明全景的“刺绣”,在杀戮面前,在父性面前,所谓的“母性”是一种赎罪,而更多的子嗣遗弃中,父性其实在偏离人伦和家族的有序轨道,“谁来演那个父亲”成为一个超越历史的疑问,当一间旅馆变成“永无终点的流浪之途”,所谓父性也只是一个“孤独王国的国王”:“我成了一个孤独王国的国王。永远只有我一人站在那里。”身世是一个虚幻的梦,而丧失父性的继承也只是一个不存在的镜中之影,只是一种魔术,一种雌雄同体的存在,一个暗哑人:“这时的‘西夏’反而不是台湾,而是外省人及其后裔。”
那个夏日旅馆里的他,最后在“四人关系的交集游戏中成为真正的剩余者”,历史的剩余也都是被书写的“大量伪造、错误链接”,而从西夏指向“外省”的现在之城,就是骆以军所重建的“在时间针尖上的幻术帝国”,而最后图尼克造字看起来是是为了重建秩序,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虚幻图景,是历史的镜像而已,比如那个“鬼”字,在一次次现有词库的扫描中,却成为“FZ豈防,<>玄~心;…全防妻二兰厉A叫一一\防”的字符集合,无法破译,亦即对于存在的陌生,这种陌生感在骆以军获得第三届“红楼梦”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成为“他者”的一个注解:
在我所承接的小说时光,另有一条不同时间钟面的“梦的甬道”,因为百年来的战乱、大迁移与离散,有另一群人被历史的错谬,脱锚离开了“中国”这个故事原乡(这其中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在一个异乡、异境,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抛离处境中,慢慢变貌、异化,在他们的追忆故事中长出兽毛和鳞片,形成另一种“歪斜之梦”的孵梦蜂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