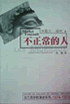 |
编号:B52·2030316·0660 |
|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03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22.00元 | |
| 页数:400页 |
本书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一部分讲演记录稿的结集。其实,福柯的几乎所有著述,都可以归在“不正常的人”这个题目下。《疯癫与文明》讲的是疯子,《规训与惩罚》讲的是罪犯,《性史》讲的是各种性倒错者。福柯总的意思是,“不正常的人”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疯子”、“罪犯”、“性倒错者”这些名词所指称的人虽然自古就有,但他们被当作另类来看待和对待,却是长期历史中权力(其中包括知识)运作的结果。建构不外乎划界限,既云界限,就分两边,划出去的属“不正常”,划进来的就是“正常”,所以,正常人其实也是建构的产物。
现在,你们看到由于类似夏尔·茹伊这样的人物,由于这一类被如此精神病学化的个人,这三个要素,或者如果你们愿意,这三种人物将汇合一处:小手淫者,严重的畸形,以及这个不服从任何纪律的人。
——《1975年3月19日》
1867年的一个具体事件,具体事件中的具体人物,具体人物表现的具体症候:一个名叫夏尔·茹伊的女孩和另一个女孩在树林边上遇到了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于是她们让他手淫,之后她们“毫无问题”地向一个成人吹嘘这件事,并笑着说“挤出来浓浓的奶”,而那个成人回应道:“哦,你们是‘两个小坏蛋’!”在美好的乡村场景中,19世纪的这个案例以夏尔·茹伊“毫无问题”的态度,以听者笑着回应的方式,成为米歇尔·福柯对于“不正常的人”进行精神病学知识和权力普遍化研究的一个案例。
米歇尔·福柯所说“这三者完全混杂的形象”是指“挤出来浓浓的奶”的夏尔·茹伊?是指那个头脑简单被手淫的人?还是笑着说她们是“两个小坏蛋”的成人?像一个玩笑,当夏尔·茹伊“毫无问题”地给头脑简单的人手淫,当她成为别人眼中的“小坏蛋”,夏尔·茹伊无疑就成了福柯所说的“被精神病学化”的人,她是三种人物的汇合:是小手淫者,是严重的畸形,是不服从任何纪律的人——当成人说他们是“小坏蛋”的时候,看起来是戏谑,实际上包含着把夏尔·茹伊归类为“不服从任何纪律的人”的权力,夏尔·茹伊给头脑简单的人手淫,“挤出浓浓的奶”就是让自己成为了“小手淫者”,而她的“毫无问题”带来的无耻感构成了也“严重的畸形“。
1867年的案例混杂了三种人物形象,混合了精神病学化的三个要素,福柯分析了案例中构成行为意义上精神病学成为可能的东西,首先不是“突然膨胀起来的本能的过分和过度”,而是不足,是缺失,是发展的停滞;而童年构成了精神病学的知识和权力普遍化的历史条件,两者所构建的是幼儿的精神病学化,但是对精神病学化进行命名的权力则属于成人,也就是说,在成人行为和幼稚科学之间,精神病学成为了关于正常和不正常行为的科学。夏尔·茹伊事件是19世纪下半叶的一个现实样本,但它为19世纪末精神病学在理论和话语上的建构提供了可能,福柯分析了这套新分类学建构的三个方面:一是把一系列变态的、异常的行为组织和描述为疾病的症状,从而将其视为不正常的症候群;第二个特征就是在重新评估中确立了“谵妄的回归”;第三,则是将法莱尔引入的“精神本质”进行了重新阐述并将其命名为“状态”。
症候群的分类学,谵妄的分类学,状态的分类学,19世纪末的精神病学从这三个方面构筑其理论结构和话语,它具有的巨大任务就是提高医学权力的价值,但是对于“不正常的人”的病理学建构,却又使它在“退化”中形成了一个悖论。“退化”是对不正常的人进行医学化的主要理论工具,退化者于是变成了“神秘地医学化了的不正常的人”,这是一个医学权力价值的体现,但是医学化了不正常的人却使精神病学在扩张中不再围绕疾病——与种族主义的接通就是一个证明:从退化的概念出发,从对遗传的分析出发,精神病学导致的就是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和人种的种族主义不同,它部分导致的是优生学的产生。所以为了解决这种悖论,福柯认为,精神病学还有一个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那就是社会保护功能,“它把无政府主义、社会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精神病学化作为出发点。”针对政治犯罪,精神病学能够起到保护社会秩序的意义。
但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完成“1975年3月19日”这一讲座之后,留下的是“我将重新思考”的计划,“1975-1976年的讲课将结束这一系列,这将是对一种机制的研究,通过这种机制,人们从19世纪末起企图‘保卫社会’。”将来时变成了未完成的状态,福柯的提前结束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退化”?当“保卫社会”的极致研究成为一个空白,当精神病学与种族主义、保卫社会无法形成对悖论的解构,“不正常的人”是不是将永远在不正常的建构中?——这种不正常似乎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回到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的第一课,1867年混合形象的案例也演变成了1955年两个极端的个案。
这是1955年的刑事精神病学鉴定报告,一个女人和她的情人,以残忍的手段杀死了女人的小女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案?女人的情人是一个私生子,他由母亲养大,很晚才被父亲承认,并有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父亲死了,他独自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的境况不佳,但是她仍让儿子读中学。福柯重点分析的是受害者母亲之外的那个情人,在他看来,情人的出身和经历构成了一种“反常”:他属于一个鱼龙混杂很不稳定的阶层,父母之间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状况,对他的自尊心产生了影响,“大体上说,他这一类的人总是感到没有很好地被他们所处的世界接受;从这里就产生了对反常思想和对一切导致混乱之物的信仰。”另外他分析认为在心理特征上,这个情人明显有着一种“唐璜主义”。而当他和女人在一起时,曾说起过一对伴侣为了建立不可分离的关系,必须去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虽然没有直接说过会杀死自己的女儿,但是女人却决定这么做,而情人也没有推翻这个说法,他的这种“反常”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缺乏批判精神的女人,甚至把这些反常当作了行为的准则。
福柯还提到了同样出现在1955年的另一个精神病学鉴定报告,那是关于一起性案件中被控告勒索的三个男人的报告,报告指出三个男人都存在着道德问题,淫荡或者同性恋,最后变成了“罪恶”。福柯分析了两个鉴定报告,为什么这些和犯罪有关的案件是从精神病学进行的鉴定?法律话语是不是转变为了医学话语?在他看来,社会同时拥有三种属性的话语,一种是司法话语,一种是医学话语,另一种则是真理话语,在这两个案例中,福柯认为医学话语代替了司法裁决的话语,从而使得真理话语的运转变成一个问题,而真理话语的问题其实质则是科学话语的缺失,如此,所谓的鉴定报告甚至成为了一个笑话,“司法真理的运转不仅成为问题,而且引人发笑,这不是第一次了。”
为什么杀人的话语变成了使人发笑的话语?如果让要司法话语运转成真理话语和科学话语,需要的是关于惩罚的原则,除了充分的、完全的、完整的证据之外,还需要一种“证明的算术体系”,那就是“内心确信”的原则:法官只能在内心完全确信而不是仅仅怀疑罪行成立的情况下才能判刑;只有法律规定和确定资格的证据才能有效;人们承认证明成立所依据的标准不是有效证据的规范表格,而是确信:任意一个主体,即不同主体的确信。这是内心确信原则的三个意义,但是内心原则即构成了对司法真实性的现实操作,又使它失去了平衡,甚至导致了扭曲,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主体进行陈述时,出现了“怪诞”的话语,而“怪诞”的背后则是行政权力,“怪诞是行政权力运行中的一个内在手法。”在这样的话语中,“权力赋予自己这样的形象,这种形象来源于这样的人,他戏剧化地乔装打扮得像一个小丑。”
福柯将这种话语称之为“于布话语”,这个出现于1922年的词汇出自A.加里的戏剧《于布王》,“指某个人,由于其怪诞的、荒谬的或可笑的性格,使人想到于布这个人物”,它是“极端地戏剧性的残忍、厚颜无耻和胆怯”的象征,在权力的“于布式”陈述中,司法话语被精神病学鉴定所取代,案件中人物品行所违反的不是法律,“心理不成熟”,“不健全的人格’,“深度不平衡”的鉴定本身就指向了“不合规范的举止”,并将其视为“变成犯罪的对偶物”,也就是说,法官判决和惩罚所针对的是“被假定为犯罪的原因、根源和形成之处”——精神病学鉴定完成了一种运转,它使得惩罚由法律确定的犯罪转到从心理-道德角度衡量的犯罪性可能。而精神病学鉴定的运转还没有结束,福柯认为在给犯罪叠加上犯罪性之外,还给犯罪的责任人叠加了18世纪出现的“犯罪人”,即“人在没有犯罪之前就已经像犯这种罪的人”。由此,犯罪的主体在精神病学鉴定中变成了客体,“一种纠正、使再适应、使再被接纳、改造的技术和知识的客体。”客体出现了,那么主体必将诞生,他就是给罪行叠加上犯罪性的医生-法官,“惩罚这个肮脏的职业就这样变成了治疗这个美好的职业。这个转变是精神病学分析造成的转变之一。”在一系列关系的转换和取代中,精神病学建立了一种规范化的权力,而这种被建构起来的规范化权力除了医学上的惩罚权力之外,更有政治权力、社会权力、教会权力等,“规范化权力的出现,它形成的方式,它得以安置的方式,它从不只依靠唯一的制度,通过游戏,它最终在不同的制度中建立起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扩展了它的统治权——这正是我想要研究的。”
精神病学鉴定提供的病理学样本,如何通向“不正常的人”这个问题?当人行为时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就既无罪行也无犯法,精神病学鉴定应当允许,这种允许其实是进行了二元划分:疾病和责任之间,病理学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主体的自由之间,治疗学和惩罚之间,医学和刑罚之间,医院和监狱之间。这种二元划分其实是相互排斥的,但是鉴定却变成了医学和司法的双重定性,同时,“要么监狱,要么医院”,“要么赎罪,要么治疗”的制度性交替也被社会反应的同质性原则取代——社会反应的同质性做出的判断是:他是不是反常?他是不是具有危险性?所以反常和危险变成了法医鉴定的本质核心和理论核心——福柯指出了这种鉴定的可笑之处,“在法医鉴定中,司法和精神病学相互通奸。”相互排斥具有的独立性被“相互通奸”具有的叠加性所取代,对正常、不正常的二元划分也变成了对个体进行规范化惩罚的权力——以18世纪出现的对待鼠疫病人的“容纳”控制为例,当它不再是以前对麻风病人的排斥,这种“容纳”意味着权力相对于个人越来越精细地接近,当个体解体,法律便被遗忘,“它是政治权力发挥到极致的美妙时刻。”被解构的个体权力,最终便产生了“不正常的人”。
从法律制度到医学病理,这是权力的一次转变,而权力在构建惩罚机制中又使得个体被解构,从而形成了规范化、普遍性的“不正常的人”,在这个精神病学化过程中,权力完成了它的谱系学,“这是一种其他类型的权力,我暂时把它称为规范化权力。通过鉴定,人们有了一种关涉不正常的人的活动,它使用某种规范化权力进行干预,并且它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它保证医学和司法之间联系的作用,趋向于一步一步既改变司法权力又改变精神病学知识,把自己建立成对不正常进行控制的机构。”福柯说,“它指向了奇特的权力谱系学”,由此,福柯分析了19世纪发挥作用的三个“不正常”的领域,它们是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和手淫的儿童:畸形首先就是一个法律概念,它站在法律的对立面,违法而且达到了极限的违法,但是它不引起法律的回应,它是把不可能和不允许结合起来的东西。但是当它是一个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当它成为反自然的形式,畸形的人便成为了“需要改造的个人”,在定义扩大中,不仅畸形的人,而且需要改造的人,都成为了普遍现象;而手淫的儿童是19世纪出现的全新形象,本身这一形象被限定在卧室、肉体、父母等狭窄的空间里,但是在最极端变态的解释中,它也成为了一种近乎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人手淫”所折射的不正常的性,又将“不正常的人”拖入到了悖论空间里。
这三个不正常的领域是如何在规范化权力中变成普遍现象?权力又如何在干预中建立它奇特的谱系学的?第一种不正常的人是畸形的人,福柯进行溯源认为,畸形不是医学概念,而是法律概念——罗马法明显是作为畸形领域的背景,只有在自然法则的混乱触及法律,使法律混乱和担忧的时候,才存在畸形性,也就是说,畸形是自然的混乱在法律中引起的“决疑论”,但是当法律成为畸形的背景,本身就制造了混乱:是否应当为一个有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脑袋,或者有动物的身体和人的脑袋的个体进行洗礼?如果出生的是一个畸胎,财产将归谁?当一个有两个身体或有两个脑袋的畸胎出生的时候,是应当给他洗一次礼,还是两次呢?18世纪的转变是“道德畸形的自治化”,也就是说吧畸形从古老的体质和自然的混乱领域转移到纯粹简单的犯罪领域,福柯认为,这样的转变是惩罚权利的经济学转变,但是到了19世纪,道德畸形又将转变的关系倒转过来,人们认为所有罪行的深处都有畸形,“无论如何,每个罪犯都可能是畸形,与过去每个畸形都有可能是罪犯一样。”而第一个出现的道德畸形是政治畸形,而第一个政治畸形则是国王,“在惩罚权力经济学的新体制中出现的、显露的第一个法律畸形,第一个出现的畸形,第一个被定位和定性的畸形,不是杀人犯,不是强奸犯,不是破坏自然法的人;而是破坏社会根本契约的人。第一个畸形,是国王。”
福柯考察了畸形历史,他认为,畸形人物有两个轮廓:吃人和乱伦,“他统治着刑事精神病学和犯罪心理学的最初年月。”于是犯罪精神病学从畸形出发被建构起来,而惩罚机制需要对理性有清晰的确认,更需要确认惩罚的主体的理性,正是畸形人缺乏理性,所以此种惩罚权力受到质疑,而这便造成了疯癫,“理由的缺席马上变成疯癫的在场。”而疯癫在傅尔尼、马克等人的理论中指向了本能,也使得无理由的行为过渡到了本能行为,“本能理所当然将成为不正常这个问题的媒介,或者还是一个操作者,通过它,犯罪的畸形和简单的病理学上的疯癫将找到它们进行配合的原则。”
用本能构建疯癫理论,使得精神病学的惩罚机制具有了普遍化:精神病学和行政控制被挂钩,建立行政的参照系;精神病学在家庭中成为一种“消费”,家庭成为另一种参照系;精神病学具有了政治要求,政治参照在社会稳定和静止的背景上使疯癫突出出来——在三种普遍化进程中,精神病学建立了三个参照系,这三个参照系完成了精神病学“非精神病化”,福柯说:“精神病学的运转不再需要疯癫,它不再需要精神错乱,它不再需要谵妄,它不再需要精神发狂。精神病学可以在不参照精神病的情况下把每个行为精神病学化。”精神病学成为关于不正常的人的科学和技术,对于精神病学来说,与犯罪-疯癫的相遇将不是一个极限的情况,而是一个通常的情况。
畸形和需要改造的个人,在精神病学“非精神病化”中建立了对于不正常的人的普遍机制,而当性问题穿越不正常这个领域时,社会权力、教会权力在规范化中建立了属于他们的奇特的谱系学。“性在西方,并不是人们要求保持沉默的东西,并不是人们必须使它沉默的东西,而是人们必须加以坦白的东西。”这种坦白,自然建立齐了强迫坦白的权力程序,这便是“忏悔”,而手淫成为可坦白的性的首要形式,“坦白的话语,性的耻辱的、控制的、矫正的话语主要是从手淫开始的。”当肉体化的身体在大的生理学中和身体的纪律问题结合起来,肉体便成为权力体系和机制的相关物,而手淫问题也指向了教育医学,指向了本能这个不正常的中心问题,一方面,教会建立了审查的法律、坦白的机制,忏悔的模式,它以权力的干预完成了对肉欲之罪的惩罚。而另一方面,手淫的体质化归因于引诱时,它凸显的是社会和家庭这个成人世界的问题,“医学-家庭的齿轮组织了这个同时是伦理和病理的领域,性行为在这里被当作控制、强制、审查、审判和干预的对象。”但是福柯认为,社会权力并不意味着家庭是控制的新组织,反而通过儿童的性让家庭落入陷阱,“在其掩护下,人们从家庭那里骗取了孩子。”或者说家庭也是规范性权力的一个控制物,而乱伦则变成了家庭意义上的不正常,它同样被纳入到更广泛的社会权力和教会权力体系中。
畸形的人,需要改造的人和手淫者,这是福柯所说的“不正常的人”的三个领域,它们在精神病学的认识论、政治任务的本能和性的孪生理论中被制造出来,构建了“谱系之书”,这种谱系学在19世纪心理病理学的重要论著——海因里希·卡恩的《性心理病理学》中得到了论述,他指出存在着一种与消化器官对应的饥饿的感觉、感受和动力学,它是一种本能,是在自然化和普遍化原则中建立的病理学。当不正常的人在病理学上成为权力的客体,当权力建立普遍化和规范化惩罚机制,精神病学的非精神病化便完成了权力的谱系学,正是这种权力谱系学命名了不正常的人,“我要说,精神病学当它把自己建构为针对精神错乱的医学的时候,就把疯癫精神病学化了,而疯癫也许并不是疾病,但是它为了确实成为医学必须在自己的话语中把它当作并使它等同于一种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