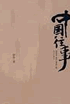 |
编号:C28·2080104·0754 |
| 作者:伊沙 | |
| 出版:远方出版社 | |
| 版本:2007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28.00元 | |
| 页数:283页 |
本书是一部带有“自叙传”意味的长篇小说,通过童年-少年视角的目击,展现出上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重大转型以及时代变迁对于人民生活和心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部真实有力的“个人编年史”暗含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一个国家的断代史。同时,这又是一部不同一般的“成长小说”,见证着大时代里也有个人的成长秘密,也有青梅竹马、青春萌动和性的困惑、迷茫与觉醒……
刚会写我的大名时,我还老是有点儿纳闷:这“武文革”和“索索”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突然就从“索索”变成了“武文革”了呢?我到底是“索索”还是“武文革”啊?
——《第六章 1975》
武文革是一种命名,索索是另一种命名,两种命名以相异的方式指向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武文革”是正规的姓名,是开始上学之后的大名,是被书写被点名的符号,它指向的是一种正式叙事;“索索”是小名,是上学之前的昵称,是属于童年纪事的记忆之名,它指向的是一种童趣叙事。当“我”被动完成了新一轮的命名,正式拥有了“武文革”这一大名,心中的疑惑更指向一种并不接受的现实,而这种疑惑甚至反抗,正是1975年这个时代的某种转向。
从“索索”变成“武文革”是一种突然发生的事件,突然的背后便是以“武文革”为代表的命名体系对以“索索”为代表的童年记忆的压制和篡改,两种命名、两个世界变成了一种对立,而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中国往事”正是在对立中展开的。书名叫《中国往事》,题辞是如下这句话:“以下是我最早认识的一组汉字(我相信你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伊沙用这样的方式赋予了时代一种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武文革”这一名字甚至也成为一个被打上烙印的名字。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存,到底会遭遇何种“成长的烦恼”?从1970年“世界开始了”,“我”无疑就是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父亲在西安的地质勘探队里,常年在外面工作,母亲则在上海,她所从事的是研制坦克上的激光瞄准镜,父母分居两地,而且都在为这个国家工作,无疑,“我”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是缺少完整性的。
之后母亲因为事故而逝世,“我”甚至连最后一眼也没有看见,整个70年代,“我”像是被抛到了一个陌生世界,而在这个陌生世界里,具有时代特色的国家事件构成了“我”记忆中的宏大叙事:1972年,我开始识字,所认识的三组汉字就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是因为这一年举办了“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特殊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从1966年“文革”爆发开始陷于瘫痪的体育行业开始恢复正常,这届运动会的举办正是一个重新起步的信号。”1974年我看到学校的宣传栏上写着大标题:“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后来在路边看到群众打出的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我市!”1975年,“勇交白卷”的习小羊变成了学习的榜样,他成为了学校里涌现的“时代英雄”;1976年听闻了“敬爱的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学校操场上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誓师大会,之后毛主席逝世,老师“苏太太”向班里同学发出了“给毛主席守夜”的倡议,肩负起“严防阶级敌人盗窃遗像花圈破坏灵堂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后来的消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这个属于父亲的春天,传来了在首都召开全国科技大会的消息,父亲作为代表受邀参加;1979年,开年就有了“大事”,这既是“国家大事”,又是“世界大事”:元旦《上海公告》发表,中美两国建交,接着邓小平访美,中美关系正常化,而父亲第二次结婚,我的继母生下了一个弟弟,他被取名叫“武开放”——一个和“武文革”一样具有时代感的名字,一个折射出国家宏大叙事的命名。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时间轴上,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的举办、批林批孔斗争、西哈努克亲王芳华、勇交白卷成为时代英雄、周恩来逝世、毛泽东逝世、批邓反击右倾运动、“四人帮”被粉碎、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中美邦交正常化,这些事件构成了国家层面叙事,当这些事件发生,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无疑会产生复杂的情感,一种是被动状态下的体验感。对于“我”来说,1970年是“世界开始了”的起点,这一年对于我的第一次就是“狠狠摔在泥水里的惨痛一跤”,在被“三八式的老干部”刘书记的儿子刘虎子、习小羊等人的欺负下,这一跤开启了“我对周围世界的记忆之门”,而导致这一跤的便是“暴力”,而我也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赢得了第一个朋友习小羊,“我的第一个朋友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获得的,这让我对暴力有了初步的好感。”之后我通过钻入裤裆的“收编仪式”加入了刘虎子领导的“革命队伍”,开始了文革一样的革命体验。
这是一种主动融入,但是更多的体验却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远在上海的母亲因为“激光的辐射毁坏了他们的血液”而死去,祖母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叫我吃饭而踩滑,最后突发脑溢血告别人世,常奶奶在一个雨夜因为房子倒塌而被砸死,以及之后舅婆的去世,这些死亡构成了我的一种体验,它们如此直接,又如此猝然;死亡之外,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我总是寄宿在别人家里,从常奶奶到舅婆,从刑阿姨到“娘娘”,从“六号坑”里的斗争到成为捡垃圾的孩子,以及从西安到成都,从成都返回西安,以及去往上海等生活空间的转变,都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个人体验,它是一种缺少归宿、缺少爱的存在,而这也正是这个时代带来的某种苦难,它在“我”的成长中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在这样一种体验中,“我”对之的反应有“以暴制暴”式的适应,有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第一次听《红色娘子军》、第一次看见彩色电视机、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的惊喜,更有一种保存个体意义的对抗,于是,这种私人性的经历就具有了对于时代的某种破坏性。第一次的惨痛摔跤留下的是痛苦的记忆,“到了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泥的滋味是一种怪怪的苦,叫人恶心欲吐!”之后的1974年,终于不再被“囚禁”在邢阿姨的禁闭室,和陈晓洁一起跑进了盛大的夏天,在阳光灿烂和麦浪滔天中感受自由;1975年,因为策划了“复仇之战”,当了一个学期的班长之职被撸掉了,还被勒令在全年级做检查,“我是一个灾星——这个巨大的阴影投进了我的内心!”而苏老太太对我的批评是:你到底对像你妈这样为国捐躯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生命的革命烈士们有没有思想感情?有没有阶级觉悟?在浸透着他们鲜血的土地上,你怎么连饭都吃不下了?你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怎么成长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怎么对得起生你的妈?!有你这样的儿子,你妈在天之灵怎么放心得下呀?!”1976年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却没有感觉变回旧社会,“这种心理让我觉得必然会有大的灾难发生,不发生就不像话。”终于后来公开的消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
在处处是国家宏大叙事的世界里,个体的生活都处在影子里,就像我对于“武文革”和“索索”名字的质疑,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体的体验、个体的命名、个体的生活,都无法逃离“武文革”背后的那个强大体系?所以要破坏,所以要自由,而对于“我”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成长性世界的开启,它是个体对私人生活的争取,而这种争取突出表现在我的性启蒙上。1974年,我住在了“六号坑”的常奶奶家,常红成为我性启蒙的第一个女人,五岁的我和常红睡在同一张床上,当我见证了常红被“八一”侵占,“活生生的最冰冷最残酷最丑陋的现实在我身边发生了”,而常红在受辱之后对我说的话是:“索索,你还想……摸小姨的奶奶不了?小姨现在已经……不干净了,也不金贵了,想摸你就来摸吧。”1974年,父亲又把我交给了邢阿姨,邢阿姨和大李叔叔要好,他们住在我的隔壁,当晚上传来“女人的呻吟和男人的喘息”,当那张大床在摇晃中变成摇篮,“我便在这富有节奏的摇晃之中甜然睡去了……”后来我还亲见了换衣服的邢阿姨,看见了她自制的花布裤衩和白色胸罩,当然更看见了身上雪白的赤裸部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目击一个女人的裸体,“心里的感觉怪怪的:有一种从很深的深处所发出来的痒,像是跳进去了一两只蟋蟀似的。”
后来还和阿姨有了“共浴”的经历,阿姨的手似乎在为我做一次中国式的“割礼”,“是把我从一个小男孩朝着男人的方向上狠推了一步!”也正是一种仪式的进行,我朝着男人的方向上继续前进,甚至变成了一种主动的成长,1975年我发现了“百草园”,爬到那棵香气四溢的香椿树上可以看到女厕所里的友人风景;后来和冯红军妈在一起,被她脖子以下丰腴的身体所着迷,“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正是在这一个女人身上,我的目光开始变得不再纯洁,开始有了‘贼意’……”到了1978年,在和父亲洗澡时,看到了父亲的男人身体,而自己那部位也“高高地硬了起来”,所谓发育,便是成为像父亲那样的男人的准备;后来在自己的家中发现了抽屉里的蕾丝花边胸罩,“捧到面前,用鼻子嗅着上面的味道,用嘴唇轻轻地与之发生接触,像得到一块骨头的小狗一般万分陶醉……”那是和父亲要好的“小谢阿姨”的物品;而到了1979年,习小羊通过私下里弄到了一本医学书,这本医学书成为了“性书”,我和他完成了“不可或缺的自我教育”……
在国家宏大叙事面前,个体的私生活是处在一种禁闭状态中,就像“我”成长所缺失的家和爱一样,就像我被改名叫“武文革”一样,当成长所需要的性教育也处在缺失的状态下,“我”便在一种争取中开始了成长,它既是私密的,也是合理的,它既是禁止的,也是自由的——伊沙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完成了个体意义上的命名,让“我”的成长趋向完整,所以这个“世界开始了”,既是一个时代畸形世界的开始,也是自我成长的私人世界的开始。但是伊沙在书写性教育的完整性、成长的合理诉求上,却又表现得太过了,常红、邢阿姨、“白骨精”白晓莹、冯红军妈、陈晓洁、小谢阿姨构成了“我”的性启蒙样本,他们用身体以及肉体打开了禁闭的门,但是“我”另一方面也主动打开了这扇门,甚至以“猎取”的方式窥视着女性身体,这似乎超出了某种道德约束,甚至在“我”十三岁的时候,从大部头的“黄宝书”里知道了一条逻辑:“人一发育成熟,就需要性交,性交得以存在,光明正大的理由是:繁殖。”于是十三岁的我和十四岁的习小羊一起学会了“干搓”;甚而至于一个名叫王梅的女人收我为“学生”,开始让我打开“女人之门”,“她在夜里在床上教会我的那些本事全是真的!令我早早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名男人,让我一次学会受用终生……”不仅超越了道德,而且也违背了法律,这样一门男人的必修课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存在?
世界开始了,世界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被打开,其实也缺少了所谓的批判意义,而伊沙似乎也沉浸其中,就像最后“今生今世的头一个女人”对我说的那样:“你……你要守住自己的秘密,不要对别人去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发现……这些都是人生中最美好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汉字中,在“中国往事”的叙事中,在压抑的时代中,当道德和法律之外的性行为成为秘密,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它在寻求补偿意义之外更是变成了一种畸形的成长,如那个时代,如那些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