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H73·2010709·0632 |
| 作者:(英)托马斯·莫尔 | |
| 出版: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 |
| 版本:1998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5.90元 | |
| 页数:134页 |
莫尔是当时一位有名的人文主义者,他在《乌托邦》中表现的理性和现实的精神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特点。尽管莫尔本人是虔诚的教徒,而且在死后四百年被天主教教会尊为圣徒,但《乌托邦》书中的思想,显然是人文主义多于宗教热忱。
 |
编号:H73·2010709·0632 |
| 作者:(英)托马斯·莫尔 | |
| 出版: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 |
| 版本:1998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5.90元 | |
| 页数:134页 |
莫尔是当时一位有名的人文主义者,他在《乌托邦》中表现的理性和现实的精神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特点。尽管莫尔本人是虔诚的教徒,而且在死后四百年被天主教教会尊为圣徒,但《乌托邦》书中的思想,显然是人文主义多于宗教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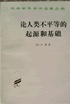 |
编号:B36·1980202·0425 |
| 作者:(法)卢梭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62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9.40元 | |
| 页数:239页 |
“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卢梭在1743年的威尼斯写下了自己对国家哲学的论断,作为一篇征文,卢梭大胆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政治学观点,揭示了人类作为政治人,与自然人相比所具有的进步与悲哀,以及恢复人类平等的“乌托邦”思想。本书另附有勒赛克尔对卢梭的介绍及哥尔达美尔、普列汉诺夫对卢梭学说的介绍。
你们都是毫无道理的人,你们不断地埋怨自然,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你们自已。
——卢梭《忏悔录》
1749年,当他步行到文新尼城堡的路上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时,他不是一个哲学家;1754年,当他在献给日内瓦国民议会的献词里喊出“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哲学家;甚至,1962年在他完成《社会契约论》的时候,他仍然不是一个哲学家。“在未使人成为人以前,决没有必要使人成为哲学家。”在一个有无数知识和谬见的现实中,在一个被情欲不断激荡的身体里,在一个灵魂已经变质的社会环境中,或者说在一个存在人与人不平等的世界里,作为“日内瓦公民”的卢梭是不会向哲学家靠拢的,对于他来说,向往自然法,愿意“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选择“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作为我的祖国”才是自己的理想国,才是成为哲学家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平等之下的自然状态,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仅仅是一种躲到圣日尔曼森林里去思考“实验”的乌托邦。
“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的知识的途径。”这是卢梭认为不幸的事情,而这个时代似乎并非如卢梭自己看见的那样,它甚至可以称之为“伟大”,在法兰西革命之前,一大批著作构成了一个等级的力量和统一战线,“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发表于1749年,狄德罗的《关于盲人的书简》和毕丰的《博物学》第一卷也同样是在1749年发表的。《百科全书纲要》是1750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和达兰贝尔写的绪言是1751年问世的;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也同时出版了。”在这个“产生伟大著作的时代”,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封建贵族;反对抵抗一切新思想的主要中心——教会的第三等级联合起来,这是他们发出的纲领,这是他们构建的哲学体系,而1749年以论文方式发表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1762年发表了《社会契约论》的卢梭,似乎在深刻的政治思想、辩证的实践思考上独树一帜,但是他显然在哲学方面远远落后于百科全书派,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他也受到了百科全书派中以狄德罗、霍尔巴赫为代表的前进派和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中间派的诟病,发展资产阶级的进步纲领和以卢梭为代表民主大众的利益发生的分歧绝非是简单的阶层利益的矛盾,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卢梭似乎还沉浸在他那个“日内瓦共和国”的荣耀里,沉浸在构筑的乌托邦空想里,甚至沉浸在自我忏悔的心灵救赎中。
撒谎、偷窃,以及流浪漂泊,甚至成为贵妇人的情人,在卢梭的生命体系中,他无法摆脱的是自己的现状,而这种现状又让他感觉到耻辱,在沙龙里,贵族们和大资产阶级,过着造成人民贫困的豪华生活,而卢梭感到自己就是人民。男爵霍尔巴赫有一天问卢梭为什么对他那么冶淡,卢梭回答说:“你们太有钱了。这些富人没有人心。他们是虚伪的。”就如他在《忏悔录》里说的那样,他们构筑的等级,他们享受的生活,都是因为远离了自然,那些痛苦正是自己造成的,“有一些人完善化了或者变坏了,他们并获得了一些不属于原来天性的,好的或坏的性质,而另一些人则比较长期的停留在他们的原始状态。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而在1749年之前,这只是卢梭一种个人痛苦,而在那个夏季在文新尼城堡路上的偶遇,则打开了卢梭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之门。第戎科学院的征文题目写在“法国水星杂志”上:“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还是起了改善风俗的作用?”社会进入的标记是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但是这种进步到底指向败坏风俗还是改善风俗?对于卢梭来说,进步带来的疑问正好是切入了自己对于社会的反思:“在读到这个题目的一剎那问,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我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变成了另一个人,是因为卢梭开始站在高处,他俯瞰着人类,俯瞰着社会,俯瞰着变化,而一切的起点和终点就是那个叫“人”的动物:“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这是卢梭在论文的“序”里表达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的知识更新和社会进入都将自己带向了一个“几乎不可认识的程度”,这是变质的自己,而这种变质是和原始状态背道而驰的,是和人与人之间本来的平等相悖的。卢梭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有两种,一是自然或者生理意义上的不平等,另一种则是精神上或者政治上的不平等,前一种不平等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而后一种不平等是“起因于一种协议”,一种人们同意或者认可而设定的。而卢梭把对不平等的论述看成是一种“实验”,他的实验议题就是:“倘若让人类自然发展的话,究竟会变才成什么样子。”
自然发展,当然需要自然状态中的生理,卢梭设置了一个“野蛮人”的范式,而站在野蛮人对面的是文明人。在自然状态下,野蛮人的身体是他拥有“自己所认识的唯一工具”,他可以通过身体的不同用途完成在自然中的生存,他和野兽搏斗,他防御敌人,虽然有幼弱、衰老和各种疾病等天然缺陷,但是对于野蛮人来说,生病也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自然,无人照看却别无指望。正是由于野蛮人的这种自然状态,所以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本能进行取舍,这个禽兽是一致的,“他所认识的唯一需要就是食物、异性和休息;他所畏惧的唯一灾难就是疼痛和饥饿。”在卢梭看来,野蛮人具有的是身体的疼痛,而不是死亡,“因为对死亡的认识和恐怖,乃是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后最早的‘收获’之一。”也就是说,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特有的恐惧,是对于欲望无法满足的恐惧。而在野蛮人那里,欲望或者等同于兽性,但是野蛮人的兽性是不会膨胀的,不会永不满足的,他没有所谓的恶,当然也不会有所谓的善,他具有人类的怜悯心,而这使得他在自然状态中代替了法律、风俗和道德,“而且这种情感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没有一个人企图抗拒它那温柔的声音”,这也是卢梭对于霍布斯“人天生是恶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人是邪恶的,因为他不知美德为何物;人从不肯为同类服务,因为他不认为对同类负有这种义务”观点的反驳。
 |
| 让·雅克·卢梭(1712年-1778年) |
而与野蛮人的自然状态相比,人类脱离了自然也就逐渐脱离了简朴、单纯和孤独,在健康上求助于精良的医术,在悟性上有了自由行动代替了本能,甚至开始有了服从或者反抗的自由,而更为可怕的是,人在自我完善化的要求下,“借助于时间的作用使人类脱离了它会在其中度过安宁而淳朴的岁月的原始状态;正是这种能力,在各个时代中,使人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谬误、邪恶和美德,终于使他成为人类自己的和自然界的暴君,这对我们说来,就未免太可悲了。”正是因为我们需要自我完善,所以求知,而目的是享受,正是因为知识,我们充满了理性,我们有了死亡的恐惧感,我们中有衰弱的、胆小的、卑躬屈节的人,有安乐而萎靡的生活方式,有各式各样的欲望,“其实这些欲望乃是社会的产物,正因为有这些欲望才使法律成为必要的。”所以有了道德、法律、风俗,从而代替了自然状态下的怜悯心,那种自然的单调不见了,出现了“人民的情欲和任意行动而引起的那种突然的、继续不断的变化”,出现了违反自然状态的思考,使沉思变成变质的人的一种属性,而这种属性也使哲学出现,而使人与世隔绝的哲学在一个受难者面前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死就死吧,反正我很安全。”
理性带来的思考和哲学,欲望带来的道德和法律,这些人类自我完善化的过程却恰好使人从野蛮人阶段走到了现代人阶段,也将人类从自然状态中带向了不平等的状态,而这些所谓人类的智慧正是不平等的起源,但是这只是在生理上的发展,“我已经指明完善化能力、社会美德、以及自然人所能禀受的其它各种潜在能力,绝不能自己发展起来,而必须借助于许多外部原因的偶然会合。”而卢梭所说的“外部原因”正是他在“第二部”继续展开的关于形而上学和精神方面的不平等基础。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卢梭从私有观念的产生出发,指出土地上的霸占和分配形成了新的不平等。“土地的耕种必然会导致土地的分配,而私有一旦被承认,也必然会产生最初的公正规则。”人的自我完善是寻找自尊的感觉,人变成了那些能供人使用的动物的主人,也成为那些对人有害的动物的降灾者,这是人类对于自然状态的第一次灾变,这促使了家庭的形成和家庭的区分,从而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争执和战斗。而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正是由于人需要别人的注意,又开始注意别人,在公众的重视中走向不平等,也走向了邪恶。
“随着观念和感情的互相推动,精神和心灵的相互为用,人类便日益文明化。”这种文明化虽然脱离了原始状态的悠闲自在,但是在卢梭看来,却是个人完美化的最好阶段,人类的自尊心作用下可以使人持续地幸福,所以这是人世真正的青春,“人类生来就是为了永远停留在这样的状态”。但是这种个人完美化的追求却永远不会止步,在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它也无可避免地“引向人类的没落”。
“自然的不平等,不知不觉地随着‘关系’的不平等而展开了。因此,由于情况不同而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效果上就更加显着,也更为持久,并且在同样的比例上开始影响着人们的命运。”尤其是土地制度上的私有制,使贫富差距拉大,“这样,因为最强者或最贫者把他们的力量或他们的需要视为一种对他人财产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按照他们的看法就等于所有权,所以平等一被破坏,继之而来的就是最可怕的混乱。”富人的豪夺、穷人的抢劫以及一切人毫无节制的情欲,“扼杀了自然怜悯心和还很微弱的公正的声昔”,所以人在悭吝、贪婪和邪恶中,在最强者的权利和先占者的权利之间发生无穷尽的冲突中,人类的不平等最后变成了能以战斗和残杀。
当然这是社会没有约束的极端表现,而在人类的自我完善中,必然会产生规则,这个规则包括法律,包括制度,包括政府。在卢梭看来,社会和法律的起源就是“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消灭了天赋的自由,“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而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而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不使自己受奴役,所以人民需要首领,需要制度,这是全部政治法的基础,而这样的基础造就的却是专制政治,也就产生了专制权力。在卢梭看来,政治法相对于自然法,是社会进入不平等的标志,而在人类社会中,不平等的三个阶段便出现了:“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也就是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因此,富人和穷人的状态是为第一个时期所认可的;强者和弱者的状态是为第二个时期所认可的;主人和奴隶的状态是为第三个时期所认可的。”起源于自我完善化,终结于专制政治,在人类的文明化过程中,一个封闭的圆圈被划定。从自然状态的野蛮人,到私有制出现后的文明人,再到有专制政治的官员和人民,卢梭绘制了不平等的曲线图:“根据我的说明,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
当人类的发展带动了事物的演进,但是这种演进的最后结果是权力代替了暴力,自然服从了法律,而那些强者为弱者服务,人民牺牲世纪幸福来换取安宁的“奇迹”只是一种空想,而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哲学家一直没有能力从中站出来,不管是人在自然状态下的非理性、无思考和无法律约束,还是在私有制和专制政治下的不平等,哲学似乎从来没有帮助人从危险中解救出来,当然哲学家也没有被人从床上拖起来。而对于卢梭来说,完成了从生理和形而上学构建的不平等路线图,依然只是为了建立他的乌托邦,“如果有谁能很好地解答下面的问题,我便觉得他配称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为了达到认识自然人的目的,必须作什么样的实验呢?而在社会中,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作这些实验昵?”认识自然在卢梭看来是成为当代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的基础,是成为哲学家的实验目的,所以他才会为了描写原始野蛮生活,竟独自一人躲到圣日尔曼森林里击思考,这是成为哲学家的实验,而这个像是完全脱离实际梦想就是卢梭式的乌托邦式。
而身为“日内瓦公民”,卢梭是希望建立一个自然人的王国,而这个王国需要的是“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所以他在1754年《献给日内瓦共和国》的文章中构建了他自己的那种平等思想,这是拥有最高智慧的国家:“可以把一个国家里的平等和不平等以最接近自然法则并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加以适当的调和,从而既能维护公共秩序又能保障个人幸福。”这是产生共同幸福的国家:“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益,因之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都只是为了共同的幸福。”这是消除恐惧的国家:“它幸运地没有强大的力量,因之没有征服他国的野心,同时更幸运地由于它所处的地位也没有被别国征服的恐惧。”那里是有着完善法律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很满意自己有权批准法律;他们可以根据首长们的提议集体地来决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建立一些受人尊重的法庭;慎重地划分国家的省份和县份;每年选举公民中最能干、最正直的人员来掌管司法和治理国家。”
但是这样的”日内瓦共和国“对于卢梭来说也只是一个理想国,在这个时期,卢梭并不知道日内瓦共和国的真实性质。等他在《爱弥尔》发表之后,才对日内瓦共和国的政府认真地加以研究,那时他改变了看法,“他们作了专制权力的奴隶,他们毫无保障,仅仅二十五个专制者就可以任意处置他们。”这是理想国的坍塌,这是乌托邦的解构,对于卢梭来说,这仍是“一个孩子命令着老年人,一个傻子指导着聪明人,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的社会,违反自然法的现实,也使得孤独、单纯和充满忏悔意识的卢梭永远无法成为一个从床上拖起的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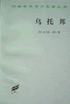 |
编号:W45·1970627·0379 |
| 作者:(英)托马斯·莫尔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82年7月第二版 | |
| 定价:7.40元 | |
| 页数:163页 |
托马斯·莫尔以旅行家希斯拉德的口构筑了“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这个“最完美的国家制度”里财产公有,人人劳动,公民有劳动、享受卫生健康和教育、自由学术研究的权利。这并不是托马斯·莫尔躲在16世纪的书斋里做的幻想,在中世纪封建专制和初期资本主义的掠夺中,莫尔进行着对恢复人本主义的反抗。当然,1516年的《乌托邦》只是他寄托自己理想的工具,他的使命并不是只是向人们展示自己心中的理想,而是希望通过宗教来实现社会的改良与进步。1535年7月,托马斯·莫尔的头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就应该使得全世界都采用乌托邦国家的法制,若不是那唯一的怪魔加以反对,这怪魔便是骄狂,它是一切祸害之王,一切祸害之母。
唯一的怪魔是骄狂,是祸害,是欺凌和嘲笑,它不是夸耀财富的女神,而是“从地狱钻出来的蛇”,盘绕在人们的心上,阻碍人们走上更好的生活道路。而只有乌托邦拔掉和消除了这一怪魔,“铲除了野心和派系以及其他一切罪恶的根源”,没有内战,没有纠纷,没有危险,没有毁灭,更没有他国的扰乱。但这是“无何有之乡”的乌托邦,这是拉斐尔的乌托邦,这是国家理想盛世的乌托邦,这是遭风暴失事而被冲上岸的乌托邦,这是第四次航程要塞上的乌托邦,而所有的乌托邦都在托马斯·莫尔的世界之外,他只是听说,只是转述,只是引用,只是杜撰。但是在没有亲历乌托邦的现实里,他依然看到了那骄狂的怪魔,那从地狱钻出的蛇,那带来野心、罪恶、纠纷和毁灭的怪魔,将这位“最著名和最博学的伦敦公民及行政司法长官”吞噬,而这种吞噬也是理想的覆灭,是哲学的死亡,是生命在微笑中终结。
这是矛盾的时代,“在他的思想中仿佛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矛盾,并构成一个独特的、统一的思想体系。”这矛盾是个体的抱负和现实的矛盾,托马斯·莫尔所追求的生活是不受羁绊和闲适,他厌恶宫廷生活,厌恶君主,当然更憎恨专制,但是却成为英国亨利八世的行政司法长官,这个“经过千难万难”才被逼近宫廷的职务或许是托马斯·莫尔的另一种政治抱负,但是英国的现状又让他感到痛苦,这里有着对盗窃犯的严刑,有着大臣的随声附和与献媚,有着国王的惰与傲,借用拉斐尔的话说就是:“这种傲慢、荒谬而顽固的偏见,我曾在别的国家屡见不鲜,有一次也在英国见过。”当然更主要的是国家私有制的存在,有着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躁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对于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的时代来说,英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一种怪魔,侵吞着政治理想。所以托马斯·莫尔只是用一种春秋笔法来映射英国社会的不合理,并提出了一种理想的制度。
在《乌托邦》里,他不是伦敦公民,也不是行政司法长官,而是拉斐尔·希斯拉德,一个精通希腊文,爱冒险,竭力搞哲学的“杰出人物”:“这位拉斐尔——这是他的名字,他姓希斯拉德——不但精通拉丁文,而且深晓希腊文。他对希腊文下的工夫比对拉丁文还要深些,因为他竭尽精力去搞哲学,他觉得关于哲学这门学问,拉丁文中除了辛尼加和西塞罗的一些论文外,缺乏有价值的东西。”而他的内心充满着冒险精神,他“请求甚至要挟韦斯浦契同意让自己成为留在第四次航程终点的要塞上二十四人中之一”,从而有机会游历到制度优越的国家,有机会登临乌托邦,有机会描绘这个理想的国家。而托马斯·莫尔只不过是拉斐尔经历的转述者,“所以我的文体越是接近他的随意朴质风味,越是接近真实,而只有真实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注意,也实际上是注意了的。”一是要保持谈话的真实,二是仅仅是转述,“在宣传乌托邦国家这点上,我当然不愿意比他抢先着笔,以致夺去他的述的新鲜花朵和光彩。”也就是说,托马斯·莫尔一直努力去除自己的影子,将乌托邦有关的制度全部变成拉斐尔的故事,而托马斯·莫尔不仅站在拉斐尔的故事之外,甚至还对拉斐尔的讲述提出质疑。
 |
| 托马斯·莫尔:微笑着死去的理想主义者 |
对于拉斐尔的聪明和勤奋,托马斯·莫尔提议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伟大国王的谋臣”,但是拉斐尔向莫尔指出了两方面的错误,一是从自己来看没有所谓的才能,“即使那么有才能,在打乱我的安静生活的同时,我并无从为公众谋福利。”也就是拉斐尔所拥有的才能并不是治理国家为公众谋福利的才能,而更为关键的是,在拉斐尔看来,国王是不伟大的,“他们更关心的,是想方法夺取新的王国,而不是治理好已获得的王国。”所以在王宫里,处处充满着傲慢、荒谬而顽固的偏见。而另一方面,以哲学家自居的拉斐尔也认为,哲学是和统治者无缘的,他引用柏拉图关于哲学家躲雨的故事说,“哲学家知道,如果他们自己外出,毫无好处,只是和其余的人一样弄湿身子。因此,如果少他们本人安全,他们就觉得满意,这样,他们便留在家中,对于医治别人的愚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对于不管是政治上的国王、大臣,还是一般的被雨淋湿的平民百姓,哲学家都是无能为力的,都不应该参与国家管理。而当拉斐尔提出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公平分配,才能使人类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而托马斯·莫尔的质疑在于“我有相反的看法。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因为我无从想像,当人人同处在一个水平面上,行政官在他们中间怎能有什么地位。”也就是说私有制消除不公平的同时,也消除了人们之间的差距,那还有谁会去努力奋斗,还有谁生产更多的物质?而拉斐尔的观点是:“因而,你若是到过乌托邦,你可以当之无愧地承认,除掉在那儿,你从未见过生活得秩序井然的人民。”
托马斯·莫尔用这样的曲折表达来构建他者的“乌托邦”,这正反映了他矛盾,甚至想逃避的心态,而这种矛盾也使他的生存呈现出一种悲剧性的意义。但在托马斯·莫尔这里,建构的欲望大于逃避,对乌托邦的向往大于对现实的妥协,尽管在形式上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转述者,站在拉斐尔文本的后面,但是他还是用一种严肃的态度构筑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这是一个庞大的制度“幻想的方案”,这是“一个独特的、统一的思想体系”,他使用的当时学术界通行的拉丁语,但是在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上,都是托马斯·莫尔的杜撰,“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本身就是据古希腊语虚造出来的,六个字母中有四个元音,读起来很响,指的却是“无何有之乡”,不存在于客观世界。而拉裴尔的全名应为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拉斐尔虽然是借用教名,但是希斯拉德是用希腊语构成,大意可能为“空谈的见闻家”。而乌托邦岛东南的“阿科里亚人”也是用希腊语杜撰,意谓无何有之乡的人,其构成类似“乌托邦”的意义。乌托邦国王乌托普征服的阿布拉克萨岛的名字也是希腊字母,代表数字365,等于全年的天数,寓有神秘意味。
杜撰的名字,也就是被书写、被命名的名字,这是托马斯·莫尔的世界,这是他创造的理想国,所以拉斐尔这个影子的存在是托马斯为了叙述更为真实更为可信,也为了规避矛盾和风险,所以乌托邦看起来是真实存在的,是一种可以抵达的现实,在几乎完全是拉斐尔叙述的第二部,一个具体、可见的理想盛世被展开了。这里有具体的地形:“乌托邦岛中部最宽,延伸到二百哩,全岛大部分不亚于矛这样的;宽度,只是两头逐渐尖削。从从一头到另一头周围五百哩,使全垒岛呈新月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哩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大水。”这里有具体的城市:“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无不巨大壮丽,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而“亚马乌罗提作为全国中心的一座城,其位置便于各界代表到来。它被看成是主要的城,亦即是首都。”这里有具体的人,“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四十人,外加农奴二人,由严肃的老年男女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每三十户设长官一人,名飞拉哈。”而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理想,最主要的体现是财产公有、生产劳动、务农为本、城市规划、卫生健康、学术研究等。
在乌托邦,财产公有是最大的特色,在城市里,每家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的格局,让每扇门都可以轻易推开,而任何人可随意进入,“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而且,每户人家“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对于每一户来说,户主来到仓库觅取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所需要的物资,领回本户,不付现金,无任何补偿。而在乌托邦,商品在全部居民中均匀分配,任何人不至于变成穷人或乞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乌托邦就是一个大家庭,甚至他们将这种“公有”延伸到其他岛屿:“他们将剩余运销到别的国家,有大宗谷物、蜂蜜、羊毛、亚麻、木枕大红和紫色染料、生皮,黄蜡、油脂、熟皮,以及牲口。他们把上述产品七分之一送给这些国家的贫民,余下的廉价出售。”在乌托邦,由于没有贵贱,所以那些金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耻辱的标记,“所以别的民族对于金银丧失,万分悲痛,好像扒出心肝一般;相反,在乌托邦,全部金银如有必要被拿走,没有人会感到损失一分钱。”他们只是在出于军事的目的才储存金银。所以废除私有制是乌托邦最大的实践,拉斐尔说:“我觉得,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除非一切最珍贵的东西落到最坏的人手里,你认为这符合正义;或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繁荣——这少数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穷苦不堪了。”
而在职业上,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除此之外,他们“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正是这些职业,使他们能安于现状,而那些优秀者可以指定做学问,在这些有学问的人当中选出外交使节、教士、特朗尼菩尔,乃至总督。而乌托邦的政府也不强迫多余无益的劳动,而在乌托邦,“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他们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快乐。”所以构成乌托邦人幸福的就是快乐,这种快乐“不是每一种快乐,而只是正当高尚的快乐”。而他们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而上帝创造人就是为了使其能这样的生活。自然是乌托邦的上帝,在乌托邦,不论是崇拜日神,还是崇拜月神,或者是崇拜另外的星辰,甚至是“道德或荣誉著称的先贤,把他当做神”,但是绝大多数人只信一个神,“这个神是不为人知的,永恒的,巨大无边的,奥妙无穷的,远远超出人类的悟解的,就其威力说而不是就其形体说是充塞宇宙间的。”这个神是父,是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和老死,而他就是自然本身,是“密特拉”,所以对神的崇拜就是对自然的尊敬,对自然的尊敬当然就是对幸福和快乐的感悟,“他们认为,探索自然,于探索中赞美自然,是能为神所接受的一种礼拜形式。”而因为认同于自然,所以消灭了私利,“自然教你留意不要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损害别人的利益”,所以在乌托邦,没有在国民利益之上的个人利益,“一切归全民所有,因此只要公仓装满粮食,就决无人怀疑任何私人会感到什么缺乏。”
当然,在这些良好的制度下,也还有罪犯,而乌托邦对于罪犯的处置并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处以极刑,而是让他们成为奴隶,“他们的奴隶分两类,一类是因在本国犯重罪以致罚充奴隶,另一类是在别国曾因罪判处死刑的犯人。”除此之外,还有在另一国家无以为生的苦工,他们是自愿到乌托邦来过奴隶的生活。在乌托邦,努力从事的是又费力又肮脏的全部贱活,这是对他们的惩罚,乌托邦人认为这种处罚既能够使犯人害怕,又有利于国家,因为这样做“胜于匆匆处死犯人,使其立刻消灭掉”,而他们的劳动也可以作为反面教员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阻止别人犯罪。
这里有公平分配的食物,有对病人特殊照顾的医院,有正当高尚的快乐,而这里没有贫富差异的劳动,没有对外的征战,没有对土地的占有,没有私有制,这就是乌托邦,远处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所有的虚构,所有的杜撰,对于托马斯·莫尔来说,是希冀成为一种现实,所以在拉斐尔讲述之后,托马斯·莫尔发出的感叹是:“可是我情愿承认,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无法实现的困窘在托马斯·莫尔1516年12月4日前后写给伊拉斯莫斯的信中成为一个虚幻的梦:“我的乌托邦国民已经推举我做他们的永恒君主。我仿佛已经庄严地向前走去,头戴麦编成的王冠,身上的圣芳济修道士袈裟引人注目,手拿谷穗做的节杖,我周围是一群亚马乌罗提城的达官贵人。”甚至还邀请伊拉斯莫斯到乌托邦去做客,“我将充分保证:在我的宽大统治下的人民,将把你当做他们的国王所最亲爱的人而致以应得的敬意。”但是莫尔知道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当曙光升起的时候,梦也就碎了,“我从王位上被赶下来了,我回到自己的禁闭室里,就是说,回到我的法律事务中。可是当我想到真实的王国并不更持久些,我就引以自慰了。”
这其实是托马斯·莫尔无法摆脱的悲情,这个“幻想的方案”虽然“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矛盾,并构成一个独特的、统一的思想体系”,而托马斯·莫尔也凭借这本书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在些后来的荣誉并没有改变当时的英国社会,也没有改变他身为人文主义者、伦敦商界的宠儿、以及英吉利王国大法官的命运,由于触及“具有模范君主的一切才德而著名”的英王亨利八世的宗教利益和私人生活,所以托马斯·莫尔被判有罪,判词称:“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泰柏恩行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但是最后英王命令只是把莫尔杀头,以代替刑罚。莫尔听见后指出:“天呀!救救我的朋友们免叨这样皇的恩惠吧!”
“死后没棺材,青天做遮盖”,以及“上天堂的路到处远近一样。”这是在《乌托邦》里拉斐尔的生死观,而这种将生死付之度外的态度也成为托马斯·莫尔的人生写照,当被处以死刑的时候,这位“总是愉快而和蔼可亲”的完美主义者以一种微笑的方式化解死亡,当他告别家人,自己用头巾扎住眼睛,并且对刽子手说:“我的颈子短的,好好瞄准,不要出丑。”最后,莫尔的头终于挂在伦敦桥上示众。而在这时候,他抛却了伦敦市民、行政司法长官的头衔,他扔掉了那种让他厌恶和矛盾的宫廷生活,当然他也脱去了以拉斐尔的名义覆盖在《乌托邦》上的遮羞布,这一刻,他就是乌托邦人,就是理想盛世的公民,就是追求正当高尚快乐的乌托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