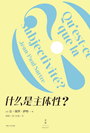 |
编号:B83·2200514·1649 |
| 作者:【法】让-保罗·萨特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49.00元当当26.60元 | |
| ISBN:9787208144453 | |
| 页数:232页 |
《什么是主体性?》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1961年12月在罗马应葛兰西学院之邀讲学的记录整理而成。当年的课堂记录尤其是萨特与现场听众讨论的部分,五十多年后重获发现,2013年在法国出版,主体为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性”的报告,同时收入数位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Enzo Paci, Cesare Luporini,Galvano Della Volpe)与萨特讨论的文字。并由Michel Kail与Raoul Kirchmayer作序言“意识与主体性”,跋文是詹明信的“萨特的现实意义”。“主体性”是萨特强调的重要概念之一,“什么是主体性”这一问题因为与当代批评理论中针对“主体”的讨论相关而重获重要性。自1930年代以来,主体性问题就困扰着萨特,萨特认为,正是人的主体性给了我们在生活中选择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因为并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客观的价值,也不存在确定的决定我们是谁或我们是什么的本质,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主观的标准、主观的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本质,而这些只能从一个主观的视角来拓展和理解。
《什么是主体性?》:总是保持在客体的状态
一个反犹主义者,厌恶犹太人的人,是犹太人的敌人,但反犹主义者通常不会公开说自己厌恶犹太人。
——《马克思主义和主体性》
一个厌恶犹太人的人,一个犹太人的敌人,当成为“反犹主义者”的时候,他为什么不通常说自己厌恶犹太人?一种身份在隐秘状态中,但是不公开说的隐秘状态,是不是在自我意识上也给予了一种否定?不公开说自己厌恶犹太人,另一种存在的状态是公开承认自己厌恶犹太人,在这种对比中,萨特似乎就区别了两种反犹主义。
这种不公开说自己厌恶犹太人的反犹主义者,他具有的反犹主义被萨特称之为“作为主体性的反犹主义”,而另一种则是“作为反思的反犹主义”,前一种是“作为把握犹太人这个客体的主体的反犹主义”,把握了犹太人这个客体,亦即消灭了主观本身,它只在主体性意义上是反犹主义;后一种则是“把自己本身把握为反犹主义的客体”,也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客体——这种把自己把握为客体的行为便具有某种唯心主义特征,天文学家发现星星,是在星星和天文学家之间建立了认识关系,但是天文学家不会改变星星,如果把天文学家变成了可以对星星进行某种改变的主观性存在,把自己对星星的改变变成了这种改变的客体,那么这便是唯心主义。
主观的认识,并且在主观的认识中把自身把握为客体,这种唯心主义是反思性的,萨特更直接地举出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工人他此前是无意识的反犹太主义者,但是当他具有反思性的时候,他的认识就完全改变了被认识的客体,于是他面临着一种抉择:要么不再接受自己是社会主义工人、共产主义工人,要么不再接受自己是反犹主义者。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对主体身份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对自我的认识的改变——他已经在一种把自己当成客体的反思中成为了唯心主义者。回到作为主体性的反犹主义,当把握了这个犹太人客体的主体,具有的反犹主义,在萨特看来,就是因为消灭了这种主观本身的能力,也就是在非反思的意义上,“本身对自己的反犹主义并不自知。”
“非知”是萨特对于主体性认识使用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客观性,它是由“某种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支撑着”,不仅没有被认识,在某些情况下,对它的认识还会妨碍行动,反犹主义者如果公开说自己厌恶犹太人,就会妨碍他的行动,所以萨特把这种认识称为“非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系统,出于某些我们将要考察的原因,非知作为它的构成部分而嵌入这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不再发展自己,不再以超越性而是以内在性来定义自身。”这种内在性定义自身在偏盲症患者例子中也具有这样一种客观性:病人并不是因为丧失了一半的视觉区域,得了一种当时无法治愈的毛病才变成偏盲症患者的,病人之所以变成偏盲症患者,“是因为他把自己造成为偏盲症患者,因为他通过把这种缺陷整合到总体当中,从而在内部保持了这种总体化。”在这里,其实一方面凸显了客观化的这个“非知”的存在,“非知状态对于偏盲症患者的这种行为来说是根本性的,他只是做他所做的,他并不理解自己所做的。”同时也引出了关于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要成为”——“主体性之所以根据定义是非知,是因为个体或有机体‘要成为’其存在。”
两个概念是结合在一起而具有总体化意义的,但是“非知”是一种客观化认识的前提,只有“并不理解自己所做”便不会趋向于唯心主义,这是一种在主体性层面上“对自我的非认识”。但是当萨特举例说反犹主义者的时候,这种客观性的“非知”却变成了“不公开说”,不公开说的含义是主观上的拒绝,是一种刻意的回避,它根本不应该是一种“作为把握犹太人这个客体的主体的反犹主义”,所以并不具有“非知”的意义,甚至这种“不公开说”就是一种反思,就是在建立认识中概念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就像天文学家改变了星星的存在——非知是一种对自我的非认识,而不是对非自我的认识。
实际上,萨特之所以提出主体性具有“非知”的特点,他所针对的就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观念,他的“客观可能性”概念。1961年12月,萨特应意大利葛兰西学院之邀在罗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主体性的报告,在这场报告中,一开场萨特就表明了自己的抱负,那就是将主体性置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以重新赋予它一度失去的活力,“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内的主体性难题,因为它涉及的,正好是从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真理出发,探讨主体性是否存在,主体性是有某种利益,抑或仅仅是人们能够在对人类发展的宏大辩证研究之外获得的一系列事实的问题。”一开始就把这个主体性问题视作是“难题”,他所言及的便是卢卡奇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物化和偶像化概念,谈及了无产阶级革命对经济关系的改变,在实践层面上,这种资本过程带来的变化,这种阶级斗争带来的概念似乎把主观的现实抹除了,而卢卡奇在阐述这些改变以及革命的未来时,产生的是抛弃主体的辩证法,“像卢卡奇这样的人,会根据一种客观的辩证法,提出一种关于完全客观的阶级意识的理论。”但这种客观主义在萨特看来却是唯心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发展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客观主义为什么会成为唯心主义?就是因为当客观主义被赋予了一个神圣地位,所欲偶的主体性便消失无踪,于是客观主义变成了唯心主义,“它可能是一种辩证的唯心主义,人们在这种唯心主义中会从物质条件出发,但它终究是一种唯心主义。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永远不可能达到一种真正的自我意识,但是却没有被无产阶级放入到这个改变的现实中,没有把无产阶级当成消灭资产阶级整个过程中的当事人,而正是无产阶级通过劳动现实,“走向对阶级意识的总体把握”。萨特引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的一段话,“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把什么想象为自己的目标。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实际上这段话的重要意义是提出了“什么是无产阶级”这个本质问题,也就是当无产阶级成为消灭资产阶级的当事人,这个成为当事人的过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过程本身就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被忽视的主体性难题,而主体性的一个核心思想便是:它是一种内在活动,一种内在性的系统——而不是与主体的直接关系。
但是主体性必定是和人有关,萨特重新审视主体性这个难题,也只是为了“让我们回到完整的人”。从青年马克思的文本中,萨特认为他用三个词定义了完整的人,那就是需要、劳动和享受,这三者定义的是一个“实在的人、实在的社会、环境的物质存在与并非其自身的实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是一种对关系的定义,而不是对主体的定义,而在这种关系里,人的实在性是一种超越性、彼岸性的东西,是某种外在于它并在它面前的东西的联系。与外部存在的联系并成为超越性、彼岸性的存在,就需要有种“客观化”,萨特认为,劳动就是对生活的再生产而进行的客观化——在这种再生产进行的客观化里,作为主体的人也同时进行着客观化,所以萨特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是什么在自我客观化?
萨特区分了两种外在性,一种是内部的外在性,或者说是此在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的身份被冠上了有机的身份,就是把人当成是实践的生物有机体,是身心的统一体,这种外在性是以死亡作为终结标志的;第二种则是彼处的外在性,是有机体为了维持自身的有机身份,“在自己面前所发现的作为劳动对象、作为需要和生存手段的那些东西。”正是这种外在性有着一种自我客观化的需要,所以它以一种内在性来定义自身,这种内在性是“非认识”的,即“非知”,它是完全区别于那种客观主义的认识——客观主义的客体已经不是客观存在,它是一种介入,一种行动,一种带着价值判断的存在,一种与整个共同体的关系,甚至是对未来的假设,而在主体性的“非知”中,唯一的客体就是那个具有主体性但非知的纯粹自我。
因为主观的认识总是在改变着客体,所以不在反思中改变客体就意味着在非知中保持主体性,“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既能谈论主体性而又不把它变成一个客体呢?”主体性的外部,是一种被构成的客体,所以它具有客体的性质,但是和劳动的再生产一样,在非知之外,它还有“要成为”的总体化需求,萨特认为,在一个内在性的系统中,“以要成为的形式,把无论什么外部的改变内在化,并以外部特殊性的形式使之重新外在化时,就存在着主体性。”第一要内在化,第二要重新外在化,这个过程就是“对有机能量的强制分配”,就是重新总体化。萨特认为,重新总体化是不断进行的,而且是在不知道情况下进行的,主体性在两个方面进行着总体化,一个是过去,一个则是阶级存在,不管是对过去的总体化,还是对阶级存在的总体化,主体性在非知中“要成为”,就必须保持一种恒定性,而这种恒定性便是:重复。
主体性是一种重复的存在,但不仅仅只有重复,还有创造,“创造的材料,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就是主体性。”在重复和创造之外,还有投射,“在一定的、直接的、总是向着外在性存在超越的关系中的重复一创造”。这三种本质特征在萨特看来,都是主体性的本质表现,那就是必须从外部来认识自己,在外部的内在化中进行总体化,“如果它从内部认识自己,它就死了。”从内部认识自己,无非也是一种唯心主义,萨特否定这种不内在化的内部,因为这种内部的自我仅仅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强化,它甚至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客体,“从一个群体或一个阶级真正获得对自己是什么的意识,并同时获得阶级意识(这是一回事)的时候开始,它就把自己看作客体,以便能够通过考虑自己的客观限制并利用这些限制来行动。”而这正是萨特批判的卢卡奇的思想,在他看来,卢卡奇可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肯定表达过这样一种想法:“一个人对自己来说越是客体,他就越是主体。”
主体的客体化,是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有着从内部开始的自我认识,当主体变成了一种在反思中把自己当成客体的存在,就取消了主体性,“我们之所以能想象一个没有主体性的社会,不是因为主体性不存在了,而是因为它总是保持在客体的状态。”所以在这场报告之后的讨论中,萨特依然反复强调这个观念:主体性保持着客体的状态,在客观化中进行着内在化和在总体化,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我们活着”,“主体性就是活出自己的存在,我们活出自己的所是,活出自己在社会中的所是,因为我们没见过人的其他状态。”而每一个个体,要活出“所是来”,都是整个社会的化身,他甚至举例具有主体性的文学创作,他认为《包法利夫人》就是“真正的小说”,它具有客观的描绘,它以自我投射的方式具有了客观性,它使主观和客观具有同一性,三者结合才是真正的小说,才是具有主体性的小说,“在我看来,完全客观的小说,是一种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
我们活着,如其所是地活着,这或者就是达到了“让我们回到完整的人”的意义,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目标,在现实意义上,这就是主体性的回归,“在今天,阶级斗争被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上,而这激发了一种就像‘任何人对所有人的直接控制那样’的‘需要的人道主义’。”从这个目标出发,抛弃客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抛弃客观可能性概念,抛弃客观的阶级意识,在重复、创造、投射的总体化中,在“保持在客体的状态”发挥主体性意义:“因此我们断言,在斗争的过程中,主观的环节作为客观环节内部的存在方式,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辩证发展中是绝对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