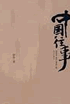|
编号:S29·2181103·1515 |
| 作者:伊沙 著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当当21.10元 | |
| ISBN:9787506391047 | |
| 页数:400页 |
“标准诗丛”之一。 伊沙,诗人、作家、批评家、翻译家、编选家,他的口语诗改变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某种方向。《一沙一世界》遴选著名诗人伊沙1988-2015年不同时期代表作品,共分三卷。第一卷“诗选”,收录了诗人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短诗代表作,如《车过黄河》、《江山美人》、《结结巴巴》、《酒桌上的谎言》、《腊八节》等;第二卷“长诗”,收录了《蓝灯》一诗;第三卷“文选”收录了伊沙写作与口语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文献、资料及序等,包括《饿死诗人,开始写作》《晨钟暮鼓》《口语诗论语》等。 精当的选本,与内容相膺的装帧形式,都让本书成为阅读伊沙的首要之选,也让本书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必然典藏。
《一沙一世界》:我的语言是裸体的
在《等待戈多》的尾声
有入冲上了台出乎了“出乎意料”
实在令人振奋此来者不善
乃剧场看门老头的傻公子拦都拦不住
窜至舞台中央喊着叔叔
哭着要糖“戈多来了!”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等待戈多》
这里是实验剧团的小剧场,这里正在上演“老掉牙的剧目”,这里的观众不多,剧场、舞台、观众构成了一种在场,而《等待戈多》当然也是一出“在”的剧目,所以戈多来不来并不重要,甚至不来的戈多也是必然的“在”——不来的戈多是无,无而在,便是等待的全部意义。但是当尾声时,那个剧场看门老头的傻公子闯入了剧场,登上了舞台,并且说出了“我要糖”之类的话,那个本应存在的“在”在有中被解构了,甚至根本不算解构,而是破坏,破坏了剧目应该有的实验性,破坏了无的等待感,破坏了一种经典式的演出。
当然,伊沙也一定在舞台之下,一定在观众之中,一定先是等待,继而是“出乎意料”,但是很有疑问的是:伊沙一开始是不是在等待中“犯困”?会不会在傻公子出现之后和其他观众一起“起立热烈鼓掌”?这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导向两种反应:如果是等待中的犯困,那么他坐在观众席上是认可“等待戈多”本身具有的解构性,也就是说,他来这里就是为了体验“等待戈多”的无,一种后现代的演出,像是行为艺术般,把“等待戈多”从剧本意义变成了观感体验,甚至观众的等待和犯困都成为“等待戈多”的一个文本。如果是因为看到傻公子闯入其中,代替了不出现的戈多而出现,从而起立热烈鼓掌,那么“等待戈多”本身应有的等待感和虚无性就荡然无存了,一种意外的闯入破坏了文本,戈多成为了舞台之外的存在,即使最后在诗歌里成为“戈多”,也绝非是一种建构。
等待戈多是把无看成有,等待的意义就是让自己进入经典文本并成为文本的一部分,显然伊沙没有走向第一个方向,而是以解构的方式让戈多变成一种真正的无,并让傻公子的出现完成解构的高潮,而伊沙在观众席上,享受这份高潮,起立鼓掌甚至大声叫好。伊沙像是一个双重的解构者,“等待戈多”而没有戈多是第一层解构,这是文本自行发生的动作,它本身是解构的经典,在伊沙那里变成了一种“传统”,而又有把这个经典的解构解构了,也就是把视为实验剧的“等待戈多”文本解构了,把传统解构了,从而获得了快感,而现在在这双重的解构下带来另一个问题是:解构的解构是不是还是解构?或者傻公子是不是另一个戈多?
这个问题,其实暗含了一个逻辑:在“全体凄厉热烈鼓掌”之外是不是还有不鼓掌的观众?实验剧场、老掉牙的剧目,以及出现的“戈多”都在伊沙解构的文本里,而在文本之外还有另外的观众,他们阅读这一首诗,阅读“等待戈多”背后的伊沙——作家出版社的《一沙一世界》,400页的“伊沙集”,标准诗丛系列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文本,而我自然是其中的观众。精装、硬皮的诗集,仿佛是对于经典的一种预设,而我就是在等待中打开了书页,甚至在阅读方式上也开始了某种颠覆——从第三卷的“文选”开始阅读,327页的《饿死诗人,开始写作》是起点,仿佛以等待的方式让伊沙真正写作的诗歌在后面露面,或者从后向前的阅读中,真的能够有一种“戈多来了”的惊喜感。
“饿死诗人,开始写作”仿佛就是伊沙的一次宣言,1993年,距离收入其中的第一首诗歌已经过去了5年,这五年,专注于中国口语诗写作的伊沙应该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所以他会发出“凭什么非要有一个文学主宰的时代?”的质问,所以他会否定“穿长袍马褂的‘现代派’和哭错坟的主儿”,所以他会鄙视“像诗”的诗作,所以他会舍弃“站在原地思考诗歌终极意义”的诗人,而他在5年的实践中让自己进入了诗歌的后现代,在后现代中“饿死诗人”,而自己却依然写着“和灵魂有关的东西”——“我已‘自在’,您认为我在‘反讽’,我认为我在‘反反讽’。”
“反反讽”像极了对于“等待戈多”的态度,后现代意义中的戈多本身就是反讽的符号,但是却让人等待,让人犯困,所以伊沙用口语诗解构“等待戈多”,达到“反反讽”的双重解构意义,而这便是他所说“饿死诗人”时代的到来:没有什么诗歌的终极意义,没有什么现代派,没有什么“世间一切皆诗”,更没有作为一种姿态而被人摆弄的“实验”,有的只是从无产生的诗,只有在严肃意义上“玩”的诗,只有对“真实”具有真实想象力的诗,而所有I一切的目的在于给诗歌本真的状态:“我不为读者写作,但我不拒绝阅读,更不拒绝误读。我的实验是为阅读的实验,目的在于激活诗歌。”
不为读者而写,却提供了阅读的文本,不是摆弄姿态的实验,是激活诗歌的颠覆,所以伊沙说:“我的语言是裸体的。”裸体而没有束缚,裸体而呈现本真,裸体而激发诗意,裸体而饿死诗人,反反讽,反修辞,反知识分子写作,反形而上学。而伊沙的语言的裸体主义其实就是指他的口语诗,口语诗是呈现世界的灵性,是叙述而非叙事的语言,是展现语言的天生丽质,很显然,伊沙的口语诗的核心是平民主义,是人性主义,是个人经验,当然里面也需要一点口水,“口语不是口水,但要伴随口水,让语言保持现场的湿度,让飞沫四溅成为语言状态的一部分。”而当他发出“饿死诗人”的时候,另一个诗人必将站立起来,他把他叫做“我”:“从语感到口气。从前口语到后口语。从第三代到我。”
这是一个诗歌的序列,当语感变成口气,从前口语到后口语,从第三代到我,在这个谱系中,伊沙是不是在为一代人建立坐标?当他用诗歌打破知识分子写作规范,当他拒绝宏大目标和主题,当他把现代派的长袍马褂塞进垃圾桶,把现实主义命名为“伪现实主义”,他其实并没有为一代人甚至一个群体寻找突围的方向,而是以一种纯个人主义的方式标榜这种颠覆的革命意义:“我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有一次来自口语诗内部的变革,我也深知这个变革只能由我率先实施——因为,比我老的口语诗人(所谓“第三代”)都是非自觉的。”颠覆那些所谓的现代派、现实主义诗人和知识分子写作之外,他更是把所谓第三代诗人清除出去,因为他们在伊沙的前面,因为他们更老,所以只有自己是自觉的,是第一个变革者——站在口语诗的旗帜下,回首而望,伊沙像是看见了无数的追随者,聚集在自己的“一沙一世界”里,而作为王者的伊沙似乎要用这样一种力量将所有的诗人饿死。
而这似乎就是伊沙所讲的个人经验,“口语诗如果缺乏鲜活可靠的个人经验,就等于放弃了它的先进性。”活在个人经验里,是不是会成为一种自负的行为?而在自负的舞台上,会不会自己反而变成了“剧场看门老头的傻公子”,在全体站立热烈鼓掌中把自己当成了众人期盼的戈多,而其实只是站在上面向叔叔要糖吃的愚笨者,甚至那些人的鼓掌只不过看一出笑话而激活的本能反应。这仅仅是一种疑问,一种阅读之后的观感,是在结束了“文选”的浏览之后返回诗歌文本过程中出现的。
的确,伊沙一直站在解构的道路上,那些宏大历史,国家主义,精英文化在他看来,都有着虚伪的一面,所以他发出了“饿死诗人”的宣言:“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饿死诗人》1990)”“我”不是伊沙本人,他只不过是一个诗人的代称,是“他们”中的一员,是污染土地的帮凶,是艺术世界的杂种,当然是“狗日的诗人”。所以“饿死诗人”的宣言下,他习惯了用戏谑的方式解构宏大主题,反讽终极意义。1988年的《车过黄河》是一个经过黄河而撒尿的诗人,“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眺望 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黄河和伟人构成了一种经典文本,但是伊沙却用撒尿的方式否定了一切,“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疏远”。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宏大的历史,“外省外国的游客/指着我的头说:/瞧这个秦俑/还他妈有口活气!(《最后的长安人》”没有高贵的灵魂,“我的灵魂是长了汗毛的/毛孔粗大 并不光滑/你继续摸下去/惊叫着发现它还长着/一具粗壮的生殖器(《灵魂的样子》)”没有抒情的诗意,“我伸出了一只手/梅花梅花/啐我一脸梅毒(《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没有传统意义所构建的崇高,“我深知劳作的意义/一支好的香烟/都弥漫着浓重的汗味/每当我享用它们/看它们在短暂的时间/烧成灰烬/我都有着非凡的快意/因为我是深明来历的人(《写给香烟的一首赞美诗》)”甚至在反讽着死亡,“那一天 我推着/母亲的遗体向前/他挡住我的去路说/‘给我,没你事儿了’/我把事先备好的一盒/三五塞给他/他毫无反应地收下/掉头推车而去/那个送走母亲的人(《一年记住一张脸》)”
 |
|
伊沙:饿死诗人也饿死了自己 |
这一切的戏谑、反讽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在《反动十四行诗》中,伊莎同样用粗俗的方式解构了“十四行诗”:“比泻肚还急 来势汹汹 慌不择手/敲开神圣的诗歌之门 十四行/是一个便盆 精致 大小合适/正可以哭诉 鼻涕比眼泪多得多/不得了 过了 过了/我一口气把十四行诗写到了第十五行(《反动十四行》)”十四行诗变成十五行诗,神圣的写诗行为变成了泻肚,在打破神话、解构神圣的同时,伊沙进入到自我世界里洋洋得意,就像等待的戈多永远不会来,而站在舞台上的是傻公子。
所以伊沙在解构的同时,开始建构自己的口语诗世界,这里有和生理反应有关的欲望和疾病,有形而下的物质,有和个人有关的经验,“姐姐 在麦地/和一个人睡觉/我手握弹弓/在树上放哨/很多年 姐姐/一听到这口哨/就哭!就哭!(《口哨》)”口哨里的记忆混杂着暴力和爱欲;“她在高潮中的一声喊/喊着元首的名字/显得异常快感/这尖锐的一喊/造成了我的软/我不是犹太人/但有着人类的软(《阳痿患者的回忆》)”将战争、民族有关的历史书写成一种生理反应;“那男孩手指太阳/给我们布道/‘这是——日/日你妈的‘日’”/他的声音/响彻了这个早晨/令我这跑来命名的诗人/羞惭一生(《命名:日》)”对词语的命名来自于被污染的暴力美学;“一个少女/单腿跳着手捂耳朵/这个动作有点奇怪/在她身上是一种美/奇怪和所谓美/人们得到了/他们所要的感受/但并不关心/这一动作的/产生与由来(《生活的常识》)”日常动作莫名当成了美,误读的世界也取消美的定义……所以“小小的祖国”只不过是“尿床”的图案,雕塑之美轻易被“高高撅起的臀部”所消解,诗歌的正当要求和女权主义者一样,“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对于伊沙来说,解构、反讽、戏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种所谓的平民主义,就如《原则》一诗中所写:“我身上携带着精神、信仰、灵魂/思想、欲望、怪癖、邪念、狐臭/它们寄生于我身体的家/我必须平等对待我的每一位客人”崇高和低俗,伟大和渺小,精神和物质,其实都无分别,如此的平等,似乎就是进入到了不被所谓的道德、信仰、思想、精英主义所裹挟的世界,就是恢复到了人本真的状态。但是伊沙的这种平民主义、个体主义在成为诗歌经验之后,明显用力过猛,他甚至在口语诗的世界里打破了一切和传统有关的东西,在持续性高潮中享受快感,最极端的例子便是在形式上的实验,“炮弹射进炮筒/字迹缩回笔尖/雪花飞离地面/白昼奔向太阳”,《善良的愿望抑或倒放胶片的感觉》的确在制造的逆向过程里拥有某种特殊的感受,《恐怖的旧剧场》里从“旧剧场是一片芜杂的荒草”回到“旧剧场是一片芜杂的荒草”的回文也具有了某种反复带来的意蕴,“结结巴巴我的命/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你们瞧瞧瞧我/一脸无所谓”模仿口吃患者的《结结巴巴》也让人获得了对词语的间离效果。
但是那首只留下标题的空白诗作《老狐狸》,真的变成了伊沙的行为艺术,没有内文只有一句说明:“欲读本诗的朋友请备好显影液在以上空白之处涂抹一至两遍《老狐狸》即可原形毕露。”伊沙曾经说起了写这首诗的冬季,在他看来,无论是内文的空白还是最后的“说明”,在阅读中制造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不下五位读者真的用显影液涂抹在空白处,最后当然是一无所获,在读者“骗人”的咒骂声中,伊沙仿佛洋洋得意在自己构筑的实验世界里,他甚至对此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老狐狸是不容易被抓到的。”
读者在咒骂,伊沙在发笑,这是诗歌文本之外的互文,也许是伊沙诗歌实验的期望的效果,但是当伊沙发出恶作剧般的笑声,实际上他所谓的平民主义、平等原则被自己取消了,他仿佛站在高处,俯视那些误读的人、被捉弄的人、发出抗议的人,在不平等的关系里,伊沙反而让自己在口语诗里保持了上帝的视角,而这无疑将他所有的实践都带入了悖论中,就像等待戈多,只有等待才是文本的最后意义,也是唯一意义,而因为等待的无而用另一个戈多取消戈多,何来那种等待感,何来真正的解构?一个傻公子站在那里,还获得了掌声,是不是变成了对自身的嘲笑?就像伊沙的那首《有一年我在杨家村夜市的烤肉摊上看见一个闲人在批评教育他的女人》,前面是16个“打耳光”,无非是男人打自己的女人,但是当伊沙成为文本的一部分,或者当打耳光变成诗歌事件,它就是一种对诗歌、对诗人本身的消解:“嗨吃烤肉的胖子你看啥呢/我教育我女人你看啥呢啪一耳光”……
仿佛就是打在伊沙的脸上,他被拖入到了事件之中,而且打在伊沙脸上的时候,因为需要这样一种感觉,伊沙反而觉得过瘾,甚至希望更多的耳光落在自己的脸上——所以,伊沙就是被自己拖进了自设的文本里,于是里面都是被当成真理的谎言,“我的朋友们/把我的话当了真/就敬着我这个人/其实我对他们撒了谎/其实我一关都没过(《酒桌上的谎言》)”于是里面都是受虐的自由,割包皮的外科医生“真他妈的幸福”,晚年不保的奸尸犯老张,“众尸起舞为他开道”,死了的吸毒者朋友,“就像电影中的超人/在天上飞”……实际上,伊沙在2002年之后有限地走出这个悖论,他的口语诗里少了戏谑,而以一种平和的语气关注日常生活,“父子悲哀”里传递出的是“谁是玩伴”的疑问,“妻在酒吧”探讨的是如何“再度赢得我的欣赏”的情感问题,“忘年的亲人”里是“我抱着母亲的墓碑”的亲情,交警和车夫不再是敌对,他们在“残酷之上的残酷”里寻找真实的生活,出租车司机也不再是那个变坏的人,甚至还要“不计报酬地给你讲个笑话”,环卫工人在零度以下的早晨,还做出了“一个敬礼的手势”,而县医院的中年患病农民甲乙丙丁说出“丢人哩!/俺这台拖拉机就快报废球啦!”时都是酸楚——这种转变似乎少了恶的趣味性,少了解构的快感,而是道出了生活的艰辛,正像《春天的乳房劫》所说,乳房已经从欲望的器官变成了疾病的器官,带来的生活的无奈:
亲爱的,其实
在你去做术前定位的
昨天下午
换药室的门无故洞开
我一眼瞧见了两个
被切除掉双乳的女人
医生正在给她们换药
我觉得她们仍然很美
那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这种转变是有限的,甚至容易湮没在伊沙自设的那个世界里,所以伊沙诗歌真正致命的是:在否定一种秩序和规则的同时,不是为了建构一种体系,而是极其用力地将其逼上毁灭的绝路,而自己反而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俯视那些失败者,所以不再有平民主义,不再有平等性。无论是口语诗歌还是精英写作,无论是叙述还是叙述,无论是不要脸的诗人还是知识分子,也无论是十四行诗还是十五行是诗,需要的是一种包容精神,而在伊沙那里,写诗变成了树立靶子的破坏行动,甚至开始了攻击、诋毁,最后所有的解构、戏谑、反讽都跌入了为口语而口语的机械主义窠臼中,最后在喊出“饿死诗人”的同时,也饿死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