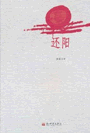 |
编号:C28·2121120·0935 |
| 作者:侯磊 著 | |
|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10月 | |
| 定价:24.00元 亚马逊10.50元 | |
| ISBN:9787510412417 | |
| 页数:230页 |
古代、后宫、京城,这些标签对于这部小说来说,或许是开启了一种陌生的文本空间,而“一部讲述后宫秘史的历史小说”、“新京派小说代表作”等注解似乎又为“小说前沿文库”丛书的整体定位带来了困难。如何消解历史?如何在“新历史”中讲述宫廷传奇?或者与现实保持的那个距离才是虚构文本走向阅读前沿的标记。没有完全净身的太监,本身就带有戏谑的味道,似乎要把故事带向身体和仪式的挣扎之中。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变回自己,所以寻找自我,寻找爱情,甚至寻找自己的后代就成为“还阳”的最终目的。在一个陌生的文本空间里,那些奇幻的色彩或许才是让我们不必纠缠于历史的理由。小说第一句:“这天一早,毕玉从毕小四家中醒来,他几乎都忘掉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还阳》:被架空的故事和理想
如我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那我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我是太监。
——《第二章》
封面上那一轮的太阳,是猩红的光,有限地照耀,却如一滩流下来的血,仿佛毕玉被刘爷处理的下身,而那太阳的中心是若隐若现的神物,仿佛是那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宫廷世界,隐秘而模糊,“还阳”的场景被设计成一张充满隐喻的抽象画,而那个用毕玉残缺的身体构筑的在场世界徐徐拉开了帷幕,小说 第一句:“这天一早,毕玉从毕小四家中醒来,他几乎都忘掉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那个世界就像一个未醒的梦,隐秘而模糊。
残缺的是鲜血迸溅之后的那一堆碎肉,从身体里割了下来,用水洗干净,用香油炸了,再“裹满了石灰、珍珠末、潮脑、樟脑面、麝香、透骨草、沉香、辰砂等细细磨成的粉末”,再包上绸子,装入精致的匣子,写上姓名、年龄、籍贯、生辰八字和净身的日期,然后再裹上黄丝带,挂在贴近天花板的位置,“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净身之举将毕玉的身体割裂成两部分:活着和死去,现在的自我和以前的自我,那男根在花椒水、滑轮、绳子和刀组成的意象被阉割,而从此,健康、读书的小书生也变成了太监。身体的割裂带来身份的转变,而这种身份的转变是毕玉进入皇宫的通行证,这种悖论对于毕玉来说,是玄幻的,是感性的,甚至是理想主义的,而一旦成为另一个人,走回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毕玉是个读书人,起码他自己是以读书人自居的。”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也是健康的身体下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因为现实,而多了一份无奈,洞房夜被骗,“发现那里是一片偌大的虚空在等待着他。”这便是不能改变的生活,偌大的虚空将他拖向现实的边缘,而在这边缘便产生了改变现实的“伟大”理想,把便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进入皇宫。所以他来到了京城,“京城给毕玉的第一印象就是从找厕所开始的。”这也是一种逼仄的现实,厕所是藏污纳垢之地,是现实的巨大隐喻,似乎在毕玉的心中,那个遥远的皇宫里的一切都是现实之外的理想存在,所以他选择用极端的形式进入皇宫。尽管他净身而成为太监并非是自己最完美的进攻方式,但却是最直接最便捷的,而从现实到理想,对于毕玉来说,是丧失作为男人的身体开始的,而丧失了男人的身体,也就丧失了自我。
几根胡须和腋毛不见了,说话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像孩子般稚嫩,又像女人那样尖细,这是另一种现实,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身体,对毕玉来说,是一个连自己都无从知道的未来。进入皇宫,成为其中一员,毕玉从最低贱的活儿开始——刷马桶。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这是一个生死如常的世界,包括肉体的惩罚在内,都用不可颠覆的秩序维系着。但是这表面森严的宫廷里,却到处是危机,甚至不堪一击。而毕玉也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被阉割只在某种程度上被分离,因为没有完全净身,他发现自己的男人身份还若隐若现,似乎一旦被激活,自我又将重新回来,而一旦自我回来,理想也可以安全地拥有。
“他发现自己和其他太监这点是不一样的,他一见到宫女还会脸红,还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在太监群体里他成了“异类”,而更大的异类在于他在冷宫中奇遇了淑妃,而且不可思议地与淑妃产生了所谓的爱情。如电石火光一般,即刻消解了男性身份缺失的遗憾,尽管后宫里“杂糅着一百年来尸体的腐臭味和酸酸的血腥味”,那是死去的味道,就像毕玉死去的那堆肉一样,但是在死面前的活更显珍贵,所以和淑妃的爱情迅速称为一个男人身份的回归,“每当和淑妃聊过天的夜里,毕玉怎么也睡不着,他的眼前总是无端出现许多奇怪的画面,是一男一女,像两个赤身的妖精在打架”。而这种与身体有关的欲望的复活,是毕玉重新找回自我的开始,对于毕玉来说,另一个更大的计划浮出水面:还阳。
“还阳”当然是重新找到男人的欲望,重新返回男人世界,或者说,还阳除了技术上的指称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的确认,找寻自己失去的那个身体和身份。“如今,宫中的故事再一次发生,毕玉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故事中的人。”已经成为宫廷故事一部分的毕玉,要重新找回失去的身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作为读书人,毕玉似乎能够在充满愚昧和阴险的宫廷里得心应手,他先是取得了皇上的信任,让皇帝也恢复了那种身体有关的欲望,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毕玉是一个闯入者,对于宫廷外的生活有着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而将外部的信息带入宫廷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闯入者当然是要改变这个封闭世界里的秩序,让皇帝取消上朝、玩“扑扑登儿”和屎壳郎拉车的游戏、给宫女缠足,然后让皇上逛妓院、吸大烟,这些光怪陆离的生活对皇帝绝对是一个刺激,也从此改变了为莫如深的宫廷生活。
对于一个闯入者来说,改变秩序就意味着颠覆规则,而毕玉也从刷马桶的太监变为宫中领班,再成为统领后宫的总管,他一步一步从最低微出爬上来,向着自己更大的理想进发。而当皇上因为萎靡生活和身体原因突然驾崩的时候,对于宫廷规则的颠覆当然受到了阻力,或者说从此毕玉转向了一种自我保护,而其实这种保护对于毕玉来说,是脆弱的,是不堪一击的,在宫廷内部,各种权力斗争对于他来说,似乎只有招架,或者说,“还阳”的生理意义已经成为毕玉的最大理想,而非身份上的认同。
这当然是一种悖论。对于已经成为太监的毕玉来说,生理困扰一直无法彻底摆脱,那个男人的自我并非顺利的回归。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尴尬依旧是现实意义的,皇帝没有驾崩之前,要毕玉晚上陪他唱《西厢记》中的《红娘》,便是他男性身份的再次丧失,甚而至于“那天毕玉就在养心殿中陪着皇上睡下了”,作为第一个睡龙床的太监,毕玉仍然被身份所困扰,这是一个刻在他身体上永远无法抹去的印痕,那个“还阳”的计划显得越来越渺茫,“毕玉对淑妃说:咱们一定选拔一批正义的、有学问的大臣,再招募一批忠实的、不会为非作歹的太监,你辅佐孩子管理前庭,我在后面稳定好后宫,咱们好好的管理这个国家你说好么?”这是他的理想,但是理想多少有些幼稚,甚至只能寄托在梦中,他梦见淑妃产下了龙种,“他猛然间有了一种做父亲的幸福感,自己的生命有了延续,将来自己死了,这个婴儿就会代表自己一样仍旧在世界上。”但这毕竟是一场梦,他甚至还要去探究那个孩子是男还是女,在他心里这是无法跨越的一个宿命。但梦醒之后,是宫廷之变,是外国入侵,以及他被尹小刘更大的阴谋架空的现实。“皇子为帝,康王为王!”的命令像一盆冷水泼在他的身体之上。
作为一个闯入者,毕玉只是一个弱小的个体,在他身上只有社会底层男人卑微的理想,甚至只是洞房被骗对于男女欲望的弥补,只是肮脏厕所的现实所带来对于物质享受的向往,而仅仅于此,“一个只是来到京城讨生活的小书生,他曾经梦想着读书中举,然后进入朝廷”,而身体被阉割变身太监,也只是个体的某种理想的满足,“现如今通过净身当上了后宫的总管,还有了众多的宫女作陪,而且把最大的宫女:娘娘都搞到手了。”对他来说,只有被放大的私欲,但是在宫廷里,这个理想多少有些幼稚,有些微弱,他敌不过那些阴谋,“这么多日子,你还没感觉到么?您的身边都已经被架空了,尹公公马就要对您下毒手了。”而在尹小六、王丞相等阴谋者之外,还有另一个闯入者:外国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一步步接近皇宫,是另一个计划,他的背后是西方文明,所以作为珍宝馆的洋人,汤若望对于宫廷的秩序比毕玉更为彻底,也更具有颠覆意义,薄荷叶、月桂树叶、鼠尾草、麝香草、薄荷花、艾菊、山竹、火龙果、蛇果、毛丹、洋桃、山梨等陌生名词成为宫廷生活的一部分,在衣食住行上都进行着渗透,而皇后最后“下令把太和殿中的大柱子全部拆掉,一律换成欧洲罗马风格的大理石廊柱,并且要把养心殿、交泰殿等等全部拆掉,改为欧洲风格的大尖顶式建筑。”这样的改造当然是异族文化的输入,对于毕玉来说,在宫廷阴谋和西方颠覆的双重作用下,走向了一条溃灭之路,被架空的自我只剩下“还阳”的虚幻梦想,而淑妃之死也将他男人的身份彻底打碎:“毕玉回头望望皇宫的方向,他突然觉得皇宫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了,起码是他在的世界里消失。那里有他的居室,有他的女人,有他的孩子,有他的理想,还有他的家。”
消失的不是那个皇宫,是他的身体梦想,是他对于男人身份的找寻,是他回归自我的“还阳”,被赶出皇宫落荒而逃的毕玉与汤若望一起远走他乡,那个未知的世界在等着他,但一定又是另一个阴谋。“秘制宦官阉割要诀”,那“在第一页的第一列上写着这样几个字”似乎也像是依稀的梦,只是梦而已,而不是现实,“先不忙,先好好的看着他。回到意大里亚再说吧。”在西方传教士汤若望面前,一个被阉割的中国男人躺在那里,身体已经缺失,身份已经丧失。
“你不过是一个太监,一个奴才。”这是淑妃曾经对他说的话,虽然被逼无奈,但也是一个明确的定位,和毕玉自己怀疑“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尴尬那样,作为皇宫的闯入者他永远难以逃脱宿命。没有完全净身,或者正是毕玉最可怕的处境,所以他既有重新做男人的欲望,又总是陷入身体的沦陷中,他所改变的只是另一个世界里的秩序和习惯,是完全在自我之外的,但是对于自我,不管是身体还是身份,都无能为力,“一只公鸡、公羊、公牛、公猪等等被劁掉了,那么它们最好的面对生活的态度就是安心的去做一只肉鸡、肉羊、肉牛或肉猪。”被架空的自我,被架空的理想,隐喻着虚幻的梦境。而那个皇宫,那些故事,是不是也是另一种虚幻的梦境,另一个被架空的现实?
其实,在这本书里,除了斜么签儿的、熬滔、官茅房、五积子六瘦、魔三道儿等浓厚的京味,以及在宫帏知识上的专业性之外,侯磊似乎并未做好写寓言故事的准备,至少在整体结构和行文上,显得短促而平淡,毕玉身份的转变、和淑妃的爱情、宫廷政变等几乎都是用简笔的方式叙述而过,对于人物的塑造没有标新立异,对于情节的设置也没有精心构筑,虽是虚构历史,但这虚构是被架空的人物,被架空的故事,以及被架空的寓意。“还阳”竟也无处落脚,就像最后汤若望准备白纸、鹅毛笔和墨水瓶,“在上面写下了第一行字”,那后面不是冒号,是一个句号,以及“2010年3月于北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