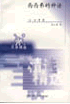|
编号:C38·2151022·1219 |
|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著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
| 定价:38.00元亚马逊22.60元 |
| ISBN:9787532761845 |
| 页数:336页 |
“人们为焚尸炉拨火,犹如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一样。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或任意而为之。”不相信才会让任何东西无意义,无意义才会让一切都变成可以为之的行为,“既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杀人者既不错,也不对。”在这种几乎荒诞的存在中,加缪提出了反抗的主题。笛卡尔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想提高到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标志、唯一条件,而加缪在《反抗者》中,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将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但是,有时候反抗却还是一种荒谬,“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为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悖论?
《反抗者》: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
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里,在“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历史上的反抗》
因为荒诞而矛盾,因为矛盾而反抗,因为反抗而死亡——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当反抗彻底变成一种行动意义上的革命的时候,“故我们存在”变成了合目的性的要求,而“我们是孤独的”命题又把反抗拉回到虚无主义的世界,虚无主义不是制造,不是存在,虚无主义的反抗就是一种否定自己的行为,在革命的旗子下最终变成专制,变成恐怖,变成暴力,“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登上王位。声称以革命的旗帜引导我们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已变成随声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本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抗,革命本来是一种制造新存在的行动,但是在反抗历史的标本中,这样的形而上学和革命,反而变成了一种恶,架设了断头台,树立了敌人。
“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引用荷尔德林在《恩培多克勒之死》中的句子,加缪其实不是为了为妥协寻找一种借口,而是“忠贞地爱它”,是“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是“绝不蔑视”,是为了“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积极乐观,是面对“严酷痛苦的大地”采取的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但是这样的解放无论如何还有着某种神圣性,甚至有时候脱离了反抗的内在需求。在加缪看来,以神性的力量来化解悲痛,是一种精神的至上主义者,但是在现存的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回到反抗的自我意识这个主题上来,“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自我审视之后才能驾驭自己的行动,才能找到“神圣的夜晚”,才能保持忠贞,才能面带微笑,才能一无所惧。
如何审视自我?加缪把罪恶放在这个链条的开端,罪恶变成信仰,罪恶取代理智,罪恶制定法律,罪恶控制哲学,“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加缪把我们时代具有的罪恶归结为逻辑罪恶,“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这是奇怪的逻辑,这是荒诞的罪恶,实际上乔装打扮的罪恶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荒诞推理而衍伸为逻辑罪恶,所以当荒诞变成这个时代的普遍意义,罪恶也就无孔不入地实施着自杀和杀人的事情,而要消除荒诞,在加缪看来,就是要进行反抗:“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样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惟一明显事实,即反抗。”
一切都是荒诞的,一切都需要反抗,反抗诞生在无理性的场景中,反抗面对的不公正的生活,反抗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反抗是寻找一切消逝事物那个统一性,也就是说,反抗的最终目的不是拒绝,不是死亡,而是发现合理性,所以在加缪看来,反抗的反抗者是说“不”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就是反抗者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超越个体,也就是说,我的反抗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身上的某种东西是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也就是人有互助性的天性,“这种互助性是在镣铐中产生的。”它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群体相信有某种正当的权利,“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
“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尊重人,符合人性,这是反抗所要建立的世界的意义,而这个世界也是超越了圣宠的感恩世界,所以加缪把反抗作为生存权利的一种“类行为”,包含着人类性和社会性。而这种“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在加缪看来,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反抗,因为“它否定人与创造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行动,不是为了目的的反抗,而其要脱离神圣的恩宠世界,就是要摆脱神性而恢复人性。所以形而上反抗精神从起源上来说,是和宗教有关,从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到杀死其弟亚伯的该隐,再到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所说的人化的神,加缪认为,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其标志人物是戴着镣铐的哲学家萨德。27年的监狱生涯似乎是将萨德推向了一种饱尝罪恶的深渊,所以他怀疑神性,否定上帝,“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否定上帝,是为了得到本性,而本性在萨德那里就成为一种自由,自由是毁灭罪恶的力量,自由是创造王国的手段,自由是本能的自由,自由是权力意志,所以萨德的自由主义到最后“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这就是那个“唯一的人”,是终结世界也是成为上帝的人,“‘唯一的人’转身走向那个囚徒,正是这个徒无穷尽的想像力创造了他,二人交融在一起。”
而萨德的“唯一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漫主义,他和囚徒站在一起,其自身也有了恶的特点,“它仅仅热衷于塑造不法之徒、善良的苦役犯、豪爽的强盗之类的形象,借以阐述要求自由的深沉的运动。”所以当浪漫主义以花花公子的形象开创自己的反抗世界的时候,他创造的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就如波德莱尔的罪恶花园,罪恶在其中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为稀罕的品种,而恐怖自身变成了细腻的感觉。浪漫主义的反抗是对于上帝的反抗,所以它以恶来回答恶,以高傲来回答高傲,甚至用沉默来回答沉默,所以说,浪漫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了另一个上帝。但是这种对于上帝的回答是建立在一种“好意”基础之上的,甚至它自己成为另一个上帝也是为了创造秩序,所以这样的反抗无法走向更远,它最后被虚无主义“一切皆被允许”而走向了其反面。
“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解救世界。”尼采的那一声宣言是虚无主义对于反抗的阐释,否定上帝,而且上帝已死,在本质上是否定上帝的道德性,所以击垮一个圣殿,建立一个新圣殿,其最终的指向是单一的“不”,或者单一的“是”,在尼采那里,不管是否定上帝,而是自己成为上帝,都是一种单向的目的论,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一切反抗,甚至放弃想要产生神明以纠正世界的反抗,反抗者才能成为上帝。“若果真有个上帝,如何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所以这样的反抗只是虚无主义,“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这样,便从绝对的失望中进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发出极大的自由。”
而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反抗变成了另一种绝对的理论,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它对一切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阿蒙与兰波告诉我们,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过何种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所以有了兰波诗歌之外那腰带里带着的八公斤黄金,有了安德烈·布勒东“无情的权力”与专制带来的政治狂热,有了破坏的混乱,有了必需的死刑,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害怕的是承担责任,它想到的是破坏,不管是诗歌的诅咒,还是物质的锤子,他捍卫的就是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只有一个主人:“我反抗,故我存在”。
从自由主义到浪漫主义,从虚无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是对恶的抗议,但是这种抗议最后变成了”过度的绝对“,也就是反抗精神也变成了虚无主义,最后吞没了创造的力量。而其实在加缪对于反抗的阐述中,除了形而上的反抗之外,历史上的种种反抗行动,似乎都在这一个“过度的绝对”中走向了反抗精神的反面,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历史上反抗的实践似乎都指向一个词:革命,“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革命是因为向往自由,革命是为了抗议压迫,革命是为了获得正义,而革命却必须拿起武器,所以革命当为了建造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变成了断头台为标志的时代。
“一个被法庭判处死刑的骗子竟说他要反抗压迫,因为他要反抗断头台!”本来,断头台是压迫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但是在怀疑一切的革命时代,断头台已经变成了革命的标志,已经变成一个绝对的符号,甚至变成了自由,所以在革命式的反抗中,这种断头台的象征意义一直存在着,而在非道德主义、科学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等理论的补充之下,破坏一切的革命甚至走向了恐怖主义,建立政府的革命则走向了专制主义。1878年俄罗斯女子维拉·查苏利奇开的那一枪引发了一连串的镇压与谋杀;同一年,“人民意志”一个成员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还死》的小册子中把恐怖活动定为原则,其后果接踵而至;仍是在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创造了国家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是镇压与革命的对峙,另一方面则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伦,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
不管是国家权力的加强,还是革命力量的破坏,多于反抗精神格格不入,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加缪看来,都变成了一种暴力,变成了另一个帝国,“原则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原则本身中的残留之物,并使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神圣化。不论这种虚无主义以后借用了什么道路,从它想摆脱一切道德规则而在本世纪进行创造之时起,便建造了恺撒圣殿。”这不是合理的革命,当然这也不是最可贵的反抗,甚至这样的犬儒主义都变成了虚无主义,反抗甚至也开始否定自己,“从而陷入最极端的矛盾”。
而加缪一开始就认为,反抗者不仅是那个说“不”的人,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否定荒诞和不公平,却也应该创造秩序,寻找自由,“我们不存在,但应当通过一切手段来存在。我们的革命就是通过制造,在一切道德规则之外获得一种新存在。”所以反抗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而是“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是“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所以加缪在艺术创造中找到了反抗精神,“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加缪把艺术中的创造视为反抗的精神,特别是小说,是对于世界的修正,是对于死亡的超越,在小说描绘的世界里能感受到巨大的反抗力量,“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而革命这一方面惟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
艺术或者才是形而上的反抗,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反抗,“在这个地狱中,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但是在艺术世界里,体察反抗精神的时代意义或者并不完整,所以加缪在《南方思想》中发出了疑问:“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在他看来,这种呼唤就是反抗,就是生命运动的反抗,就是生命站立起来的反抗,不是虚无主义,不是革命暴力,而是一种尊重个体生命,建立公正世界,符合人性需求,超越自己而共同享有的力量:“我们每人要拉开弓经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