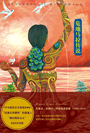 |
编号:C59·2160516·1294 |
| 作者:【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2月第一版 | |
| 定价:30.00元亚马逊15.50元 | |
| ISBN:9787532770540 | |
| 页数:150页 |
《危地马拉传说》是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早期的神话故事集,是阿斯图里亚斯根据早年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写成的,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危地马拉传说》包括《危地马拉》、《现在我想起来》、《火山传说》、《幻影兽传说》、《文身女传说》、《大帽人传说》、《花地宝藏传说》、《春天风暴的巫师》、《库库尔坎 羽蛇》这9 篇神奇而富有诗意的民间传说。这些作品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原始、魔幻、令人赞叹的世界。阿斯图里亚斯同时对危地马拉的独特自然风光作了美丽的描绘,全书仿佛一幅幅绮丽多彩的油画。这些传说直接或间接地采用了印第安人的著名神话故事《波波尔?乌》的题材和技巧,笼罩着浓重的魔幻色彩。
《危地马拉传说》:为了相信我到了家乡
两人用玉米籽算我的年龄,从左到右一颗一颗地加,像是祖先们在数石头上记录年代的圈圈点点。数年岁是件忧伤的事。我的年龄让他们忧愁。
——《现在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的是孩提时那些画里受伤的鹿,是番荔枝树下土地里的眼泪,是灯笼果花上的阳光和空气,是森林里万物的歌唱和舞蹈,可是,当时间经历了百年,石头上何时长出年岁的灵魂?田园里何时会有不衰老的土地?堂·切佩和蒂娜女孩何时能记下我的故事?
这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白昼将要降临,黎明将要显现,子孙后代将被赐予力量,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件忧伤的事,因为堂·切佩和蒂娜女孩患甲状腺肿,疾病侵袭了身体,而且那些巫术正在影响他们,堂·切佩说:“为了将我的生命延至永生,在绿眉翠鴣巫术的作用下,我到了透明的境地。”而蒂娜女孩说:“野百合巫术的影响剥夺了我的时间意识,只知道一天连着一天,一年连着一年。”透明的生命中年龄是不是变得虚无,一年连着一年是不是没有了时间仪式?仅仅是我想起来了,仅仅是他们用玉米籽算我的年龄,而现在的道路,在巫术中已经找不到后代。
石头在看,树叶在说,河水在笑,还有太阳、月亮、星星、天空和大地在自己的意志里运行,而我在告别孩提之后看见的道路,却和天的四极相反,那里有绿色的路,有红色的路,有白色的路,在左右和中间交叉开来,而我无意间踏上的是黑色的路,四条路交会于西巴尔巴前,但是当那个幽灵说:“这条是国王之路,谁走这条路谁就是国王!”当我走上去的时候,我会引领子孙,还是幽灵带领我?我是有着首领的打扮,可是孩提时代已经远去,堂·切佩和蒂娜女孩已经患病,巫术已经统治时间,那一条黑色之路却有着黑暗的破坏力,它冲散万物,“将它们卷入昏暗的漩涡,直至化为粉末、无形、幻影。”
时间化为粉末,时间而无影,时间成幻影,玉米籽一颗一颗地架在年龄上,石头上写下圈圈点点,可是忧伤的岁月啊,那些子民都已经被驱赶出了传说,“子民听得见我,子民拥有着我,子民看得到我……”听到、看到和拥护,却是在时间的幻影里,“我钻得越深,我的心就越痛!”疼痛如我,疲惫如我,忧伤如我,首领如我,一定要把他们带离这一条黑暗的路,一定要打破那石头般的沉默,一定要回到祖先的石头纪事里,我听到堂·切佩说:“盲人用狗的眼睛看路……”我听到蒂娜女孩说:“翅膀是将我们绑上天空的链条……”仿佛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没有死去的祖先,在巫术、黑暗、忧伤里,我必须回到孩提时代,回到时间之中,回到家乡,“为了相信我到了家乡”成为我当初离开的理由,也一定会是我最后回来的终点。
“献给曾给我讲故事的母亲”的题辞写在一本传说的封面上,母亲是我的母题,母亲是我的家乡,母亲是我的传说,“这片土地上,多种力量筑起岩石与腐殖土的舞台,随后孕育出生命。它们依旧威力无比,精力旺盛,仿佛已枕戈待旦,待天灾突降于两片大洋之间,创造出新的融合与生命乐章。”创造的生命从何处而来?他们就在“火山传说”里,三个人来到风里,三个人来到水中,他们组成了纳华特尔民族恒久不变的数字,风里的三人像鸟儿一样以水果为生,水中的三人和鱼儿一样以星星为食,可是当这个世界被打破的时候,山之禽便成为远古的记忆,为了赢得土地而屠戮牲畜,为了获得城市而戴上面具,水中只有倒影,风中只有叹息。而对于鸟巢来说,山之禽是他们最初的父母:“这是我们的面具,面具之后藏着我们的脸蛋儿!这是我们的替身,我们靠他们伪装!这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山之禽,我们为夺得土地杀了他!我们的纳华尔!我们的纪念!”
风已不见,水已不见,他们把山叫做“卡布拉坎”,山是力量,吐出的火焰燃烧大地,指甲剥开的是火山口,于是,“鸟巢看到同伴们消失了,是被风掠去的;水中的替身消失了,是被火吞噬的,闪电从天而降落入玉米地,燃起了火。”火是燃烧,吞噬了大地,火是毁灭,杀死了水和风,火也是创造,一位圣人、一朵百合以及一名孩童,他们接纳了鸟巢,他们建立了庙宇,他们形成了村庄——火山孕育了新的希望,而所有的希望之产生因为有一样东西没有被毁灭,那就是图腾,当图腾活了下来,图腾便说:“某世纪中有一天长数百年。”
重新启动了时间,重新书写了传说,重新诞生了生命。这是“火山的传说”,燃烧而毁灭,驱赶而留下,时间回到身边,于是有了编年史,于是回到了童年的家,于是有了“幻影兽的传说”,当修道院的修女剥去天使的果皮,果肉和种子便长成了基督的身体,“隐蔽的上帝”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与肉。而那个“罂粟人”呢,却像一个幽灵在门前等着圣饼盒,他对修女说:“有人要剪你的辫子!”又说:“小姑娘,我领圣餐时,上帝有您手的味道!”这是亵渎,修女收回了碰圣饼的手,她从此看见梦中的自己站在罂粟人的身旁,身处魔鬼般的婚礼,蜡烛、棺材、蝙蝠,以及自己的肉身,罂粟人甚至摩挲她的私处,这是欲念的魔鬼,这是地狱的幻影,基督在哪里?“她撕扯影子,睁开双眸,带着不安的瞳孔脱离深沉的内心,如落入陷阱的老鼠们,混乱、失聪,脸颊一泪珠盒——变了形,伴着脚上他人痛苦的喘息和背上无形火焰里麻花辫的炽烈炭流,她瑟瑟发抖……”
肉体和精神,在幻影兽里变成痛苦的挣扎,可是这只是一场考验,辫子还在,手臂还在,肉身也还在,当夜晚降临的时候,罂粟人化为一头长形兽,而修女“她正跪在房间里,带着天使的笑靥,与百合和神秘羔羊一起耽于清梦。”幻影兽是信仰的幻影,终于在肉身之外找到了自己,如图腾一样,“某世纪中有一天长数百年”。肉体的一天,信仰的永恒,而在生命在火山传说中诞生,信仰在幻影兽中寻找到,那么“文身女传说”则是关于文字的开始,杏树尊者将灵魂分给四条不同的道理,起先是朝向不同的四极:“黑极是魔咒的夤夜,绿极是春天的风暴,红极是金刚鹦鹉或热带的狂喜,白极是新土地的希望。”这是时间回来的鸮渔月月圆之时,白鸽在白色道路上用灵魂医治幻想症,红心在红色道路上用灵魂开始遗忘,绿葡萄在绿色道路上用灵魂抵偿债务,而最后的黑色道路上,杏树尊者却让自己脱去了植物的外衣,变成一个走向城里的人。
黑暗的路最短,黑暗的路最寂寞,可是在城里,来了商人,来了花鸟,来了三十名骑马的随从,杏树尊者问一个女奴:“四条路走过了多少月亮?……”他们像一对恋人,在月圆的时候彼此相望,从黑暗中来,想念着和月亮有关的时间,但是女奴却被追捕,说她中了邪,然后锒铛入狱,然后除以火刑。在行刑前,尊者在她的手臂上刺了一条小船,“文身女,有了这个文身的力量,你总能死里逃生,就像今天,你也能逃脱。我愿你如我的思想般自由;你把这条小船画在墙上、地上或空中任何你想画的地方吧,然后闭上眼,走进去,离开……”文身是符号,是希望,人们发现在牢里,长出了一棵枯槁的树,而在树枝间却有三朵小小的杏花,粉色依旧。
月圆之时,肉身上的文身是另一种时间的文字,在生命、信仰出现之后,文字是另一种力量,从黑暗和灾难中来,却拥有了思想,拥有了方向,甚至拥有了某种爱情。而她会逃向哪里?遥远的世界?美丽的寺庙?崇山之间?还是重新回到编年史里?可是那负责祭祀的教徒承载的是人类的羸弱,是对知识的渴求,是面对新世界时的虚荣或对精神传统的诉求,是沉湎于钻研美术、学习科学与哲学,但是却疏于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在末日审判时,“竟忘了在召集做弥撒后打开庙门,祭祀结束后关上庙门。”
谁会从那扇庙门里进入?是没有写进旧编年史的哲学家和智者?修士在修道院里发现了那疯狂跳动的小球,它为什么会跳动?谁在空着着它?是神秘的力量还是被魔鬼附体?没有哲学家,没有智者,没有思想,也没有知识,魔力是一种让人恐惧的东西,在睡梦中修士也进入到恐惧之中,他终于看见了云朵深处的战争征兆,看见了战士向俘虏射出的箭,看见了向城市进发的敌人。“愿白人看到我们的武器后迷惑不解!愿我们手中不缺闪亮的羽毛,它就是利箭、花朵和春天的风暴!愿我们的长矛刺伤敌人又完好无损!”那些战士们在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驻守在城市里,可是那外面的敌人呢,他们叫西班牙殖民者,他们带来集市和交易,他们也带来哲学和知识,他们更看见了从没有看见过的镜像:“山重叠山,林覆盖林,河流连成瀑布,一堆堆石子、火焰、灰烬、熔岩、沙子、湍流沉落下来。”
太帽人的传说诞生,其实是一种殖民,而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对于写着旧编年史的国家来说,对于已经有了生命、信仰和文字传说的民族来说,眼前的西班牙人就像那个小球一样,“它是诡秘莫测还是魔鬼附体?……”胡安·波耶和妻子胡安娜·波耶缺失了胳膊,像这个城市里的人一样,他们在自己的编年史里孕育出雨水,孕育出河流,孕育出孙儿,也孕育出灾难,“每一株植物,每一次植物诞生的尝试,都会出现新的灾难,沸腾的黏土冷却、流淌。”而他们看见,当自己的儿子进入到无形的离鸽女神城的时候,那里变成了第一座倒影城,“多少河之舌舔过这座城市,直至将它冲走?久而久之,城市逐渐失去了意识,变得柔软如梦,瓦解在水中,与其他原始的倒影城一样。”倒影里是新的年鉴,是新的男人和女人,是新的战争,是新的时间。这是“春天风暴的巫师”带来的传说,而当新的一切开始的时候,还会有火山的喷发,还会有幻影的梦境,还会有文身的希望?还会有新鲜的镜像?
“传说这些村镇就是这样失去了与神灵、土地和女人的亲密接触。”其实回到了我已经遗忘的孩提时代,回到了患甲状腺肿的男人和女人,回到了幽灵的记忆,回到了玉米籽带来的忧伤,帕伦克城、科潘城、基里瓜城、蒂卡尔城在哪里?当老者的寓言消失,当国王患上丘疹,当梦页数梦椰树编织故事,“岩石脚边,一个幼小的民族穿着宽大的外衣,缠着传奇的腰带,玩弄政治、贸易与战争。”还有织布方法、零的价值以及粮食的收获,而出现的城市是征服者的第一座城市圣地亚哥圣人城的孪生城、第二座城市安提瓜、第三座城市危地马拉·德·拉·亚松森,当记忆占据了通往西班牙城市的阶梯,那么记忆其实在失去时间的传说里变成了一个盲者:“西巴尔巴与图兰,神话中遥远而氤氳的城市;伊希姆切,城徽上,被俘之鹰为卡克奇克尔贵族的御座锦上添花;乌坦特兰——权贵们的城市;阿蒂特兰,镶嵌于一片蓝色湖畔岩石上的瞭望台。”
新的传说,新的城市,新的人类,新的父母,那个哭泣的女人说:“我哭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我深爱的男人!他不是我丈夫,但我很爱他……请原谅,兄弟,这是罪过!”模糊的道路、殖民地的旧衣裳、忧伤的宗教精神是不是来自家乡之外的那些征服者?是不是就是雅伊所说的“装我在心间”的黄战士?《库库尔坎 羽蛇》似乎就在展示关于时间的三个段落,黄幕拉开是早晨的黄色魔力,红幕拉开是午后的红色魔力,黑幕拉开是夜晚的黑色魔力,这是库库尔坎的三色宫:晨为黄,晌为红,夜为黑。他是太阳,他是统治者,他是掌控一切的神,当钦奇比林向库库尔坎深深鞠躬,称他是“神,我的神,伟大的神!”的时候,金刚鹦鹉却说库库尔坎设置了圈套,金刚鹦鹉是倒影城,那么它提供了另一个关神的镜像;当隐形的拉拉巴尔可以提供最好的箭去射杀的时候,金刚鹦鹉说生活是“太过严肃的欺骗”,在他看来,“太阳并没有亲自来到夜晚,到的是他镜中的影像。”黑幕降临,库库尔坎的臂弯里是少女,但是有人把她带入了城里,然后反锁,“这样就没人会闯进庙宇的禅房,庙里存放着蠕虫和深色绒羽!”黄幕里解构了库库尔坎的神话,红幕里揭露了库库尔坎的谎言,黑幕里逃离了库库尔坎的控制。而在第二个循环中,永生不朽的金刚鹦鹉撒出不祥之兆的红豆,于是钦奇比林骂:“这些鸟就是如此,珠光宝气,外表光鲜,心肠黑毒!”库库尔坎说:“金刚鹦鹉用舌头搅乱神灵们的脚,使之弄错凉鞋,踏着右脚在左脚上的回声行走……”于是在红幕里有了不计其数的士兵,有了那最后一支箭,库库尔坎制造的战争,也欺骗了雅伊,,金刚鹦鹉告知的是:“你如果真想守住幻想,就听一听我黄羽毛的语言,电光石火间,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好让他的床不被占据,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新欢……”而在黑幕里,雅伊终于对库库尔坎说:“在太阳宫里,一切皆为谎言、流言,没有真相,什么都没有,只有个阔佬引领我们从晨至晌、自晌入夜、由夜及晨……天地之主,请告诉我,如此昼夜、昼夜、昼夜交替究竟有何用?百无一用。”
爱情变成爱情,幻想变成谎言,而金刚鹦鹉作为倒影城、魔力鸟,对雅伊说的话是:“你将与一个影像搏斗……”神之库库尔坎,统治之库库尔坎,也是一个影像,与影像搏斗的世界里是黄战士:“一旦库库尔坎到来,他会连忙闻一闻黄花,他优雅地弯下身子,好仔细闻闻她,闻闻让男人沉醉的女人味,然后握住茎秆将她带到婚床上,对她说情话;这时,黄花用手爱抚库库尔坎至尊的头发,直到他的脑门锃亮得如一面鏡子。”于是第三个循环里,黄幕里、红幕里、黑幕里,都是穿着黄衣、戴着黄头盔的钦奇比林在那里跳动,像那一个小球,被魔鬼附身,而最后的最后,是一败涂地的钦奇比林,是涕泗交颐的钦奇比林,而那口中不断重复的“雅伊,黄花!雅伊,黄花!雅伊!雅伊!雅伊”是最后的疯狂,疯狂之后,倒影城出现:“他慌忙撕扯衣裳,以尽快解开,接着从胸口掏出月亮。一枚悬于黑幕之上的金环陨落,不再移动。”
落幕,却是如石头般站立,却是永恒的照耀,黄花是武器,是信仰,是符咒,是寓言,却也在倒影城里返回,返回时间,返回家乡,返回父母,返回每一个古老却不曾泯灭的传说,从火山、幻影兽、文身女、太帽人和巫师,构筑的是一个激活图腾、信仰、文字、哲学、知识和战争的世界,但是当一切都变成倒影城的时候,镜像世界里的家乡是不是预示着一种新的开始?库库尔坎的循环,与其说是时间的最古老统治,不如说是时间如何在倒影城中成为另一种时间,它们是石头、玉米、河流和土地,它们是阳光、月亮、城市和集市,它们是永远存在的传说:“这些历史、梦境、诗歌,如此潇洒地混合了信仰、故事、一个秩序井然的民族的沧桑岁月以及一片强劲并始终跳动的土地上的鬼斧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