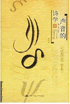 |
编号:W71·2060502·0738 |
| 作者:张闳 | |
|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3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 | |
| 页数:308页 |
书名很文化,内容有很诗学的一面,也有很当下的一面,如在此书的第三辑和第四辑中,有一些极为精彩的短文,像《革命中的医生》《霓虹灯下的上海》和《小资的精神幻象》等。张闳学的是医学,也是弃医从文。《革命中的医生》说的是两个外国医生的故事,不是白求恩和柯棣华大夫,而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医生,因这两个医生跟中国的读书人有一种亲缘性。《声音的诗学》是“先锋批评文丛”中的一本,同期出版的还有崔卫平的《积极生活》和敬文东的《被委以重任的方言》。
我猛地喊了一声:
“你好,百一花一山——”
“你好,孩—子—”
回声来自遥远的瀑涧。
——北岛《你好,百花山》
没有面对面,是隔着几张桌子的距离看见;也没有猛地喊了一声“张教授”,当然也没有得到转过头的回应;不是来自遥远瀑涧的回声,而是来自遥远的回忆——那是2006年5月初,一场全国范围和文学有关的活动正在举办,作为组织者之一的我,和作为嘉宾的张闳保持着某种距离,他参加了座谈会,他在研讨会上发言,在网络文学刚刚兴起的时代,张闳的确不是最合适的受邀者,甚至身为高等院校的教授来参加活动,纯粹是一次疗休养。这是一种误读?而保持距离的看见,似乎把记忆也带向了某种偏离的轨道:看见的是光头的张闳,看见的是带着美艳女人的张闳——是不是这些和形象有关的遐想就是一种低俗的臆想?
大约是因为没有和张闳有过面对面平等的对话,大约是缺失了文本之外解读个人的那些声音:既没有“猛地喊了一声”,也没有从瀑涧传来遥远的回声——连《声音的诗学》这本书上的签名也是批量购买图书之后批量签上去的。于是就如北岛诗中所说,在声音呈现的分离中,万物应和带来的是骚动不安,作为教授的张闳用一个个签名制造了在上的感觉;喃喃低语之后则是“手中的雪花飘进了深渊”,于是有了误读,有了臆想,有了偏差的记忆——当25年后回到这本有着张闳的签名的文本,对于“声音的诗学”的理解完全成为了一种遥远的回声。
以北岛的“声音”为样本,2006年之前写作了这本书的张闳认为,北岛这一代人的诗路历程,可以看做是一个时代的“自我意识成长史和精神档案”,《你好,百花山》的喊声和回应隔着遥远的距离,大自然没有与“主体”完全同一化,甚至异化为一个“他者”的声音,而且在张闳看来,这个“他者”完全是一个“父辈”,正是从这里开始,北岛开始制造声音神话,他喊出了“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个声音是曾经撒娇和哭闹的孩童喊出的独立的、自我的声音,它是向父亲发出的挑战;他写下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北岛对声音的自足及永恒性的信任,这是对“自我”成熟性的自信相一致的态度……但是,无论如何,北岛的声音世界里这个“他者”是永远带着影子的,他在自我反思中获得的“自我意识”,其实是因为发现了“自我”与历史之间的同谋关系,“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所以北岛要摧毁这种同谋关系,而最后的结果是摧毁了自我意识——上世纪80年代北岛离开中国,似乎在割裂这种和“他者”的同谋关系,在张闳看来,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北岛才成为自我声音的倾听者,“域生活将北岛抛掷在与世界的疏离状态中,也将他抛掷在语言的真空中。只能是自己成为自己的倾听者。”
张闳把作为一代人成长小说的北岛放在“抒情的荒年”专辑里,似乎也只有在北岛身上,那种自我倾听的意义才会凸显,声音的诗学才会成为可能——尽管一开始是以遥远的回声作为回应的。在这一专辑里,“抒情的荒年”是被大众传媒打扮成文学奇迹的舒婷成为“世纪末的诗歌口香糖”;是以今天派为代表的介入诗歌在追求“纯诗”中走向丧失自身艺术性的危险;是海子之死作为象征性事件而开启的“昏暗的诗歌”,“非非”的“晒谷场”、“口语”的“餐桌"、“知识分子”的“粮仓” 组成了这一诗歌现象;是民间派和知识分子派之间的争论制造的“分边游戏”,它是权力阴影下的闹剧……
但是,在“抒情的荒年”,张闳在批评诗人对“声音的诗学”自我丧失的同时,也批判了社会意义上的昏暗,也正是这种昏暗,使得原本具有自我意识能够发出声音的抒情诗人变得“贫乏”:1995年43岁的胡宽因慢性支气管哮喘逝世,他是在张闳眼里“只需通过诗歌的声音,我们就可能分辨出诗人的面貌”的诗人,但是诗人最后发出的是呼吸道里痉挛的声音,在“卡夫卡式”的疾病和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致命的疾病”中最后窒息了诗人;“新生代”诗歌运动先驱者之一的钟鸣,长期蛰居在诗人杜甫隐居过的地方,他出版的3大卷、150万字的《旁观者》是一部作者个人的“成长小说”,更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档案;“知识分子写作”倡导者和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的欧阳江河,把虚构的纯粹性看成是世界的最高真实,从而超越现实身份和立场的局限性;在萧开愚的诗歌里,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嚣,戏谑的嘲讽,夸张的吁告和充满异国情调的优雅,但是他的宽厚之心来源于悲悯,而这种带给诗人强大精神力量的悲悯是中国式的;小海不属于任何诗歌群体或帮派,但是,特立独行的小海用纯净的口语制造了声音诗学;还有蓝蓝,“蓝蓝的诗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蓝蓝关注的是生命中最脆弱的部分。”
“致命的呼吸”的胡宽、“旁观者”清的钟鸣、“虚构的立场”的欧阳江河,有着“简朴的力量”的萧开愚、“像河流一样抒情”的小海、“无奈叹息的美妙”的蓝蓝,张闳在“抒情的荒年”中为他们留着一个位置,而他们构成了荒年里不同的“声音诗学”——“荒年”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贫乏的诗人只是发出了零星的声音,那么这个时代为什么在整体上不再有北岛那样的喊声?为什么没有了声音的诗学也没有了倾听者?“沉默与倾听”是张闳对整个时代汉语写作困境的概括,他认为在这个时代,感官在萎缩,欲望在衰退,心志已荒芜,创造力已丧失,这种种的失落乃至堕落就在于写作已经不再是“代圣人立言”,而是变成了代权力立言、代君主立言——这就是“圣”的没落。
从字源学上解读,张闳说文解字:“聖,从耳,从口,表示一个人在倾听,并在言说。”在他看来,只有能听能言者,才能成为“圣贤”。倾听和言说,是圣的基本标准,也是最高意义,而在汉语文学的发展历史里,听与说都变成了问题史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史的起点是孔子,《论语》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的“圣经”,实际上却是一部孔子的教学记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提倡学习的重要性,却成为圣人之言的解释者,“尧舜时代的那种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声音,到了孔子这里变成了温柔醇厚的鹦鹉学舌;那种‘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奇观,变成了一种‘勃如战色,足蹜,如有循’的卑微。”张闳将此看成是圣人之“志”的沦丧和萎缩,而当权力不断渗透和强化,“圣”的没落便成为事实;相对于孔子“中心话语”,庄子的话语是“结构式”的,他是在证明言说的不可能性中为言说的可能性划出了疆界,这种双重性导致了“道”对言说的废止,在抽空了权力对言说的渗透之后,也抽空了自己的生命,这便是“道的空虚”;而在鲁迅那里,当他以倾听作为重建民族“自我意识”和言说机制的出发点,却忽略了欧洲精神文化中的理性主义,这是“听的误差”;还是鲁迅,他既是倾听者,也是言说者,但是在《野草》中,鲁迅却以一种带有自杀倾向的语言制造了恐怖主义的言说,最后的结果是言说者和敌人以及作为武器的语言同归于尽,这便是“言的窘迫”;从孔子建立的文化记忆机制导致个体生命本身的“遗忘”,到庄子关于“道”的记忆是对记忆本身的“遗忘”,再到鲁迅披露国民劣根性中的“记忆缺损”,再到寻根文学追忆集体的文化记忆而遗忘自身的生命感知,这种种的过程都导致了“记忆的缺失”。
圣已没落,道成空虚,听是误差,言在窘迫,记忆已缺失,这便是声音的“沉默”——但是在这样的声音问题史中,张闳还是听到了一些声音,那就是鲁迅发出的声音,尤其是在《野草》中,鲁迅以“自言自语”的方式表达者心声,这是这个民族所不曾有过的心声,是废除“恶声”之后的“新声”,“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张闳把这“声音”看成“是对个体生命本身的最高礼赞,是‘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最本原、最纯粹的生命歌唱是自我意识的“声音诗学”,但是并没有走向“代圣人立言”的目标,或者说,这样一种声音诗学在当代的先锋文学中就成为“自我意识”的练习,是想要摆脱“中心话语”的奴役,要寻找汉语文学言说更自由空间的努力,但是它是未完成的,是不定式的,甚至是一种涂鸦的“作业本”。
但这至少是一种努力,至少是对生命本身的体悟,而张闳的忧患并不仅仅在于这些,在一个“圣的没落”时代,沉默之后是“抒情的荒年”,荒年之后则是“感官王国”,“感官王国”之后则是“情欲时代的神话”——从沉默到荒年,再到“感官”,再到“情欲”,汉语写作的没落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建立赤裸的文本,它像一次次剥落了汉语文学身上的外衣,最后抵达的是肉体世界。在张闳看来,“感官王国”里有着莫言小说建立的关于生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肉体性的“自我”;是从鲁迅作品作为祭品的血到余华作品作为物品的血和作为商品的血,“血的精神分析”最后没有了精神;是李洱的“虚幻之约”、行者的“南阳梦”、刁斗现实生存的“证词”和墨白“偶然的命运”构成的“虚构与梦幻”世界……而在张闳所描绘的“情欲时代的神话”中,“霓虹灯中的上海”成为当下文化粗鄙又俗艳的象征;卡布基诺、哈根达斯、BOBOS为代表的品牌消费是全球化可以制造出来的饮食神话;卫慧、九丹的小说,小女人散文、70年代后写作等策划下的文学运动完全是一种骗局;还有卡拉OK的空洞声音,流行歌曲对革命词汇的解构,全球化这个幽灵带来的欲望和想象,带来的是幻觉,更是将声音的诗学彻底解构:一种声音的标本是电影配音,西方声音的汉化,汉语声音的装配,虚构了西方的语境和言说艺术,“由配音所构建起来的虚拟的声音世界及其所映射出来的西方幻象,像雾气一样迅速地消散在新时代的喧哗与骚动中。”
从倾听沉默到抒情的荒年,从感官王国到情欲神话,张闳带着批判的目光,审视着汉语文化“声音的诗学”被湮没的当代困境,这种审视是俯视意义的,作为学者、教授,他当然自我定位为知识分子,但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书写有着太多仿写的痕迹,“声音的诗学”是不是让人想起“梦想的诗学”?“血的精神分析”是不是对于“火的精神分析”的一次摹写?而“声音”也是他试图恢复“代圣人立言”的宏大叙事,“应该努去恢复我们古代‘圣人’的那种‘耳’和‘口’的功能,恢复‘圣’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最古老的智慧和荣誉,并同时抹去‘权力’的污迹。”但是当站在高处,当俯视众生,这种“圣”的形象以及“代圣人立言”的方式依旧是一种“权力观”,张闳希望重建的“声音的诗学”也是在他的言说中希望他人倾听,“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如上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