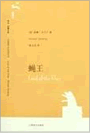 |
编号:C38·2120720·0905 |
| 作者:[英]威廉·戈尔丁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06年8月 | |
| 定价:13.00元 亚马逊9.40元 | |
| ISBN:9787532740109 | |
| 页数:236页 |
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是充满着残杀和死亡,在历史被虚构的情境中,活着的人如何继续活下去,荒无人烟的孤岛里存在一个空白的秩序,而只有人的到来才改变了这里的一切。未来的核战争,孩子的世界里没有童趣,没有善良,在世外桃源般的、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孩子们从最初的齐心协力,变为某种争夺,由于害怕所谓的“野兽”分裂成两派,以崇尚本能的专制派压倒了讲究理智的民主派而告终。恶的本性统治了一切,也主宰了一切,威廉·戈尔丁将抽象的哲理命题具体化,猪头说:“别以为野兽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那颗布满苍蝇的猪头象征人性恶和心中的黑暗世界?由于他的小说“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198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戈尔丁的寓言,总是表现“人心的黑暗”这一主题,就像《蝇王》中所说:“恶之出于人,犹如蜜之出于蜂!”
《蝇王》: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
还是一只猪,《蝇王》的封面里的一头猪,仰着头的一只猪,抬起了脚——它没有手,却可以说话,喃喃自语也好,发号司令也罢,总之,猪的世界里可以有尊严有理想有道德,甚至还有荣耀,仿佛是统治者。但其实是一场虚构,猪只是一个被捕捉的对象,一个举着木棍被赶进包围圈的对象,甚至是被屠杀被食肉的对象,而最后一定是作为被人类征服的野兽之一,成为一个在荒岛上的象征。
“杀野兽呦!割喉咙呦!放它血呦!”这是人类对它的屠杀口号,杰克带领的孩子们用他们的勇敢杀死了野猪,在一个荒岛上,只有野猪是和孩子们一样,是活的,是见证着一种荒芜和孤独,也见证着力量的此消彼长的斗争,而他们是野兽,人类之外唯一的野兽,所以,它们背对着人类,“别梦想野兽会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这是猪头说的话,其实只是一个暗语,人类可以征服野兽征服一头野猪?或者说,只有征服野兽征服野猪才会成为真正力量的象征,真正成为一个统治者?猪头在嘲笑,也即是在否定,那布满苍蝇的猪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巨大的象征,不是捕杀不是食用,而是一种证明,一种规则,一种恶,以及耻辱。
好吧,如果一定要把野兽当成是一个象征,那么荒岛这样的乌托邦是必须存在的。戈尔丁设计了一个寓言,不存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存在的荒岛,不存在的孩子们的斗争,这是一个缺少大人的世界,缺少大人就是缺少规则,“这是一个岛。至少在我看来是一个岛。那里是一条伸进外海的礁脉。兴许这儿没大人了。”大人不在谁听谁的话?这是一个世界走向秩序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们都是孩子,十二岁还多几个月的拉尔夫,那些同龄的孩子,更小的约翰尼、萨姆和埃里克(双胞胎)、梅瑞狄、莫里斯、罗杰,或者除了年龄之外,还有合唱团与否的身份,但最主要的是该听谁的话,或者谁是头儿?投票表决?这是文明社会的一种制度印记,在孩子们身上有着初步的萌芽,但是投票缺乏说服力,缺乏必要的物质证明,所以,海螺出现了。
这是召集这些纷乱的孩子们走在一起的东西,这是传递声音的东西,所以海螺是一个规则,从一开始大家可以接受的规则的一部分,所以拉尔夫因为海螺而成为一个头儿,“这贝壳就叫海螺。我把海螺给下一个要发言的。他就拿着海螺说话。”用海螺说话,用海螺召集,这就是最初的秩序建立,而秩序和规则是文明人的一个符号,是区别于野蛮人的标记,“海螺时代”是从文明社会而来的孩子们在荒岛上的第一个时代,“咱们必须有规定照着办。咱们毕竟不是野蛮人。”对立的野蛮人当然没有秩序没有规则,没有海螺,即使有海螺,也只是一种漂亮的动物躯壳而已,它的身上不具有文明社会的印记。
有了海螺建立的秩序,是不是会这样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会不会在头儿下会有等级会有生产会有制度?在初期,这些东西都在慢慢产生,比如分配谁该干什么,比如建造窝棚比如大家开会商讨,但是随着社会的秩序逐步建立,新的不同声音就会出现,起先,他们在没有成人的荒岛中,享受到了最简单的快乐和自由,面朝大海随意游玩,那种旧有生活的禁忌已经无影无踪,但是存在过的文明法则也带来了某种强有力的统治力,这包括在荒岛之外世界里“有着父母、学校、警察和法律的庇护”,包括一些物质的文明成果,“再来一架飞机,再来一台电视,还要一部蒸汽机呢。”这是孩子们的心愿,物质文明同样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一个部分,在荒岛中一切的秩序都需要以文明社会作为模板。
但是,在荒岛上,在孩子们反面的并不是这些物质文明,而是存在着的一种野蛮性,一种最原始的人类征服欲望。海螺是一个规则,吹海螺开会、决定事情、喝水、看好火建窝棚,以及选一个地方作为厕所,等等不断在新的规则建立下完善秩序,但并不是绝对的,或者说不是唯一的,拉尔夫是一个先行者,第一个使用规则而成为“头儿”,但是杰克就在荒岛生存中提出了新的规则。在荒岛中他带领孩子们一起猎杀野猪,用暴力实现了物质的供给,在一个人类可以征服的世界里,杰克也同样希望成为一个规则的制定者,从而成为一个“头儿”成为统治者。特别是在看守火堆的过程中,因为捕猎野猪而使烟火熄灭错过了大海经过船只的注意,拉尔夫和杰克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一个是先行的秩序拥有者,一个是暴力的实施者,规则自然产生了分歧,而且在杰克看来,拉尔夫不是一个猎手,“他从没给我们弄来过肉”,所以“指望别人任他摆布”就成为一种扯淡。正是这种怀疑论的出现,使荒岛上的孩子们分成了两派:以拉尔夫为首的海螺派和以杰克为主的征服派,“因为规则是咱们所有的唯一东西!”所以,在这种分裂中,规则实际上已经被瓦解了,而海螺时代也走向了覆灭。
在人类的对面是什么?是野兽?是野猪为主要对象的野兽,它们永远没有规则没有秩序,它们只要在阳光下享受生活,它们只要在追捕时本能的反抗,甚至,在戈尔丁的叙述中,被猎杀的猪头还在嘲笑孩子们,在西蒙的目光中,“猪头像被逗乐似的咧着嘴巴,它无视成群的苍蝇、散乱的内脏,至无视被钉在木棒之上的耻辱。”人类的反面绝不是野兽,绝不是野蛮,绝不是黑暗中的恐惧,而是多重的规则,多重的秩序,多重意味着没有唯一没有最高标准,也就意味着世界的不同走向,所以拉尔夫和杰克之间的争斗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中的必然矛盾,“哪—个好一些?——是法律和得救好呢?还是打猎和破坏好呢?”在荒岛上,其实永远没有对与错,永远没有输和赢,对野兽的恐惧其实最后变成了一种人类欲望的恐惧,杰克偷走了火种,抢走了猪崽子的眼镜,象征社会文明的眼镜实际上走向了不可收拾的命运,拉尔夫对于杰克也从起初的合作者变成后来的分歧者,最后变成了对立者,“你是野兽,是猪猡,是个道道地地的贼!”杰克成为了新的野兽,人类的对立面以人类自己作为标志物而开始了恶的走向。
海螺被巨石砸碎了,海螺时代真正走向了终结;猪崽子失去了点火的眼镜,而且一块巨石砸死了猪崽子;走向山顶寻找野兽的西蒙在雨夜被当成了野兽而被乱棍打死……野兽其实并不存在,对野兽的那种恐惧也只是人类对自己的恐惧,那只猪头从来不说话,甚至它连最初的象征意义也被解构了,“猪头像先前的海螺那样地闪着微微的白光,似乎在讥笑他,挖苦他。一只好奇的蚂蚁在一只眼窟窿里忙碌,除此以外猪头毫无生气。”只是猪头,只是死去的野蛮动物,而文明人一样是在野蛮的荒岛上自相残杀,“罗杰把一根木棒的两头都削尖了。”在巨大的不安中,人类被自身制造的恐惧所笼罩。而当拉尔夫在荒岛中被这样的自相残杀而走投无路的时候,军官出现了。
这是成人世界的介入,军官说,“在闹着玩吧,”孩子们在荒岛的斗争最后还是一种玩乐。在成人世界的规则下,海螺、眼镜、两头削尖的木棒也都还原为一种游戏的物件,所有的规则属性重新被界定,也只有成人,才可以带领孩子们告别荒岛告别一种乌托邦,而当军官问“谁是这儿的头?”时,拉尔夫响亮地回答“我是”,首领在没有规则的最后,也只是具有游戏意义,像过家家一样,军官宣告了游戏的结束,野兽永远不会出现了,离开了荒岛重新进入成人的秩序,重新适应“旧生活的禁忌”,重新“有着父母、学校、警察和法律的庇护”。
这像是一个轮回,但是在经历了荒岛生活之后,人性的恶变成了被暴露的一部分,“拉尔夫在这伙孩子当中,肮脏不堪,蓬头散发,连鼻子都未擦擦;他失声痛哭: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为忠实而有头脑的朋友猪崽子坠落惨死而悲泣。”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是不是就是杰克为代表的征服和自我欲望的膨胀?是不是海螺时代的规则一定是不可破坏一定是最文明的规则样本?其实拉尔夫的胜利并不是值得赞扬的,那种头儿式的对秩序的维护是文明的象征,但却不是最可靠和最安全的手段。
如果没有军官的出现,在荒岛的争斗可能就是拉尔夫的失败而告终,那么最后拉尔夫就会是杰克的一个被征服对象,或者说就会成为那个猪头,变成“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那么文明就会走向反乌托邦,走向恶的极致,所谓”蝇王”,也就是这样一种象征,在猪头上的象征,“蝇王”即“苍蝇之王”,源出希伯来语“Baalzebub”,在《圣经》中,“Baal”被‘当作“万恶之首”,在英语中,“蝇王”是粪便和污物之王,因此也是丑恶的同义词。“LORD OF THE FLIES”,戈尔丁说过:“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在极致的恶,极致的野蛮面前,所谓的文明就是“一个无知的傻小子”。一个缺少秩序和规则的荒岛,就会成为一个乌托邦,缩写着人类文明的进化史,而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矛盾对立其实贯穿其中,直到新的秩序和规则的出现。“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这是一九八三年戈尔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价,其实所谓的神话,也即是发现了人身上的那种野蛮性,那种猪头一般的恶,正如西蒙所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而他自己最后也便成了这样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