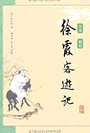 |
编号:E26·2190320·1546 |
| 作者: [明]徐弘租 著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05月第1版 | |
| 定价:35.00元当当17.50元 | |
| ISBN:9787549381296 | |
| 页数:384页 |
徐霞客二十二岁起在母亲的资助下开始云游四方,游历祖国的山水,一直到五十六岁过世之前几乎都在进行旅行考察。在这三十四年间,他的脚步东到浙江普陀,西到云南腾冲,北至河北盘山,南到闽奥一带,覆盖了现在十九个省、市(区)。《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创作的一部散文游记,在原稿的基础之上,王忠纫手校、季梦良续成稿本,成书于崇祯十五年。该书按日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广泛系统地探索和记载岩溶地貌的地理学巨著,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此外优美的文字也使之成为文学佳作,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徐霞客游记》:模范山水,积记成帙
乙卯八月十四日 三空先具小食,馒后继以黄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软更胜于糯粉者;乳酪椒油,蔓油梅醋,杂沓而陈,不丰而有风致,盖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约而来。(以下缺)
缺省的记录,仿佛让“乙卯年八月十四日”成为徐霞客最后的时间,吃着馒头小食,嚼着黄黍之糕,当滇游之行完毕,徐霞客似乎还在美食中回味着一路的辛苦与喜悦,但是为什么之后再无日记?当自己的游记本文处在缺省状态,或许只能从他人的叙说中勾勒徐霞客的最后时光。
好友季梦良记叙中说:“玉堡纫先生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后,俱无小纪。’余按公奉木丽江之命,在鸡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则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垄《志》之日也。公另有《鸡山志》摘目三小册,即附载此后,而《丽江纪事》段及《法王缘起》一段,并附见焉。”季梦良也是从玉堡纫那里转述而来,徐霞客回到鸡足山之后,就开始修山志,历时三个月,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而陈函辉在《徐霞客墓志铭》中述徐霞客回家前最后这段生活:“霞客游轨既毕,还至滇南。一日,忽病足,不良于行。留修鸡足山志,三月而志成。丽江木守为饬舆从送归。转侧笋舆者一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黄冈侯大令为具舟楫,六日而达江口,遂得生还。”时间和季注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修完鸡足山志是徐霞客生命中做完的最后一件事,而志成时它身体已经不行了,那年的徐霞客55岁,最终被云南丽江守派人护送,经湖广黄冈返回家乡,第二年就去世了。
“归而两足俱废”这是季梦良在序中对徐霞客重病的描述,两足俱废,所以无法行走,也就宣告了他一生纵横祖国河山的行程画上了句号,这最后一次远行历史近5年,当“以下缺”遗憾终止了游记的记录,当“两足俱废”无情地终结了他游走之路,徐霞客是不是完成了他的计划?显然没有,在《游九鲤湖日记》中,徐霞客说:“浙、闽之游旧矣。余志在蜀之峨眉、粤之桂林,至太华、恒岳诸山;若罗浮广东东樵山、衡岳,次也。至越即浙江省之五泄,闽之九漈闽方言瀑布,又次也。然蜀、广、关中,母老道远,未能卒游;衡湘可以假道,不必专游。”而在《游嵩山日记》中他再次讲到了他的游志:“余髫年蓄五岳志,而玄岳出五岳上,慕尤切。久拟历襄、郧,扪太华,由剑阁连云栈,为峨眉先导;而母老志移,不得不先事太和,犹属有方之游。第沿江溯流,旷日持久,不若陆行舟返,为时较速。”从这两个计划里可以看出,徐霞客都把峨眉列在计划里,而未能远游的原因也都归结于母亲,而实际上,“母老志移”并非是徐霞客的一种幽怨,他的母亲一直支持徐霞客,对于徐霞客“间奇于名山大川”的志趣,更给予有力的支持,“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岂令儿以潘中雉、辕下驹坐困为?”母亲亲手为霞客制作“远游冠”,以壮行色;每次霞客出游归来,“为言各方风土之异,灵怪窟宅之渺,崖壑梯蹬之所见闻,有令人舌挢汗骇者,母:枣反大惬。”为了打消霞客出游的顾虑,她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还豪兴满怀,和徐霞客一起游了荆溪、勾曲。
所以,母亲的一贯支持是徐霞客游走神州的一种动力,而当当初的计划未能如愿,最后在“两足俱废”中被人抬回了故乡,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某种宿命,从第一次出游,到记下游记,“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闻此地於菟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这“癸丑之三月晦”的第一段文字开始,徐霞客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行程,也从此开创了旅行实践者的伟大历程,他用脚行走,用脚丈量,东渡普陀,北历燕冀,南涉闽粤,西北直攀太华之巅,西南远达云贵边陲,当时十四省,即现在的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十六个省区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三十多年间,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中留下了他的足迹。
但是从第一句中听闻有“於菟夹道”,到最后一篇的缺省,对于徐霞客来说,似乎某些东西已经冥冥注定,这几十年的游离到底留下了什么?这一生的旅行到底获得了什么?族孙镇谨作序中说:“族祖霞客公,生有游癖;凡屐齿所到,模范山水,积记成帙,积帙成书,昔人所折称为千古奇书者此也;惜未脱稿而公卒。”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模范山水”,成为千古奇书,并不能概括徐霞客的功绩,而和书一样,徐霞客的非凡之举在于“作者之精神”,或者说“游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内动力作用下,徐霞客凭着着那一双脚,以无人可匹敌的勇气与毅力,以前无古人的不屈精神,让那些模范山水踩在自己脚下,也呈现在公众面前。
游历山水,用脚丈量,对于徐霞客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获得书斋之外的全新体验,他游雁宕山天聪洞时看到一道光从洞中射入,别有意境,发出了“锐峰叠嶂,左右环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观!”的感慨;他对于黄山松的评价是:“高者不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髲,盘根虬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而两次游黄山带给他的都是不一样的体验,第一次见到黄山诸峰,发出了“各夸胜绝”的惊叹,而第二次再次探访黄山奇览,一切尽收眼底,“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擥同揽。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直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有一种“狂叫乱舞”的兴奋感;在他的笔下,庐山的桃花峰“铮铮比肩,然昂霄逼汉,此其最矣”,太和山诸峰“诚天真奥区也”,武功山的雾是“奇胜”,而五台山悬空寺则是“石崖悬绝中,层阁杰起,则悬空寺也,石壁尤奇”。
那些名山大川似乎在徐霞客抵达、描写之后才发现为一种奇景,徐霞客说黄山是“薄海内外之名山,无如徽之黄山”,后被当地人引申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他认为武彝山“诸峰上皆峭绝,而下复攒凑,外无磴道,独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岩更为奇矫也。从其中攀跻登隐屏,至绝壁处,悬大木为梯,贴壁直竖云间。梯凡三接,级共八十一”而龙门石窟则是:“伊阙连冈,东西横亘,水上编木桥之。渡而西,崖更危耸。一山皆劈为崖,满崖镌佛其上。”历时10天游历的华山在他笔下被描写成:“两崖参天而起,夹立甚隘,水奔流其间。循涧南行、倏而东折,倏而西转。盖山壁片削,俱犬牙错入,行从牙罅中,宛转如江行调舱然。”五台山更是奇绝:“闭魔岩在四十里外,山皆陡崖盘亘,层累而上,为此中奇处。入叩佛龛,即从台北下,三里,为八功德水。”其实在大山大川之外,即使是一些小景,即使是当地的风情,只要有着独到之处,也会让他兴奋不已,《粤西游日记》中记载他坐在木盆中,随竹筏进入山洞,“始由洞口溯流,仰瞩洞顶,益觉穹峻,两崖石壁劈翠夹琼,渐进渐异,前望洞内天光遥遥,层门复窦,交映左右。”让他有一种超然的感觉,而“从澄澜回涌中破空濛而入”时,则想起李白“流水杳然,别有天地”,于是自己也仿佛成了谪仙人。而在《江右游日记》中他记载,当一日行了三十五里终于休息时,主人与自己饮“村醪”,“竟忘逆旅之苦”,忘却了一切的辛苦,而当处在寂静山村的时候,“但彻夜不闻一炮爆竹声,山乡之寥寂,真另一天地也。”
 |
|
徐霞客:模范山水的模范行者 |
对于徐霞客来说,旅行的目的和意义其实都在这不可知的过程中,而对于交通工具、信息度不发达的当时来说,离家远足很多时候甚至是一种冒险,在漫长的旅途中,徐霞客经历了数不清的自然风险,再访雁荡山时,他和同行仲昭同登天聪洞,东面看去有两个圆洞,北面望过去则有一个长洞,为了探知鹫津,徐霞客到下面的寺庙里借来梯子,开始了登洞的努力,“负梯破莽,率僮逾别坞,直抵圆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则斫木横嵌夹石间,践木以升;复不及,则以绳引梯悬石隙之树。”树木够不着的地方,则用梯子接住,梯子不够的地方,则用树枝相济,而一旦“梯木俱穷”,便用引绳,如此费力,最后才到了长洞,那时已经是中午了。在登恒山山崖的时候,“满山短树蒙密,槎桠枝柯歧出枯竹,但能钩衣刺领,攀践辄断折,用力虽勤,若堕洪涛,汩汩不能出。”最后只能靠着一股蛮劲,才最后登上危崖。
每次遇到这些困难,徐霞客总是有一种“余欲入”的执着信念,《楚游日记》中记载探险秦人洞,“计匍匐水中,必口鼻俱濡水,且以炬探之,贴隙顶而入,犹半为水渍。”后来必须泅水而入,但是泅水又无法传递火把,于是徐霞客只好放弃,“出洞,披衣犹觉周身起粟,乃爇火洞门。”而在《楚游日记》中记载探险麻叶洞的情境,却是冒险抓住了一切可以进入的机会,一开始没有人做向导,因为他们传说:“此中有神龙。”有的人则说:“此中有精怪。非有法术者,不能摄服。”最后用重金才找到一个向导,而向导却认为徐霞客只是一个儒士,“予以为大师,故欲随入;若读书人,余岂能以身殉耶?”徐霞客一不做二不休,到村子里把一切行李都寄存下来,抛却留恋之想,和向导一起进入洞中,而外面沾满了村民,无一敢进洞,于是,“余两人乃以足先入,历级转窦,递炬而下,数转至洞底。洞稍宽,可以测身矫首,乃始以炬前向。其东西裂隙,俱无入处,直北有穴,低仅一尺,阔亦如之,然其下甚燥而平。”过得数关,终于“穿窍而出,恍若脱胎易世”,而洞外的人对他说:“前久候以为必堕异物,故余辈欲入不敢,欲去不能。想安然无恙,非神灵摄服,安能得此!”徐霞客对此答复说:“吾守吾常,吾探吾胜耳,烦诸君久伫,何以致之!”
不论是负梯破莽也好,还是胸背相摩匍匐前行,不论是泅水入洞,还是抛却一切杂念,对于徐霞客来说,“吾守吾常,吾探吾胜”便是前进的唯一动力,但是在旅行途中,除了自然风险之外,还有途中的各种历险,《游嵩山日记》中记载:“从南寨东北转,下土山,忽见虎迹大如升。”《楚游日记》的记载到了云嵝山时,听人说两年前这里有一只老虎抓走了一个僧人,“于是僧徒星散,豺虎昼行,山田尽芜,佛宇空寂,人无入者。”后来徐霞客遇到了路人,那人“为君前驱”,“各持械,赍火冒雨入山。”才避免途中可能遭遇老虎;而在《楚游日记》中,在登山之时,也看到了疑似虎穴的地方。《滇游日记》中记载,戊寅九月初二日在黔滇交界处,“忽闻西岭喊声,寨中长幼俱遥应而驰。询之,则豺狼来负羊也,幸救者,伤而未死。夫日中而凶兽当道,余夜行丛薄中,而侥幸无恐,能忘高天厚地之灵祐哉!”大约是和虎狼豺豹距离最近的一次。
除了猛兽可能出现之外,还有乱世的那些盗匪,《楚游日记》中记载在路边听到人说有大盗二百余人从北面过来,大家都逃跑到后山避难,“余与顾仆复携囊藏适所游穴中,以此处路幽莫觉,且有后穴可他走也。”后来听说“贼从章桥之上,过外岭西向黄茅矣”,才打消顾虑;《楚游日记》亲眼见到被盗匪劫杀的渔船:“二十里,过大鱼塘,见两舟之被劫者,哭声甚哀,舟中杀一人,伤一人垂死。”《粤西游日记》中徐霞客在去往投宿的旅店时,看到路边都是“虞警候望的警戒”,而这些所谓的“麻兵”其实是土司汛守盘查往来之人的兵士,平时就和那些山贼很熟,所以这一次奉调过来抓匪,麻兵就设计了一计,“故群贼縻遵者束缚,依从一人斩之,以首级畀麻兵为功,而贼俱夜走入山,遂以‘荡平’入报。”在粤西别处,听说的故事更加恐怖:“流贼七八十人,夙往来劫掠村落,近与官兵遇,被杀者六人。旋南入陆川境,掠平乐墟,又杀数十人。还过北流,巢此庙中,縻诸妇女富人,刻期索赎,不至者辄杀之。”
但是这些似乎都在传说中发生,徐霞客尽管有所惧怕,但毕竟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但是湘江遇盗,则在他的游历生活中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当时徐霞客和好友艾行可、仆人顾行和随从静闻正坐船于湘江中,刚下过一场雨,月亮出来了,从岸边小解完之后再回船上的徐霞客便听到了群盗的喊杀声,只见火炬刀剑发出的寒光,情急之下徐霞客被闯进来的盗贼掀翻到江中,入水余最后,足为竹纤所绊,竟同篷倒翻而下,首先及江底,耳鼻灌水一口,急踊而起。”后来从水中回到船上,盗贼已走,但是艾行可落水身亡,仆人顾行身中四刀受重伤,好友静闻和尚则失踪,后来找寻半日和静闻相逢,得知静闻为保护血写的经书冒死留在船中,抢救了一些衣物和书籍资料。徐霞客不为困难所动摇的决心,最终感动了他的“他乡故知”金祥甫及衡阳当地人戴宇完、刘明宇,徐霞客以家中田产为抵押,从金祥甫处借得“二十金”,于三月十四日重新踏上旅程,经过十天旅程,于三月十三日抵达湖南永州。
“风雨凄其,光景顿别,欲为《楚辞》招之,黯不成声。”徐霞客的悲伤并不只是艾行可被杀死,而是一种不祥的感觉疯狂袭来,经历了此次事件之后徐霞客也得了病,“饭后余骤疾急病,呻吟不已。”而静闻因为拼死护住《法华经》而受伤,到了南宁崇善寺时生命已垂危,静闻只有一个愿望,“我志不得达,死愿归骨于鸡足山”那就是让徐霞客把他的骨灰和《法华经》带到鸡足山。静闻圆寂之后,“为之哀悼,终夜不寐”,返回崇善寺,“余谓辨公,乞其南为静闻穴。辨公请广择之。又有本公塔在岭北,亦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师为便,议遂定。静闻是日入窆。”之后,徐霞客千里跋涉,终于完成了静闻的遗愿。
不管是自然山川之险,还是猛虎、盗贼之险,徐霞客似乎并没有与退缩,“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三次遇盗、四次绝粮,这些惊世骇俗的野外考察生活,非但让徐霞客收获了不同的体验,更在于游历中对山川的考察,得到了第一手的知识。徐霞客行程经过的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一带,正是典型的石灰岩地貌区域,徐霞客对沿途见到的石灰岩地貌的种种特征,如“铮铮骨立”的石山,“攒出碧莲玉笋世界”的峰林,如“坠壑成井,小者为眢井,大者为盘洼”的圆洼地,如“漩涡成潭,如釜之仰”的落水洞,以及“伏流潜通”、“水皆从地中透去”的伏流现象,无一不作具体细致的考察记述。对于形形色色的石灰岩洞穴,徐霞客不仅描述其瑰丽雄奇的景观,而且分析其成因,考察其方位,研究其结构,经过长期、大量的观察,他明确地指出了石钟乳的成因:“崖间有悬干虬枝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在岩溶地区的长途考察,使徐霞客深刻体会到“水”在形成这种特殊地貌中的重要作用。他记述岩溶漏斗洼地、伏流等现象道:“岭头多漩涡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为并,深或不见底……始知山下皆石骨玲珑,上透窍,辄水捣成井”;“透穴……皆平地下陷,或长如峡,或圆如井……下则渊水澄澈,盖其地中二三丈以下,皆伏流潜通,其上皆石骨嘘结,偶骨裂土进,则石出而穴陷焉”。
除此之外,徐霞客还实践辩证了一些讹传的东西,在雁宕山考察时,他从《大明一统志》》上获知:“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但是第一次到雁宕山,发现“今山势渐下,而上湫之涧,却自东高峰发脉,去此已隔二谷”壬申年,他与与族兄徐仲昭“再访雁山”,登上去之后,发现:“(雁湖)而水之分堕于南者,或自石门,或出凌云之梅雨,或为宝冠之飞瀑;其北堕者,则宕阴诸水也,皆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云。”仙女峰讹传为会仙峰,武彝山“杜辖岩”讹误传为睹阁,军峰被传为文笔峰,这些错误的地名,徐霞客一一给予纠正,另外,在云南“盘江考”,也以极其认真的态度,辨析了《一统志》中记载的说法是错误的,“彼不辨端末巨细,悍然秉笔,类一丘之貉也夫!”他认为里面的三处错误的原因,“盖惟南宁府西左右江合流处为合江镇,是直以太平府左江为南盘,田州右江反为北盘矣。”
对于徐霞客来说,考察中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当属《江源考》,他在文章中提出的疑问是:“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眠江经成都到叙州府,不到一千里,金沙江流经丽江、云南、乌蒙府到叙州府,共有二千多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徐霞客明确提出了“非也”的结论,他认为,云南各种志书都没有写几条河的出入不同处,不知悉它们是一条江还是两条江,分在北方还是分在南方,又从哪里来辨明它是不是长江的源头呢?而《禹贡》中有“岷山导江”一文,就是把长江的源头归为岷江,徐霞客通过考察认为,“岷流入江,而未始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为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蕾,经黎、雅与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长于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推翻了“岷山导江”的说法,提出了“以金沙为首”的观点,同时,他认为,“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不与河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远。谈经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这样一种实证主义的观点和实践,对于中国地理的科学考察树立了榜样。
徐霞客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即使是孤绝,即使是个人的志向,甚至最后因“两足俱废”而告别行者生涯,告别生命历程,但是一种记录,一种书写,是超越身体之上的不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徐霞客无疑是实践认知的一个开拓者,后辈所说“夫是书之名世传世,均非予小子之所敢知,要使作者之精神不澌灭于煨烬之余,更不灭没于妄庸之手,是则后人之责所万不获辞者也”,大约是“积记成帙,积帙成书”的一种意义,而从游记还原徐霞客的历程,或许也是在还原“模范山水”,模范山水,模范行者,是为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