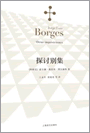 |
编号:E63·2160313·1279 |
|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7月第一版 | |
| 定价:35.00元亚马逊14.70元 | |
| ISBN:9787532768035 | |
| 页数:273页 |
收录《长城和书》、《帕斯卡圆球》、《柯勒律治之花》、《时间与约·威·邓恩》、《天地创造和菲·亨·高斯》等三十五篇,是博尔赫斯对他所读过的钟爱的书,对他钟爱的作家,作出的个性化评论。在博尔赫斯论述相关的作家作品时,我们既可以读到那些作家作品的风貌,更可以读到博尔赫斯个人的见解。我们看到他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追踪卡夫卡的美学先驱,从济慈的诗句中找寻个体与群体的时空联系,从霍桑和爱伦·坡那儿发现了幻想与真实相碰撞的心理轨迹,这些不囿成见的审美认识总是那么新颖而生动,显示出某种超前的感知。《探讨别集》就是博尔赫斯对他心目中的好作家好作品的评论集。
《探讨别集》:索要一枝花作为信物
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
——《时间的新反驳》
真实的世界其实“只要一本书就够了”,从最小处的一句话开始,第268页,从上往下是第9行,而从下往上是第5行,从句号开始到句号结束,但是句号并不是终结,往下是《基路伯式的漫游者》第六卷第二百六十三首诗的引语:“朋友,这也已足够。倘若你想多读,就去,自己会成为文字和本质。”再往下是“陆经生 译”的落款注释,一种附带,却完全在解读关于世界的不幸和我的不幸;如果往上,在句号之前,是博尔赫斯的另一句话:“时间是我的构成实体:时间是一条令我沉迷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时间是一只使我粉身碎骨的虎,但我就是虎;时间是一团吞噬我的烈火,但我就是烈火。”也是句号,完整的句子,似乎在诠释那个完整的我。
我就是博尔赫斯?我就是真实世界里的博尔赫斯?很不幸,这或者只是一个名字,连“豪尔斯·路易斯”也省略了,不幸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似乎就是陷入了某种“唯名论”的误区,所以一个名字,一种世界,就是为了证明真实的存在。其实,不管是第268页的句子,还是“陆经生”的译者,或者是《基路伯式的漫游者》的引语,其实都被纳入了“一本书”的唯一性里。这是一九四四年发表在《南方》杂志第一百一十五期上的文章,即使一九四六年曾做过修订,但当时间成为一种历史的时候,它应该是真实的。当然,从第268页回到卷首,回到封面翻过的背后,是关于“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简介,全称的名字,后面是放在括号里的数字,1899-1986,生卒年份完整地成为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关于他的出身,关于她的著作,关于他的经历,以及关于她的逝世,一览无余;而如果文字还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全称的名字上面的照片却指向了最真实的存在:右手靠在拐杖上,左手又放在右手上,而下巴则抵住了双手,眼睛以一种平视略微仰视的方式看待前面的一切。
四角方方的影像,四角方方的博尔赫斯,目光必定是沿着框子向外延伸,像是一种穿越,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四年,又从一九八四年到了二〇一七年——确定的时间,和四角的影像、全称的名字、具体的文字,构成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构成了一个博尔赫斯的我,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自己会成为文字和本质。”文字和本质,其实并非需要如此认真的方式寻找证明的线索,其实博尔赫斯在句号之前就已经讲清楚了什么是本质:当时间是河流,我就是河流。于是,时间是吃掉我的老虎,我也是老虎,时间是吞噬我的烈火,我也是烈火——我在世界中,我在时间里,我就是本质。
“在我以前没有时间,在我以后没有存在。时间与我同生,时间也与我同死。”丹尼尔·冯·切普科的这句话也是对于“我在时间里”的最好注解,时间在我出生之后成为时间,时间在我死亡之后没有时间,时间因为我而存在,同生同死的意义就在于我就是我。但是很不幸,时间在一九四四年的唯一之后为什么会有一九四六年的修订?时间在一九八四年我的逝世之后为什么会存在?时间在二〇一七年的时候是不是只剩下被阅读的名字?不幸其实就在这一篇文章的题目里:时间的新反驳,“这个标题是对逻辑学家们称之为语词的怪物的一个儆诫,因为说它是一个新(或旧)的对时间的反驳,就意味着给它加上一个时间类的谓项,而这个谓项又重申了主项想驳倒的概念。”
新反驳,是相对于旧反驳而言的?就像一九四六年的修订是建立在一九四四年书写的基础之上的,时间类的谓项区别了新与旧,区别了一九四六年与一九四四年,但是谓项总是相对于主项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那个不幸的博尔赫斯,那个我,才是不变的主体,当我成为唯一成为自己,而时间就是我、我就是时间的等式,就是要把这新与旧的区分抹杀,就是要把世界带向一个真实的存在。时间不变,其实意味着时间在持续性中的不变,时间在我的世界里的不变,此一种不变的时间当然是为了反驳那一种变动的时间,贝克莱的唯心论和莱布尼茨的不可识别的同一性原理是博尔赫斯反驳的支持理论,“存在就是被感知,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存在于感知它的思维之外。”这个唯心主义的观点突出的是感知,感知在贝克莱那里可能是那个无处不在的上帝,但是感知存在作为人的一种意义,它提供了关于时间同一性中灵魂的作用,只有活的灵魂才能持续感知存在,而这样一种活的灵魂,在博尔赫斯看来,就是一种时间的持续存在,它是一个整体,一个主体的宇宙,“宇宙,作为所有这些事实的总和,是一个集合体。”
这个集合体是我,是时间,唯心主义把它称作是灵魂,或者是上帝,它似乎在衍生和指导着物质,用贝克莱的唯心论来否定唯心主义,博尔赫斯并非是要去除灵魂的意义,而是要在这种因我而存在的时间里寻找那一个不幸却真实的我,时间流淌,时间持续,在这条河流里,似乎只有时间本身,它是灵魂,它是精神,它是上帝,“除了思维过程外没有别的现实。”就如中国的庄周梦蝶一样,庄周或者成了蝴蝶,蝴蝶或者成了庄周,他们都不是主体,只是梦把这一切变成了灵魂意义上的存在,甚至梦都只是灵魂的外射而已。所以博尔赫斯对于时间的新反驳,其实是对于缺少主体的唯心论的反驳,“唯心论判定有一次做梦、一次感知,但却没有做梦者,甚至没有一个梦。”所以这种“否定时间的持续性,否定‘我’,否定天体宇宙,都是表面的绝望和秘密的安慰”,真正回到真实的世界,就意味着要把我安放在时间的持续性之中,把我变成天体宇宙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就是时间,我就是宇宙,作为作者的我,在这样的时间意义中完成命名,于是,他就是那个不幸的“博尔赫斯”。
像上帝一样存在,在时间中成为一种永恒,这并不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解读,在博尔赫斯那里,当时间被反驳而被带入永恒状态的时候,并非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宇宙时间,而是我之为我存在的本质时间,这种本质时间在约·威·邓恩和菲·亨·高斯的两种学说中找到了模式。邓恩在《时间试验》中提出了认识主体的绵延论,一个人认识主体不仅认识了其观察的东西,而且认识一个在观察的主体,也就是客体和另一种主体都变成了认识的客体,而认识的主体又认识另一个认识的客体和下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一个链条趋向的是无限,环环相扣,组成了一种无穷的时间:“朝着预先存在的未来流淌着宇宙时间的绝对之河,或者说,我们生命的死亡之河。这种移动,这种流淌,像一切运动一样,需要有确定的时间;那我们就要有第二个时间来使第一个移动;要有第三个时间使第二个移动,就这样,直到无穷……”
邓恩的时间是向前的,而在高斯那里,时间是创造天地的一种起源,引用托马斯·布朗爵士的这句话“无脐之人仍存吾体”似乎把上帝和我结合在一起,而且是从肉身意义上而言的,肉身而创造,却是没有肚脐的夏娃,于是圣父创造亚当的年龄和圣子死时的年龄,都变成了三十三岁,于是宇宙在这个三十三岁的时间中,从死亡走向了起源——时间在过去被诱发,“时间的第一瞬间与天地创造的瞬间一致”,而这个第一瞬间不但包含了一个无限的未来,还包含了一个无限的过去。一个假定的过去。所以从这个过去的时间推论,高斯提出了原因论:“没有一个结果是没有原因的;那些原因要求另外一些原因,并不断向后递增;所有的原因都有具体的线索可寻,但只有天地创造之后的原因才是真正存在过的。”
向前的时间递增至无穷,向后的时间递减至起源,不是无中创有,而是有中创有,它是一个寓言,却也是关于时间的一部小说,而当时间从上帝到我,从原因到结果,无非是像寓言从小说一样,从属类变成了个体,从唯名变成了现实,“抽象事物拟人化了,所以在一切寓言中都有一些小说因素。小说家提出的个体因素都竭力成为普遍因素。”它是帕斯卡的圆球:“一个骇人的圆球,其圆心无处不在,而圆周则不在任何地方”。圆心是永恒,是属类和整体的永恒,是具有神性的永恒,就像宇宙起源的时间,而圆周则是个体,是不幸而真实的世界里的我,不在任何地方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意味着:无处不在;它是柯勒律治的花,“如果一个人在睡梦中穿越天堂,别人给了他一朵花作为他到过那里的证明,而他醒来时发现那花在他手中……那么,会怎么样呢?”花在过去那里,但是当梦醒来花还在,不是一种虚幻,而是一种继续,一种属的归类:“所有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诗作,都只是一首无穷无尽的长诗的片断或选段,那是全球所有的诗人建树的长诗。”所以博尔赫斯说,在柯勒律治创作的背后,其实是历代有情人共同参与的、古老的创造,“索要一枝花作为信物”,它和一个人有关,却也和所有人有关,它预见了未来的出现,却也是在过去的梦中就已盛开。
索要一枝花作为信物,完全是从那一个睡梦中来的,所以“柯勒律治的梦”里有着过去的记忆,有着未来的希望,有着现实的存在,不如说,这是未来和我有关的记忆——时间的悖论不是要取消每一种意义,而是打通过去和现在、现在和将来的阻隔,“忽必烈汗在上都之东修建一座宫殿,宫殿设计图样是其梦中所见,记在心中的。”《忽必烈汗》这首诗里的这句话就是这未来的记忆的一种写照,而忽必烈的梦到了柯勒律治那里,依然是一个梦,一个记在心中的梦,一个看向未来的梦。
无数的梦只是一个梦,无限的时间只是一个时间,无数的花也只是一枝花,“索要一枝花作为信物”,信物是小说,是寓言,是诗歌,所以博尔赫斯说:“有许多年,我一直认为在那几乎浩瀚无垠的文学中,只存在着一个人。此人就是卡莱尔,就是贝希尔,就是惠特曼,就是坎西诺斯-阿森斯,就是德·昆西。”无论哪一个作家,他们都是个体意义上的作家,都是单数的他,但是在“一枝花作为信物”的梦中,他成了他们,他们成为文学,连接过去和现在,打开现在和未来,时间是一个人的时间,时间是所有人的时间。
这便是不朽,这便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不朽是“最佳作品超越了产生作品的灵感,超越了丰富其作品的通常概念”的克维多,是“乐于混淆客观和主观,混淆读者的世界和书的天地”的塞万提斯,是
“创作意图是想定义一个可能的人”的惠特曼,是“以一种随意的成功创作了截然不同的作品”的王尔德,是“关心的不是造物主的伟大而是创造的伟大”的帕斯卡,是提出“难道这位朋友是上帝?”的卡夫卡及其先驱者,看上去,他们在时间中生,在时间中死,而其实,当一个人是所有人,时间在他们中生,时间在他们中死。,就如普鲁塔克所说:“昨天的人死在今天的人中,今天的人死在明天的人中。”
死是一种不死,不死而不朽,不朽而永恒,这就是“自己会成为文字和本质”,这就是经典,而那个我作为我们的一部分,就是一本书而书写的世界,马拉美说,世为一本书而存在,这本书在布洛瓦那里就变成了我们的书:“我们是一部神奇的书中的章节字句,那部永不结束的书就是世上唯一的东西:说得确切一些,就是世界。”世界是一本书,是一本在时间中成为经典的书,而经典的意义就是把一个人的时间变成我们的时间,把一个人的章节变成世界的章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要永远的质疑,永远的否定,“我无可奈何地怀疑伏尔泰或者莎士比亚的无限期的经久不衰,而(在一九六五年底的今天下午)认为叔本华和贝克莱的作品是不朽的。”
一九六五年底的今天下午,是具体的时间,它只是给那本书切开了一个口子,但是时间照样流过一九六五年的今天,流过伏尔泰或者莎士比亚的作品,流过叔本华和贝克莱的书籍,然后在某处合拢成为一条完整的河,像一部完整的书,在时间中以一枝花为信物,寻找自己的文字和本质:“我重说一遍,经典作品并不是一部必须具有某种优点的书籍;而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
“重说一遍”的人曾在何时说过话?他又是谁?曾经和谁,其实并不是让时间返回过去,返回个体,一本书,一个人,一枝花,一个梦,其实是集合的书,集合的人,集合的话,集合的梦,在集合的时间里,我是翻到第268页集合的读者,我是写下“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的我——于是,我把自己叫做“博尔赫斯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