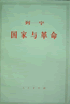|
编号:E29·2120514·0884 |
| 作者:刘瑜 | |
|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 |
| 版本:2010年1月 | |
| 定价:25.00元 当当15.10元 | |
| ISBN:9787542631664 | |
| 页数:339页 |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的刘瑜,其实审视的一切都戴上了政治的标签,将民主和市井生活、酱醋油盐联系起来也许是要把政治消解在当下生活中,“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这本2005—2009年左右生活里点点滴滴中,刘瑜感受到了“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的人生百态,而这样的人生百态或许和知识无关,但一定是和智慧有关,在《渊博的人》中,她就“邪恶”地提出了“知识智慧负相关论”:“渊博的人往往不需要很讲逻辑就可以赢得一场辩论,因为他们可以不断地通过例证来论证其观点,而大多数不那么渊博的人都因为无法举出相反的例子而哑口无言,以至于渊博的人的逻辑能力得不到磨练,但事实上,例证并不是一种严密的科学论证方法。”
《送你一颗子弹》:和现实隔着一个薄荷时刻
我认识一些渊博的人。他们是另一种生物。——《渊博的人》
第一单元第一篇的第一句,等于是刘瑜在书中的第一个宣言,《送你一颗子弹》的“你”是不是就是那些“渊博”的人?是不是就是“另一种生物”?或者是不是那些“对罗马史都很有研究,对每一种农作物的起源也如数家珍,经常探讨的问题包括‘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只到底有多大’,以及‘下一场科技革命究竟会发生在什么领域’,对‘三国’‘水浒’‘红楼梦’里面的谁跟谁通奸,那搞得简直是一清二楚”的那些人?一颗子弹的作用在刘瑜看来,足可以射杀这个群体,对“另一种生物”的不解、疑惑,似乎已经变成一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生物间的仇恨。其实,对于刘瑜来说,对“渊博”的批判一定可以走向和自己身份的相反方向,因为,“我只是人类而已”。
生物和人类,这种指称划分本身就含着对于知识的人为的类别区分,作为政治学博士和剑桥大学讲师,刘瑜的身份本身就是构筑了一种知识的高度,这种高度是把她划分在普通人或者普通女人之外,或者叫做“女知识分子”,这种对身份的划定渗透着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作为一个‘女知识分子’,我当然要经常看非常高深的书,参加高深的回忆,跷着高深的二郎腿,皱高深的眉头。(《逃避自由》)”也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身份的代表,为身份活着,也必须做和身份相符的事情:“人们指望我了解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和加拿大选举制度的不同,指望我说清中亚地区在人种进化过程中起的作用,还指望我对1492年这一年的历史意义侃侃而谈。(《渊博的人》)”也就是说,在他人的世界指称着一个自我的世界,用知识构筑起的身份帝国总是有着非人类的理性,而成为另一种“渊博”的生物。但是对于刘瑜来说,是否定的,也是在逃避中,对于刘瑜来说,自我界定反而变得宝贵,“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收银员,或者清洁工,或者餐厅服务生,或者大公司的前台接待员。”取消“女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就是取消知识的禁锢,取消理性取消应该的意义,“一个非体制内家庭里的乖乖女,一个愤青,一个为成功奋斗的留学生,一个坐冷板凳的学者”(《乱》),在这一系列身份属性的背后,却是一个“乱的角色”,也就是说,刘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七年之后》)”如果这是颠覆,那一定是刘瑜对于那种他人“指称体系”的颠覆,对于“知识体系”的否定,是自我的松绑,或者也可以理解她的八年留学生活就是一场“逃离行为”,还原自己,还原角色,还原身份,还原一个女人的喜怒哀乐。
在异国他乡,一定是文明的撞击,一定是观念的碰撞,也一定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的人生旅行,不管是哥大还是哈佛,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刘瑜的“自由之途”上也到处是“他人即地狱”的风景,在那里,有像“马克思一样的老头”,有“路灯下举着圣经高喊哈利路亚”的黑人,也有“对着我手淫的年轻男孩”。在知识渊博的生物之外,这些“他人”的到来则是完全打开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类世界,那个叫查尔斯的人,会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而他“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的境况只为自己的某种信念;或者,还有“请在你的房间里,耐心地,等死”的斯蒂夫,他们呈现着那种几乎疯狂的举动,而对于“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的人生旅行来说,一定是触及了内心那根反传统的神经。
其实,对于刘瑜来说,她的骨子里就是挣扎着那种对于规则和潜规则的轻视和蔑视,喜欢摇滚并把崔健当成一种原则,坚持“干一行,恨一行”是为了给自己更多的空间,其实,刘瑜的某种否定和轻蔑,并不是轻而易举驾驭的,或者,“获得承认和选择自由”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刘瑜用一种走出去“他们”的眼光来审视自我,审视自由,和某种现实其实隔着很长的距离。在纽约,这个世界城市里,刘瑜感受到了作为“纽约客”的世界性和公民性,“纽约就像一座跨寒温热带的森林,所有种类的昆虫、蘑菇,参天大树都可以在其中成长,只要你的生命力足够顽强。(《纽约客》)”这种共融的特性也使刘瑜提出了一个公共秩序的问题,纽约代表的城市文化是不是为一个理性、和谐、争议的公共秩序提供了可能?
在政治上六亲不认,这是纽约的最大特点,所以,纽约客的真正含义就是世界公民,刘瑜用纽约这个标本无非是要构筑一种公共化的秩序和私人化的自由,而相对而言的则是那个叫中国的地方的“江湖上的恩怨”,其实,纽约无非是一个标记而已,在刘瑜的留学生活中,一直就在进行着蜕变,关于理想,关于自由,关于政治,或者关于每个人都有的“薄荷时刻”:
忽然想起我生命之中也有很多“薄荷时刻”。开会的时候忽然想尖叫,走在街上忽然想裸奔。深夜突然想给某人打电话说不如你借我一个精子生一个孩子吧。突然想伪造自己的死亡然后跑到某个新疆小镇去隐姓埋名做个售货员,切菜的时候突然想切掉自己的一个手指头。还有此刻,突然想抢劫一个老太太的猫。
这是不是最接近自我的疯狂?“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而“忽然想起”这四个字,则把一个人拖向了严酷的现实,这是一个间歇性的情绪,里面一定隐含着现实的压抑,也一定深藏着疯狂的向往,它可以轻易抵达,也可以艰难获得,“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么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被搁置的生活》)”被推迟、被搁置,甚至被腐烂,美好的东西就只是意淫,而生活中原本很多的“薄荷时刻”,终究“屏住呼吸、向内生长”,只是一种“非正式疯狂”。
这里的无奈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一个人没有成为一支队伍,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矛盾和犹豫,每个人也都成为《麦田守望者》里的那个霍尔顿,逃跑是一个悖论,“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请别让我消失》)刘瑜也是霍尔顿,一方面想离开现实,回到疯狂、自由和个性,想成为一个“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的女人,一方面想“做个‘麦田守望者’”,用自己的行动来阻挡那些追求“薄荷时刻”的人的疯狂,“他人即地狱”,世界已经被一遍一遍的命名,哪里还有所谓的人生意义?“猪头肉的乡愁”就是一个悖论,逃避和回归,而在留学之后回到那个现实,对于刘瑜来说,则完成了“论自己作为他人”的蜕变,对她来说,一定是“既不可知又不可能”的一个社会。
抛弃成为一个贴上标签的“高深”的“女知识分子”,这是刘瑜对自我的定位,也是她走向真正自我,消除“焦虑”的努力。她说自己一般写两类文章:政论时评和生活随笔,而这本书的文章属于后者,作用当然是可以有“小小的个人历史博物馆”。其实除了“送你一颗子弹”系列的一些政论之外,整本书还是能感觉到一个女人的清新和自我,以及幽默,而在爱情世界里,虽然刘瑜阐述了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但是对于自己个人的近经历却很少提及,而在多年之后的这篇《后记》中,刘瑜托出了这生活中的变化,“在这4年里,我生活经历了很多变化,从纽约搬到波士顿又搬到了剑桥,从学生到老师,从剩女到结婚,因此有些文字现在已经过时,不能代表我现在的观点、心情和状态,只是作为‘文物’的一部分展出。”
重要的隐性话题是:她结婚啦,“从剩女到结婚”揭开了刘瑜最重要的生活,所以在网络上,读后感中对于这个话题倒是讨论热闹,谁是刘瑜的老公?从书中的点点滴滴似乎推断出了那个叫蚊米的男人,《老张、亦文和蚊米》、《饭扫光》、《我想乘一艘慢船去》等等文章都提及了这个男人,而刘瑜在其中用很可观的笔调描述着这个男人,“蚊米多好啊,在我和他之间,建立了一个进退自如的距离。 既可以去中国城扛东西,又可以从地平线上诗情画意地升起。(《老张、亦文和蚊米》)”保持距离又不做陌生人,这有点像刘瑜对待现实对待人生的态度,所以对于刘瑜的爱情和婚姻生活,除了一些八卦性质的打听之外,还可以深究如下命题,刘瑜说:“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园丁,一个是花园。(《园丁与花园》)”那么谁是虐待狂,谁是受虐狂?又或者他们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是谁先推倒的?他们如何“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他们的爱是不是“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
爱情被省略了,对于阅读来说也无非失去了一种对于内部生活的窥探而已,但是所谓的“稀薄的生活”,所谓的“形而下的乐趣”,所谓“自始至终的焦虑”,也都还存在,而且阅读完刘瑜的这本书之后,这种情绪反而越来越浓烈,所谓“他人即地狱”,也难逃阅读的禁锢,而当我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他们中的一个”的时候,正如刘瑜所说,或者我们心中的那个“薄荷时刻”真正到来了,只是,和疯狂永远只相隔喊出“薄荷”那一秒,所以在最后,一定会闭上嘴巴,拿出书签,缩回双手,书被合上,像一直没有人翻过一样平整、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