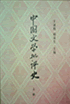 |
编号:Z32·2010325·0565 |
| 作者:王运熙 顾易生主编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1981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32.10元 | |
| 页数:718页 |
本书为高校文科教材,共三册,以时间为经,先秦两汉为始,至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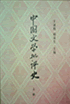 |
编号:Z32·2010325·0565 |
| 作者:王运熙 顾易生主编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1981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32.10元 | |
| 页数:718页 |
本书为高校文科教材,共三册,以时间为经,先秦两汉为始,至近代。
 |
编号:H12·1960301·0253 |
| 作者:张新颖 | |
| 出版:学林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9.80元 | |
| 页数:287页 |
本书是文学硕士张新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文集,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张新颖的文学视角较多从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吸收上进行研究的,所观照的文学作者也是以马原、残雪、余华、史铁生等人为代表,显示了新一代学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勇气与创新精神。本书还专辑论述了台湾文学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移植。本书共分四辑,为“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之一。
文学就其小而言,是我的家,是我居住的地方和逃避之所;言其大,则是空旷辽阔生机勃勃的原野,我的感受、思想、精神在这原野上自由游牧,以水草为生。
—《后记》
陈思和的《鸡鸣风雨》、蔡翔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和张新颖的《栖居与游牧之地》是我1996年3月购买的图书,这是“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三本,当时隔14年打开书页让自己进入一种阅读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怀旧:那种知识分子情怀,那种学院派风格,那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方式,的确呈现着20世纪末的人文风格,而那时的我似乎也将其作为一种理想,渴望走向知识分子的学术体系中。
是有启蒙意义的,是有自由思想的,是有个性追求的,甚至是一种如上帝式的俯瞰。据说,当时推出这套丛书的意义是试图在“滔滔商海之上”,建立起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是希望在知识贬值、人心浮动的时代中再次探寻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火凤凰”无疑是一种涅槃式的符号象征,它以一种强烈的燃烧意识革新颓败的现实,从而完成从此在到彼岸的重生。但是当14年未曾打开,现在却进入到阅读视野,除了一种自我虚构的怀旧式满足之外,是不是反倒变成了自我随波逐流的隐喻?甚至,在连续两天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和《栖居与游牧之地》的翻阅中,当看到明显的错字出现,竟然有一种失望之后对所谓知识分子情怀的嘲讽:学术批评需要的异质,需要的是独特,更需要严谨和崇敬,为什么戴着高傲面具的学院派,竟然连最基本的校对都没有达到要求?
这或者是属于编者的问题,或者可以用“不拘小节”化解之:重要的是思想,是观念。但是,当一本书作为整体出现的时候,作者无疑也是一种整体,而文章里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为作者的疏忽。站在高处的作者,低到细微处的文字,是不是仅仅是思想和知识之间的不同场域?也并非是吹毛求疵,在某种低级错误所处可见的文本里,即使观点如何带有启发意义,即使思想如何具有洞察力量,都有可能毁及一个作者甚至一套丛书的声誉。如此强调,是因为在张新颖的这本书里,看到了一种相反的见解。《现代精神的成长:从感悟到抗拒》,副标题是“对王文兴小说创作主题的一种贯通”,在这篇文章里,张新颖阐述了“现代精神”的特质,他认为,现代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是自传性的,因为它只有在“经验过程中才被经验到”,这种经验是个体的、私人的,只有顺利进入到完全私人的惊艳世界里,他者才可能经验到,才可能体会到极度内向性的现代精神。
关于现代精神,这里就设置了双重标准,一个标准是“经验的”,经验构建的是私人意义的世界,即使他者能够进入,进入其中的他者也已经不再是他者,而是经验的一个影子,这样就完成了关于现代精神的排他性,“不存在一个预设的、能够被清晰界定的现代精神,因而,没有相应经验的人就很难把握住它,至多抓住一些关于它的概念和说法。”第二个标准是:非知识对象,“一旦成为知识的对象,也就被知识规范、限制,渐趋稳固,抽空了内在的活力和生机,失去了变化与冲动的可能性,恰好沦落为现代精神的反面。”知识是一种体系,是一种规范,所以现代精神要保持其独立性和私人性,必然是对知识这个体系和规范的否定。作为经验的现代精神,作为非知识的现代精神,当张新颖如此界定了现代精神的内核,也就完成了另一种批评体系的构建:“在台湾文坛,站在乡土派立场上对现代诗和以王文兴,欧阳子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的严厉指斥,就常常表为一大堆空洞符号的无意义堆积。”
很明显,在张新颖看来,如果把王文兴、欧阳子的现代主义小说纳入到乡土派立场,就是一种知识的构建,就抽取了经验的内在意义和私人品质,在另一个意义上,当张新颖以“现代主义”来界定并寻找王文兴、欧阳子文本中的现代精神,才是一种“经验”的触摸,也只有在这种层面的批评和解读中,才能抵达他们的私人内心。没有读过王文兴、欧阳子的小说,也没有读过罗门的诗,当然更没有系统全面了解台湾乡土派的立场和观点,也从来不曾读过那些对王文兴和欧阳子现代主义小说“严厉指斥”的批评文章,所以无从判断他们是不是“一堆空洞符号的无意义堆积”,但是在看完张新颖的这篇文论,再次回过头来揣摩这句话,似乎也体会到了读到这些知识分子批评文章却看见那些未被校对出的错字的复杂心态。
张新颖一定是深入研读了王文兴、欧阳子、罗门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在他看来,王文兴的小说创作中,内在的有一条精神发展的线索,“我强烈感觉到小说中的精神世界与作者的内心路向互相投射,当然这种投射不是直接的,不是建立起一种事实相似性的纪实传记,投射对于外在事实的穿透使自传性立基于超越品格的层次,以保证书写活动是一种创造而不是复现,保证其产物是虚构的小说。”而对于欧阳子的小说,他认为对于内心探索是其关注的焦点,借用欧阳子自己的话说,“一种心理观念占据了欧阳子主观情智的中心,她把这种观念施之于作品,以此开始心理的演绎和诠释”,白先勇认为,欧阳子的小说人物不是血肉之躯,而是“几束心力的合成”;罗门的诗,在张新颖看来,则是一种“灵视”,借用罗门自己的说法,是一种宛如“多向归航台”的仪器,“从各种方向,准确地飞向机场。”诗人就是通过自己心灵的“多向归航台”,将世界从各种方向导入到存在的真位和核心,以此形成“多向性”的诗观,所以罗门诗歌里的都市、战争和死亡三个重要主题,都以“灵视”的方式显示了独立的品格,“那种内向探索的深度,那种超俗的高度,那种知性的透视、批判和令人震颤的心灵激情,这一切罗门坚持了三十余年且将继续下去的紧张的诗性精神活动,都是当代文化和文学所极端匮乏又极端需要的。”
很明显,在张新颖看来,王文兴、欧阳子、罗门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内向探索的深度,而这种内向性便是他所说的现代精神,所以当台湾文坛用乡土文学进行解读的时候,无疑是把他们的视域又抛向了外部。内心世界的外部解读,现代精神的乡土划分,这种错位在张新颖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当张新颖认为这些作品具有现代精神,是不是也是一种专断?当批评者以他者身份审视作品时,谁能从一种统一标准说谁必定经验到了内在精神,谁是在的非知识体系中触摸到了现代精神?乡土文学是另一种视角,即使完全向外,也是呈现了不同的感悟,也是提供了不同的阐释空间,何以这就是“一大堆空洞符号的无意义堆积”?
所以,这种“唯我论”是偏狭的,站在高处其实完全可以低下头来,甚至可以走下来——如果回到文本本身,当作者把文稿交给编辑,当编辑完成了校对,难道最后作者都不会再次校对自己的文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态度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仿佛能想象作者高高在上,那些低微的工作从来不通过自己的手,不通过自己的眼——毋宁说,当编辑完成校对工作,却留下那些错字,就如那些乡土派对于现代小说的解读一样,为什么反倒看不到作者站出来指责他们是误读,指责他们把内在的精神变成了知识体系?错字只是一种隐喻,对于现代精神的排他性解读或者只是一个影子,当自我识别了错字,当保持独立判断意识之后,再次回到张新颖的批评文本,其实折射的是作为作者之“我”的书写困境。
“我们可以做越来越多的事槽,我们却越来越不能表达自己。”这是张新颖提出的一个疑问:我们如何表达自己。在他看来,世纪末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标识,更是心理层面的符号,它使精神价值失去崇高性,自我失去独立性,它使知识分子面临尴尬——世界不再是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中心即边缘,在这个不断解构的世纪末,社会分裂成各自独立的单元,“各个单元都站在同样的高度,每个单元都有各自的语法,谁也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正是这种失去了中心存在的世纪末,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边缘化了,显然,在知识分子面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中,张新颖反对的是“渗透”“演化”以及“侵略”“灌输”,他似乎在如何表达自己中寻找出路:一方面找不到历史,因为历史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创造物,另一方面也找不到现实,因为现实已经被他者占有,而在历史和现实之外,未来也没有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张新颖看来,“我们”已经变成了沉默者,“为了拒绝现实、保护自己不被现实侵害,我们成了无言的话语主体。”
但是,这不是颓败,不是否定,张新颖把我变成了我们,是寻求一种集体性存在,而当我们沉默,是一种无言的状态,但不是失语,所以在世纪末尴尬的同时,张新颖其实慢慢建立起了知识分子另一个存在世界:“我们不要做现实中的话语主体。我们在沉默中孤绝。”就像指责乡土派的空洞批评,现代精神必须拒绝现实,拒绝外部,必须在共同经验中返回内心世界,在我们中沉默而孤绝。先锋文学无疑是这一“沉默中孤绝”的生动写照,它们破坏历史与现实的通行法则,就是破坏被外部引导的知识体系,它们构建其他人无法进入的独语世界,就是以彻底绝望者的姿态,拒绝向外部世界祈求——我们如何表达自己?我们在沉默中表达,在独语中言说。
在先锋之前,张新颖看到是一种叫做“反抗”的态度,这也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拒绝,是对于我们自身表达的努力,从北岛到崔健再到王朔,这是一条完整的反抗演变路线:北岛代表的朦胧诗喊出的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和人是同一的,所以作为从历史过来的见证者和受难者,朦胧诗人一直在强调“我”的出场,而我的出场是在反抗中完成的;北岛出版《北岛诗选》的1985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出了“一无所有”的呐喊,他继承了朦胧诗的精英文化心态,却又在流行意义上走向大众,但是崔健的歌声里那个我是不明确的,他只是在等待明确;而到了王朔的时代,个人主义消弭了,人文关怀被戏谑了,他甚至以逃离的方式制造了平民化粗鄙化的反抗世界,“因为他缺乏自我审视的意识,回避个体内部的分裂性,他的文化反抗的形式就是他是时代的一种病,而这种病有可能产生反社会的意义。”
从北岛“我只想做一个人”到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从朦胧诗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到痞子文学“玩的就是心跳”,文学和文化在嬗变,但是在张新颖看来,反抗却是一致的内核,“这种文化伴随新生的时代精神而生,对于先它而在的社会来说,它是陌生的、异质的,它向已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结构,意识挑战,以便争取自己的合法存在和权利。”那么到了知识分子面临世纪末的尴尬时,这种反抗是不是还具有构建意义?“文化反抗的实质存在于对立双方的紧张关系中,这决定了被反抗者对反抗者的‘牵制’,文化反抗必须在这种不自由的关系中进行。”但是很明显,当九十年代出现的先锋派在“沉默中孤绝”,它其实是取消了“牵制”力量,取消了紧张关系,所以文化反抗转变成了一种独语——一种返回自身,返回私性,返回精神之地的“巴别图书馆”——博尔赫斯对于中国先锋作家的启悟,就是构建了一个可能性的语言迷宫。
无论是马原的虚构,孙甘露的冥想,无论是余华的荒谬,还是残雪的恐惧,无论是吕新的“弥漫性文本”,还是史铁生的独舞,实际上,在中国所谓先锋文学建造的巴别塔图书馆里,每个人的独语,每个人的孤绝,都不足以提供一种“我们”式的群像标签——之所以是“我们”,只是批评者对于一种现象的阐述方便,而这种阐述方便其实也隔绝了作者经验和读者经验,其实也割裂了文本和知识,就是巴别塔本身,它只是提供了可能性,而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属于“我们”的现代精神,正如张新颖评价吕新时所说:“对于吕新,我感觉到而暂时没能说出来的和根本就属于不可说范畴的部分,也许更有意义。”
暂时没有说出来,根本不可说,是作为读者的张新颖对于作者作者的吕新的体悟,在欲说不说的呼应中,张新颖似乎找到了进入其中的“经验”,但是他又不想进入,而在退回来之后,其实可能看见更多的风景,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更多的“我”——站在近处和退回远处,也许是一个批评者必要的两种方式,而宽容和多元,也是构建一种人文视野的必要态度,正像他自己将书名取名《栖居与游牧之地》,文学是一个自我居住的家,但是绝不是排斥一切的独语,还需要寻找一个具有可能性意义的游牧之地,“我的感受、思想、精神在这原野上自由游牧,以水草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