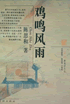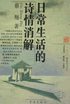|
编号:H76·1960303·0262 |
| 作者:王晓明 编 | |
|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6\1992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9.00元 | |
| 页数:518页 |
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学社团,它与创造社并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20年代的文坛,并产生了冰心、庐隐、茅盾等一大批作家,特别是它的一系列“问题小说”成为针砭当时中国社会时弊的最好武器。在其不断发展历程中,也出现了与其他文学社团和流派之间的论争。本书辑录的大量资料对研究文学研究会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
所谓时代性,我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换言之,即是怎样地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再换一句说,即是怎样地由于人们的集团的,运动、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
—茅盾《读<倪焕之>》
上下两册,是该一分为二还是该合二为一?一分为二的标记是明显的,上册是钱谷融主编,下册是王晓明选编,上册出版于1986年12月,下册出版于1992年12月–6年的时间,变化是巨大的,连统一书号都有了新旧不同的格式。当上册和下册在诸多的不同中合二为一的时候,似乎也印证了关于时代性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整体性的文本会被搁置在时间里?下册的《后记》似乎解释了这种断裂感:这是一套配合教材的评论文章选集,“本书的基本体例、选编标准以及入选文章的排列次序,都和《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上)》相同。”体例、标准和次序,和上册相同,但是在6年的时间间隔里,是不是本身的教材也处在搁置的状态中?没有看到《文学研究会作品选》的上下册,当然也无从知道在这6年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似乎只是文本编辑和出版中的一个小疑问,但是时间所造成的断裂感似乎也对应于时代性的某种错位。当茅盾在《读<倪焕之>》中谈及了文学所需要的时代感,其实距离文学研究会成立已经过去了十年–甚至距离《小说月报》停刊、文学研究会活动停顿也只有短短几年时间,这篇刊印于《文学周报》第8卷20期的文章,是茅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年之后所写,那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十年,当茅盾站在“五卅”这一时间节点上,是不是对于时代性的理解更多是一种回顾,在他看来,时代性需要表现时代的空气,需要呈现时代的影响力,需要推进时代的新方向,当文学研究会即将走向终结的时候,文学的这个时代性到底该如何成为“历史的必然”?如何在必然中又具有社会化意义?
回顾十年的历史,展望时代的方向,茅盾的这两个动作似乎是有机统一的,在不是一分为二的情况下,似乎并不会走向如选编的评论集本身那样,走向了被时间完全错开的尴尬里。在评析叶圣陶的《倪焕之》这部作品时,茅盾回顾了十年前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情况,但是他的态度依然是有些无奈的,即使是文学研究会发起成立的十二人之一,对于十年前“五四”运动中的文学现状,对于文学研究会的地位,还是偏向于悲观。他认为,“五四”和现在的“五卅”一样,对于一个时代来说,这样的事件对于中国现实来说,是一种“命定”。但是落实到新文学应该具有的文学使命上,却名不副实,“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然而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出来。”在他看来,新文学最具惊艳色彩的作品是鲁迅的小说,但是它们攻击了传统思想,表现了五四精神,但是“并没反映出’五四’当时及以后的刻刻在转变着的人心。”也就是说,在茅盾看来,鲁迅小说具有对旧时代的批判和解构意义,但是并没有对新时代形成一个必然性的方向,或者更具体来说,那时的新文学都“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人生。”
茅盾认为,在鲁迅之外,郁达夫、许钦文、王统照、周全平、张资平等人写出了一批反映现代青年生活的作品,但是作品反映的人生还是狭小的,局部的,“我们不能从这些作品里看出’五四’以后的青年心灵的震幅。”鲁迅的作品没有反映出五四基调的都市人生,其他人的作品表现了现代人的生活,但是格局又过于狭小,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茅盾认为就是当时的文坛忽视了文艺的时代性,甚至还反对文艺的社会化,正因为高唱“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正因为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即兴小说”充满了出版界,正因为时代性被“灰色的迷雾”所笼罩,所以“这样的入了歧途”–很明显,茅盾对于这一现象的批评直接指向了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几乎同一时代成立的创造社主张的是“为艺术的艺术”,甚至说过“毒草虽有毒而美,诗人只赏鉴其美,俗人才记得有毒”这样的观点,所以感情主义和个人主义充斥在作品中,所以在“为艺术的艺术”的艺术派里时代性被遮蔽了。
批评创造社,将五四新文学对于时代的弱化毛病归结于它的“艺术派”主张,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茅盾的这一观点似乎也有着太多的个人情绪。但是如果回到十年前,回到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状况,是不是它本身也忽视了时代性和社会化的努力?评论选上册里收录了两个宣言,一个是“文学研究会”在1921年1月10日发表的成立宣言,其中讲到发起这个组织的目的有三点: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这三点目的似乎都没有涉及文学需要表现时代性和社会化这一使命,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也说到,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自始即不曾提出集团的主张,后来也永远不曾有过”,它只是一个“著作同业工会”,所以在成立十年后茅盾在这篇导言里也表达了某种缺憾:“’五四’时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后应当建设怎样一种新的文化呢?这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回答。”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会也如鲁迅的小说一样,在于批判和解构旧传统和旧思想,但是并没有回答如何建设具有时代性的文化,而在《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文章里,茅盾再次说到了文学研究会当时只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发起成立的时候没有企图,没有野心,没有主张,没有宣言,“对于文艺的意见,大家也不一致–并且未尝求其一致!”
但是,在《文学研究会宣言》里,提到了另一句话:“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动一样。”这是一种怎样“切要”的工作?作者如何像劳动一样“治文学”?当然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倒是在《文学旬刊宣言》中,针对文学的意义,以及创办这一刊物的目的,说得比较明确,“我们确信文学的重要与能力。我们以为文学不仅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人的反映,并且也是超与时与地与人的;是常常立在时代的前面,为人与地改造的原动力。”在这里就提到了时代,而且要站在“时代的前面”,用一种力量引导人们改造现实,而且,把文学上升到实现最高精神的意义所在,“人们的最高精神的联锁,惟文学可以实现之。”但是,作为《文学旬刊》,它所说的文学“立在时代的前面”更多指的是译介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我们很惭愧;惟有我们说中国话的人们,与世界的文学界相隔得最为远,不惟无所与,而且也无所取。”的确,文学研究会以《文学旬刊》为阵地,不断拉近与世界文学界的距离,他们著重翻译俄国、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而文学研究会的另一本刊物《小说月报》也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译介作品,是为了拉近距离,是为了“有所取”,“在此寂寞的文学墟坟中,我们愿意加者译者之林,为中国文学的再生而奋斗,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于世界的文学界中。”而在文学创作中,这种整体性似乎并没有得到体现,但是正如把文学视作一种工作的观点一样,工作反映的是人生态度,反映的是事业追求,所以隐约地传递着作者的使命,茅盾在《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中也说到,虽然新文化运动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真正结出写实主义的实,但是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主张还是越来越清晰,“文学研究会这集团并未有过这样的主张。但文学研究会名下的许多作家–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力的作家,大都有这倾向,却也是事实。”也就是说,它表现的是一种倾向性,而今心在《两个文学团体与中国文学界》一文中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置在一起,他认为,“文学研究会,差不多可说是一个宣传自然主义的机关,而且因为他们是主张人生的艺术的原故,对于社会人生,很是注意,所以介绍文学原理的功效,远在创造社之上。”所以当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给暗无天日的中国文学界带来生气,“我们应该以十二分的诚意向他们致谢。”
这或者是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流派论”,茅盾所言及的“人生派”倾向,在他看来在许多作家中得到了体现,比如冰心的《斯人独憔悴》是一部典型的“问题小说”,比如,在庐隐《海滨故人》这样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比如在叶圣陶的作品中,反映着“小市民智识分子的灰色生活”,还有徐玉诺、潘训、彭家煌、许杰,他们在作品中描写了农村的现实生活,这些都构成了“人生派”的标记,构成了“为人生”的倾向。而和茅盾认为只是一种倾向的低调相比,郑振铎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中则认为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打着为人生的艺术旗号,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文人,甚至他们比《新青年》更进一步揭起了写实主义文学革命的旗帜,“他们不仅推翻传统的恶习,也力拯青年们于俗流的陷溺与沈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纯正的文学大道。”所以,对于文学研究会来说,他们实践的正是“文学是时代的反映”。
而当时,对于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者,对于他们创作的作品,很多人也是从中看到了中国新文化的真正希望。这其中有对于俞平伯的散文、王鲁彦的小说、丰子恺的小品文、彭家煌的小说、朱湘的诗歌的诸多评论,比如善行评论朱自清是“很清醒的刹那主义者”,“但他的刹那主义,虽不是颓废,却不免是‘欢乐苦少忧患多’……”阿英谈王统照的作品,“从他的诗歌一直到小品文,都可以充分的说明这一作家,是坚苦的人生真义的探求者,时代的歌者,而不是‘世外的游仙’。”茅盾谈庐隐:“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刘大杰谈到庐隐,也认为,庐隐是“五四”时代古典主义崩溃、浪漫精神和人权运动新生的“典型人物”……朱自清文章里“欢乐苦少忧患多”,王统照是“时代的歌者”,庐隐是时代的典型人物,是不是就如茅盾所说,他们表现了为人生的倾向?
在诸多的评论中,比较集中的是对于冰心和叶圣陶的创作评价,而这两个人的创作态度似乎也可以管窥文学研究会是否具有“为人生”的倾向性?对于冰心的文学创作,上下两册选编了14篇相关文章,为单个作家最多。直民在《读冰心底作品志感》中认为,冰心“像一朵荷花一样,洁白”,是一尘不染地直伸起来的诗人,所以在她的作品中能感受到到与神灵同化的意境,在他看来,这就是健康的文学,而文学也不管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就需要这种健康,“我们为艺术底真价值上,为人类底前途上,都该要求健康的文学。”而式岑认为冰心的文学创作中透出的一个字是“爱”,“宇宙的神秘,和人类的深思,本来不能遮蔽人类的烦闷。唯有人间的爱,才能使人沉醉,使人忘其分内的悲伤。”阿英认为冰心是“新文艺运动中的一位最初的,最有力的,最典型的女性的诗人”。
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作为创造社的成仿吾就指出,《超人》不是一篇成功的作品,“所以象《超人》那样把主人公写到极端否定,不仅理论上说不过来,还使结构上生了一层缺陷。”在他看来,冰心的小说和诗歌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她的作品都有几分被抽象的记述胀坏了的模样。”对现实的观察不够深入,反而被客观想象蒙蔽了;而梁实秋认为,冰心的诗集《春水》和《繁星》都不是成功的作品,比起小说来逊色不少:“她的短处是在她的气力缺乏或由轻灵而流于纤巧,则由浓厚而流于萎靡,不能大气流行,卓然独立。”草野在《始终没有走出象牙塔来的谢冰心》也认为,冰心的生活似乎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那也只是“从象牙塔移到象牙床上罢了”,“她对于社会一切都不能有澈底的见解与进步,结果只站在社会的外面说空话,另一方面渴望着无中有,这样的经过,使作者抱了犹疑恍惚玄想的态度,离开现实世界,走上不可推测的迷离歧途。”
无论是赞誉者所说的神灵同化的意境,爱的主题,荷花一样的文风,批评者所说抽象的迷茫,没有大气的品格,躲避现实的虚无,似乎都可归结为茅盾所说的没有真正的时代性,没有站在时代的前面,当然也就缺乏社会化,但是对于叶圣陶的作品,似乎评论的观点都指向了它具有的时代性和社会性,顾颉刚认为叶圣陶的小说《隔膜》表达了真实的情感,“他的小说完全出于情之所不容已,丝毫假借不得的。”化鲁也认为《隔膜》“是一页一页的现实生活的影片”;而赵景深读了叶圣陶的《火灾》后感受到了内心的澎湃,“他将温柔敦厚的人格感化了我这徬徨歧路的迷羊,使我很愉悦的饮幸福之泉!”朱自清说到了叶圣陶的《倪焕之》,他认为,倪焕之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时代史,“这二十年来时代的大变动,自然也给他不少的影响:辛亥革命,他在苏州;五四运动,他在甪直;五卅运动与国民革命,却是他在上海亲见亲闻的。这几行简短的历史,暗示着他思想变迁的轨迹,他小说里所表现的思想变迁的轨迹。”夏丏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倪焕之》中所描写的,是五四前后到最近革命十余年间中流,社会知识阶级思想行动变迁的迳路–作者叫这许多人来在舞台上扮演十余年来的世态人情,复于其旁放射各时期特有的彩光,于其背后县上各时期特有的背景,于是十余年来中国的教育界的状况,乡村都会的情形,家庭匡的风波,革命前后的动摇,遂如实在纸上现出,一切都逼真,一切都活跃有生气。”
而正是这部小说,成为茅盾所说是表现时代性的一个样本:描写了旧制度崩溃,也描写了新时代的开启,再现了农村生活,也展现了城市现实,表现了时代空气,也“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五四’来了,乡村中的倪焕之也被这怒潮冲动,思想上渐渐起了变化;同时他又感到了几重幻灭,在他所从事的教育方面,在新家庭的憧憬方,在结婚的理想方面。他感到了寂寞了。他要找求新的生活意义,新的奋斗方式,从乡村到了都市的上海。”而这样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具有典型性意义,“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
时代性和社会化是一种历史必然,它既是文学上的必然,也是现实中的必然,“这样有目的,有计划的小说在现今这混沌的文坛上出现,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有意义的事。”而茅盾在那个时代创作的《幻灭》《动摇》和《追求》似乎也在实践着这样一条创作之路,回顾而展望,历史而未来,当文学被赋予必然的时代性,这或者也成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意识形态”,成为作家必须具有的标签–文学在贴上诸如此类的标签之后,是不是也意味着走向了一种功利主义的目的论道路?无论是为艺术还是为人生,也许文学真正应该还原其本质,如潘垂统所说,“我以为什么写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最好不提起这些名词。-方面说是要表现个性,是要创作;一方面又说这是写实主义,这是浪漫主义。我不明白写实主义是谁的创作?浪漫主义是谁的创作?文学而有主义,还说什么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