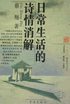 |
编号:H12·1960303·0260 |
| 作者:蔡翔 | |
| 出版:学林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7.50元 | |
| 页数:219页 |
“消解”一词是蔡翔以中国社会商业特色为背景,对精英文化产生的历史作用进行的批评,这种失落是文学的个体特征的现实命运。蔡翔的文化批评明显受到西方以机器文明为特色的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精英意识与文人传统复活的强烈欲望,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如何消解文学等方面缺少积极性。本书共11章,为“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之一。”
“寻找”开始从精神的范畴中悄悄撤离,而转向一种个人此在的世俗性幸福。
—《写在前面》
“寻找”其实是一种陈列:一本1994年12月出版的书,一本1996年购置的书,始终以合拢的方式静置于书橱的某一个位置,从学校宿舍到出租房,从老房子到新房子,在不同的空间变迁里,它始终是一本书,一本合拢的书,意味着它只是在物的层面上进入到流转的时间里,尽管里面已经敲下了象征被阅读的书章,尽管在无数次的机会中它被看见,但是在没有打开而阅读的世界里,它以泛黄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仅此而已。
而现在,当进入到2020年的阅读计划,当从书橱的位置抽出来,当打开第一页进入到蔡翔的叙述空间,是不是在一种历史层面证明了它一直在场?从1996年到2020年,时间跨度是14年,当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一本书甚至变成了历史的见证:《写在前面》中,蔡翔说:“我们在此将要讨论的,乃是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或者说,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当代文学中,究竟呈现出知识分子什么样的精神风貌乃至基本的思想走向。”蔡翔关注的是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当代文学”,关注的是在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八十年代,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当1994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蔡翔是以回首的方式看见八十年代的文学风景,而现在,当在二十一世纪二〇年代,以一个读者的视角再次回望的时候,八十年代是不是还是那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是不是还是那批知识分子?
显然,这是一个伪命题,时间总是向前,人物总是更替,环境总是变化,在这种历时性的语境下,在场几乎就是一个神话,蔡翔在上世纪末期言及了一种存在,那就是历史和当下的双重“不在”:既如先锋小说一样,在焦虑、迷惘、绝望、荒诞、黑色幽默、荒原感、等待戈多等内心的革命风暴平息之后,在“日渐从众日渐优雅日渐什么都无所谓的社会”里,先锋先说无非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那样,在陆高和姚亮终未抵达天葬场、没有见到野人,以及“姚亮不一定确有其人”的故事里,诱惑反而变成了在场的不在场;也像新写实主义文学、新历史小说一样,在历史的空间化处理中,感受到人的日常性存在的无可改变,它们制造的“意义的缺席”,是用一种将人替换成物的方式表达了“不在场”–无论是诘问和怀疑,还是妥协和消解,不在的存在如何构建立体的时间,如何凸显寻找的母题。
不在之在,像极了这一本14年都未曾打开的书,但是,当在14年后进入到时间的内部并且以回望的方式阅读,寻找似乎也只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了解和认知。当任何一个故事都“以没有结果而告结束”,当处处充满“冈底斯的诱惑”却又一无所有的时候,寻找是不是只是一个行为艺术?其实,蔡翔在《写在前面》的话里,很明确了自己站立的当代立场,也很无奈地启示了日常生活咄咄逼人的解构力量,当“当代”被无情地解构,寻找只是为了拾掇一些逝去的碎片而已,而从“当代”望过去,不论是1994年的现在,还是2020年的未来,蔡翔都无力在某种知识分子的情怀中找到真正的神圣使命。
“文化失望”是蔡翔统摄全书写作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当代”呈现的语境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开始悄悄引发。由此导致了某种失望,并通过文学的形式程度不等地流露出来,从而构成种种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进入1978年之后的“新时期文学”,所出现的是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社会良知的角色,伤痕也好,寻根也罢,包括朦胧诗,知识分子在告别了一个时代之后开始了寻找,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坚守一种启蒙主义的精神立场,是为了让文学重新关怀社会和人类的终极意义,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得以重新强调,社会良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自由思想、终极意义、个性解放,凡此种种,知识分子他让自己成为神圣的代言人,从而在俯视的目光中寻找一种意义。
这种寻找的意义,就是蔡翔所说的“潜在地存在一个‘失乐园’的文化主题”,他们努力的一切,都是为了摆脱俗性时间的缠绕,“而普遍充溢着对神圣的追求”。毋宁说是寻找,不如说是重新发现,在蔡翔看来,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有一种明确的人文目的,那便是要求在现实中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这便是“道”,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老庄哲学,启示真理和改造社会的两大主题,都成为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源头,即使当人的理想遭到社会压迫时,也用一种“隐”的思想,在从“解放人类”到“解放自己”退而求其次中保留着知识分子身上的人文色彩。
但是,当时间进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新时期的启蒙渴望慢慢退化,当“寻找”成为一种行为艺术,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不是必然是对日常生活的事情消解?“失乐园”之后的“复乐园”是寻找的暂时结果,还是不必寻找的必然状态?在场与不在场,失去和寻找,似乎构筑了一种虚构和摹拟的紧张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小说和日常生活”之间演变成了词与物的悖论。蔡翔认为,小说作为一种虚构,作为一种叙事,是鼓励小说话语行为的主体权力,这个主体便是小说家,而且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小说家,在这个具有主体权力的小说世界里,小说是一种个人化的存在,要求的是叙事行为的抒情化,而这便是“诗情”。但是当小说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小说,它又必须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性”行为的存在,也就是说,它必须引入读者,引入听众,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只是一个“转述人”,而小说所营造的世界,便是一个公众世界,“从而具有着明显的类的痕迹。”
所以悖论就必然产生了,主体和客体,虚构和摹拟,表现和再现,个人性和公共性,构筑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语境,在这个悖论中,如何突围便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选择,甚至如何突围,有时候却只是如何叙述–当小说的叙事变成了叙述,“证实权威”的意义何在?主体权利何以体现?寻找的母题如何凸显?而这些问题在蔡翔看来,无非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终结命题:“小说究竟是对存在之物的言及,还是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而在八十年代的“当代文学”中,小说作者的遭遇,一种是“退出”,主动退出主体权力世界,在“缺席”状态下,用流水账式的叙事方法形成“新写实”的风格,而另一种则是“受阻”,当个人性的文化态度进入到复杂琐碎的日常生活时,因为遭遇一系列的阻滞,于是产生了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态度。主动退出和被动阻滞,都不可避免地在“复乐园”的所谓寻找中,让小说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变成了在公共性叙述中的“不在”,甚至变成了对于“生活就是生活”的世俗性幸福的摹写。
蔡翔对这一议题的分析着重于对现象的解读,在他看来,八十年代的“当代文学”呈现出了不同的文本风格。一种是以先锋派作家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他们带着诘问的语气,带着怀疑的目光,对时代进行叙事,洪峰、格非,余华和马原,这一群体作家从二元对立中撤离,他们对真实性世界采取了彻底的拆解态度,就像冈底斯的诱惑一样,从来不是确定的,不是必然的,而是用不在来代替在,而这种存在的消解意义使得“逻各斯中心”和“元语言性”都被戏谑,“好吧,我认识你,我说(实际上我想说;我认识你算了)。”格非的《褐色鸟群》中这样说;父亲之死之后的“奔丧”,只是一种沉湎自我的行为,洪峰的《奔丧》构成了对神圣亲情的亵渎和调侃–;在戏谑中,在亵渎中,在调侃中,作者自己命名了存在,命名了故事,在充满诘问和怀疑的虚构中,“以没有结果而告结束”。
但是,这种戏谑和调侃,这种亵渎和解构,是在诘问和怀疑中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是消解“逻各斯中心”,不是颠覆“元语言性”,而是用自我命名的方式重新构建了逻各斯中心,重新发现元语言性,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神圣性使命赋予自身,冈底斯的诱惑,毕竟还有那一种悬而未决的诱惑在,所以这不是真正的主体权利的丧失,不是主体性的衰落。和先锋小说有着同样使命意义的还有那些制造了新的英雄神话的作家,“在这普遍平庸的时代,他孤独地坚守着自己的立场。”蔡翔指的是张承志,他在《北方的河》里,唤起了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诗意向往,但是这孤独的英雄只不过是一次尴尬地再生,像叶兆言的《挽歌》一样,当他们拒绝谋求和日常生活的妥协可能,他们迷恋的是精神崇高的一曲挽歌,苏童的《十九间房》里,土匪,女人,性,暴力,满足了读者的某种阅读嗜好,这种再生的叙事中,其实没有英雄,它只不过是被包裹了一个“凄楚的灵魂”,只不过制造了悲怆的“热泪盈眶”的表象感受。
但无论如何,先锋小说还是英雄神话,都有着作者再造的中心,都有着自设的元语言性,或者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走向主体性衰落的困境,他们还在用另一种力量支配语言、支配作者,从而支配读者–一曲挽歌唱起,不是感慨于挽歌带来的孤绝的凄楚,而是应该赞赏于还有人勇敢地唱出挽歌,这是可贵的。而在这种可贵的对立面,真正主体性衰落而带来的对于日常生活的摹写,则真正走向了所谓的“个人此在的世俗性幸福”:人不再是自我选择,而是被选择,不再是必然性现实,而是偶然性生活,不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特殊具体性的个体,不再是虚构,而是写实。“这些小说相当强调’叙述’,以一种貌似客观的口气中性地叙述’生活’,并且以流水帐式的结构方式替代了情节性的故事编排,也许,这就是其中一些作品被称之为’新写实’的原因之一。”当知识分子像大众靠拢,甚至妥协,他必然是从众的,必然只是在一种类存在中成为此在。
蔡翔认为,这是“示者”与“看者”的根本性颠倒,小说作者本来是看者,是在看的过程中成为一种主体,但是当从众发生,当人物变成类,看者反而在读者世界里变成了示者–;示众,成为文本和作者乃以摆脱的宿命。示众,被说成是回归大众,被看成是融入了“人民神话”中,但其实,“由于知识分子的日益贫困化,在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已经和大众溶为一体,遭遇到共同的生存困境。”王朔的小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似乎正说明了与大众文化潮流的合拍就是一种主动的示众,就是一种妥协式的从众。知识分子的主体只是那些“贵族痞子”,只是活在“小时候”,而当这一切都走向了没落,当等级社会完全解体,世界也许真的只剩下“我是你爸爸”式的伦理抚慰,所以王朔说:“我的作品的主题用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就是‘卑贱者最高明,高贵者最愚蠢’……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念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
当蔡翔在“生活就是生活”的消解中阐述主体的衰落时,他是悲观的,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学者的他,正是在不停地寻找“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意义,那应该是一种人文情怀,应该是一种启蒙思想,应该是一种人道主义,应该是一种终极意义,“精英文化在中国,并不单纯指称所谓的上流知识分子文化,更多的是指在新时期文学中,严肃的知识分子所逐渐构建的某种文化系统。”但是在“当代文学”的两种走向中,当新写实抹去了先锋派最后一抹知识分子化的诠释痕迹,他说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商业大潮冲击下的时代,这是一个被市场经济逐渐控制的社会,这是一个不再有英雄的世界,“终极性真理的迷失,使得知识分子不仅对世界,同时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主体性逐渐走向黄昏的没落,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战斗精神已经悄然远逝。”当蔡翔发出“我们走向哪里”的疑问时,他的言外之意其实是我们应该寻找,寻找主体性,寻找战斗精神,寻找终极性真理。
挽歌式的感慨,需要的是文人传统的复活,但是在逐渐失语的时代,在诗情消解的社会,在“工具理性”弥漫的空间,知识分子再无法指点江山。蔡翔注目的是八十年代的“当代文学”,当时间流转,14年后再次回望那被“生活就是生活”的历史,或许那时的当下呈现的也是一种迷局,无论先锋还是新写实,无论马原还是王朔,都制造了一种在场,而当14年后进入阅读的当下,另一种迷宫其实早就铺陈开了:没有了寻找,没有了启蒙,没有了主体,没有了先锋,甚至文本本身也早已经湮没在公文、档案和日常对话中,于是,一本1994年出版的书,成为阅读世界里最后一声叹息,在二〇年代的开场中,成为微弱而可怜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