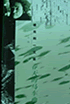|
编号:C41·2040130·0694 |
| 作者:(日)横光利一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275页 |
《家徽》是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文集中的一册,收入了其长篇小说《家徽》。孤独的发明家雁金八郎研制一种新酱油的过程中,山下的儿子久内娶了与雁金已私定终身的敦子为妻……这部作品与《寝园》都是以“第四人称”讲述的。作者认为,要更深入地描写或挖掘人物的行动、心理和自我意识,三个人称已经不够,于是设定了第四人称的模式,试图探索自我意识深处的心理的现实性。
他穿过这片豪宅时心中暗想,这些人都不过是依靠生产或贩卖他人的发明品而暴富的。世上万物,除了自然存在的以外,都是由某人发明而产生的。
——《家徽续篇》
年近四十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感情归宿,自己苦心付出的酱油发明专利又一次次胎死腹中,对于雁金八郎来说,人生或者就是寂寞潦倒,只是当他再次走上大街的时候,西装口袋里依然装着两个小坛子,“衣袋里的东西很轻,只要沿着海边大道前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自己长年从事研究的沙丁鱼群。”这是被人忽视的发明,却也是自己毕生的心血,只有带在身上,只有陪伴左右,才能让自己有某种存在感,甚至有成就感,像沙丁鱼群,总是成为自我生命的一种写照。
像是逃离,但是是带着一生最爱的东西逃离——雁金离开的是“社会上最成功的事业家门的聚居地”,离开的是鳞次栉比的豪华别墅区,其实也是离开某种家徽荣誉的象征,一种割裂其实就活生生展现在他面前:他是一个发明者,但是却处在极度贫困之中,而那些生产或贩卖发明的人却成为暴富的人,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不再是个体间物品的转移,而是从脑力劳动转移到资本市场,那暴富的手背后是操控市场的人,这便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这样的差距面前,“他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许违反了神的旨意,因而愈发感到自己窝囊无能。”
而雁金的逃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避开感情的那个漩涡,夜宿在久内家里,对于雁金来说,一定会涌现出复杂的感情:因为久内的妻子敦子曾经是自己的未婚妻,甚至在离开之后两个人还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但是即使敦子之后嫁给了久内,他们的婚姻也并没有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久内和初子保持的情人关系,初子和雁金曾经的恋人关系,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复杂的纠葛之中,即使久内和敦子经历了冷战和争吵,也重新开始相互体谅,但是当雁金夜宿家里,那种涟漪似乎又被荡漾开了,和久内夫妻同住一个屋檐下,对于雁金来说,是种奇怪的感觉,一个是曾经的未婚妻,一个是旧情人却也是最被信赖的人,他所面对的不是现实的尴尬,而是对可能结局的悲观:“他想,倘若自己与敦子的婚约真的付诸实行的话,那么现在每天一定会是这个样子。但是,自己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两个人无疑会成为一对最为悲惨的夫妻。”
而对于久内和敦子呢?似乎也一样不是在感情上的所谓的嫉妒和无奈,久内处在一种自责当中,不仅是自己作为博士的父亲和研究所所长多多罗的设计陷害使得雁金的发明遭遇重大挫折,另一方面,是自己要和雁金一比高下的好胜心才使得两个人陷入某种僵局,甚至在感情上,和敦子、和初子之间总是有某种角力的成分,而当看到雁金潦倒的时候,久内的一个奇怪想法是:“这两个人真的有过婚约吗?”一个是穿着又脏又皱的外套,一个是亭亭玉立的妻子,他们怎么可能会有相配的婚约,而初子,当初和敦子一样,是家产超过二百万圆的富家小姐,她们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空有名门、小雪都没毕业的雁金而发生争夺战?所谓天壤之别,也是一种割裂,而对于久内来说,内心的浮想还在于自己也曾与这两个女子有过不解之缘。
而在这个屋檐下的敦子呢?当初是自己离开了雁金,取消了婚约,之后又与久内结婚却走向了分居,最后能够相互体谅走到了一起,但是面对雁金,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嫉妒、怨恨、焦急等这些伴随着爱情的复杂心情早已远离敦子,她之所以能接受这些,恐怕是为了填补空虚的内心吧。”空虚的内心所填充的早就没有了爱情。如此,不管是雁金,还是久内、敦子,所谓的爱情都已消弭,他们在一起,除了遗憾、无奈、嘲笑、空虚,还剩下什么?甚至在没有了爱的世界里,他们的关系早就退化成简单的合作,他们眼中所见到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人在社会上存在最表象的一部分。
仿佛就是那一群沙丁鱼,被捕捞,被加工,在牺牲了自己的同时,却也让别人成为了富翁,让别人住在了豪宅区,让别人享受幸福,而所有这一切的结局是不是在他们的身份转变中就已经注定?敦子和初子曾经是富家小姐,久内是名噪一时的博士之子,他们本来就是富人,本来就应追逐享乐生活,但是当家族遭遇破产,当父辈遭受争议,他们自己反而陷入在泥潭中,甚至难以自拔。而雁金更是一种典型,“家族代代勤王为荣”,这便是所谓的“家徽”的荣誉,但是这个家徽一样是表象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祖先传下来的家徽荣誉变成了现实的讽刺,小学没毕业成为雁金最现实的处境,所以在家道中落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走上发明创造的的道路,研发新的酱油成为他一生的付出,的确,他以自己的天才完成了发明,并引起了业内的反响,但是在阴谋论中,无论是研究所工作还是自己搞研发,最后终是无法逃离那一套规则,终是成为他们暴富的牺牲品,造成这一切的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可以说雁金其后的恶战苦斗皆源于世人的蔑视。”这句话似乎点出了雁金陷于困境的原因,不仅仅是个体的争强好胜,不仅仅是内心燃起强烈的希望,而是整整一代人的疯狂和无奈,“世人的蔑视”是什么?为什么会在蔑视中迷失自我?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又意味着什么?家徽的荣誉属于过去,而这个过去无疑也成为一种包袱,当人被丢掉了一切而走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时候,荣誉甚至变成了阴影,正是在这个阴影里,蔑视出现了,那种无法看见你成功的人一定会以蔑视的目光审视你,嘲讽你,所以愈发要激起斗志,也愈发陷入到割裂现实的困境中,长久以往,便像是一种牺牲品,找不到自我的定位。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在“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中,雁金、久内,甚至敦子、初子,在被摘掉了头顶那桂冠的同时,已经看不清自己应该的定位,从而也失去了一个时代最积极的相应。
发明创造是向着那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前行,薯类生产酱油,鱼干生产酱油,这是创新,这是革命,从资金,从材料,从智力,雁金都投入其中,“雄心勃勃的雁金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次机会,同时也开始了他冒险的旅程。”所谓苦心旨意便是要告别这个被蔑视的时代,但是在努力告别蔑视的过程中,新的蔑视产生了,当发明成功,当报纸把他捧上天,他也依然无法逃离计谋,逃离资本的控制,“雁金只是一个纯粹的发明家,对于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一窍不通。”最后终于在研究所多多罗的计策中身无分文,还陷入了长久的专利战争。与发明一样,对于感情,雁金也在不被蔑视的争强好胜中,“是的,我奶奶去年去世了。要不是为了怕我奶奶操心,当初我就跟初子结婚了。与敦子相比,我更喜欢初子,如今,我愈发对她放心不下了。”是因为奶奶,才在感情中陷入两难,而“奶奶”无非代表着一种“家徽”,它是压在雁金身上的另一个负担,所以最后既无法和敦子结婚,也无法和初子走在一起——因为自己专利的事,雁金错过了和初子和好谈论结婚的事,这仿佛也是一种暗示:为了旧有的家徽而错失,为了新的荣誉而迷失。
而久内也难以逃脱这一种束缚,和敦子结婚又和初子来往,同样是名门之后,久内仿佛是游手好闲的一代,而初子则是家族破产的第二代,所以他们的交往也是在去除“蔑视”:“看样子久内仿佛是在下意识地与初子赛跑,看谁往下滑得快,他无由地疯狂欢呼,那欢天喜地的样子十分怪异。”那一句“没等初子家破产,我这儿倒要先走一步了”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而久内对于雁金的关注,表面上看是对于他不断努力超越自我的敬仰,当他终于自谋出路时,满溢着对雁金的感谢:“我是个不肖的儿子,至今一事无无成,现在能够使父亲不再为我操心,也皆得益于雁金先生美德的感化,我对他怀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感激之情。我也讲不好,就是代父亲说几句话。”甚至在交往过程中,雁金成为他唯一信赖的人,两个人仿佛都在理想的路上奔跑,“啊,雁金这个人是堂吉诃德,而我就是桑丘·潘沙。”
但是,这无非是另一种虚妄,久内对善作说:“我从他的身上受益匪浅。我从现在开始拥有爱情和正义这类高尚的东西。我将渐渐地恢复自我,你现在还远不是你自己。”是雁金唤醒了他内心高尚的东西,而这些高尚的东西成为回复自我的象征,便是告别蔑视重新回到“家徽”荣誉的轨道上。所以久内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被人蔑视,所以即使雁金是自己的敌人,他也能从敌人的世界里发现自己的意义,这便是他所命名的自由:“正因为是敌人,他的行为才清楚地告诉了我什么是自由。表面上,我一直是输给雁金的,其实最终我还是赢了。”而最终他想让自己得到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控制,就像他看的那本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书:“人类的幸福逐渐变小了,但是这种事于我无关紧要,因为鹫诞生了。我已不爱人类了,我开始爱的是以人类为食维持生存的鹫。由此,我宣布无历史的人类已经寿终正寝,人类的历史毫无疑问就是鹫的历史。”
对人类历史的重新命名,就是用鹫取代人,就是用争夺取代自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多多罗和父亲设计陷害雁金,何尝不是普罗米修斯的那只食人的鹫?和敦子分居是为了寻求自由,见到多多罗的女儿又想起了初子,是不是又是那只渴望控制人的鹫又复活了?以及做了保险销售员拉善作进来使他成为牺牲品,“为达到目的,久内狠下心肠,决心先拿善作开刀,他选中善作的另一个理由是,怨恨善作不久就要夺走初子。久内突然变得如此冷酷无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惊喜地发现了一个自己能够发挥全部力量的场所,而且与金钱毫无关系。”如此,“家徽”不仅没能从他的骨子里被去除,而且一直处在这样一种阴影下,当用不同的计谋试图消除那种被蔑视的感觉,其实反而加重了被蔑视的体验感,“随着煎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久内迎来了春天。他想,这一切都是自己自作自受,所谓心灵上的痛苦超过赚钱的辛苦指的就是这种工作吧。”
雁金活在自作自受的世界里,只不过他将其转化为对于发明的自觉行为,久内也处在自作自受的世界里,他则是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里成为困境的制造者,而当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审视三个人以及更多人之间的关系之后,“愈发感到自己窝囊无能”的感觉根本没有改变,甚至变成了新的轮回,只是,在《家徽》之后,在《家徽续篇》之后,这个循环并没有走上终结,当雁金离开久内的家,离开那个富人居住区,小坛子成为他唯一信赖的东西,而沙丁鱼的自喻将他又推向了蔑视而努力,努力却再被蔑视的未来中。作者最后的附言是:“我计划将这部作品继续写下去,最后归纳成一部单行本。此次只作为第一部告一个段落。”
第一部告一段落,这是未完的结局,雁金会走向何方,久内会如何生活,都是未解的迷,而其实这个未知的世界没有多少悬念,因为所有的路都已被预设,甚至一直在发生着,就像家徽,“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只是一种轮流,而对于这一现实,有一个人却在俯视着,那就是横光利一笔下那个特殊的“我”。从一开始,我是和雁金在一起的故事人物,甚至雁金追逐着敦子的车辆,我就是目击者;之后,我去找善作,知道了敦子和雁金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故事的参与者;之后,我在银座看到了久内和初子在一起,于是我又变成了旁观者;后来我又读到了久内给我他写的稿子,在文章中他描写了自己的内心生活,一种私生活小说展现在我面前,我则成了阅读者,“在这篇小说里,若从雁金与久内聚餐那晚回去的描写中抽出一小部分就更精彩了,我决定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动,当然,文中雁金、敦子、久内及初子用的都是化名,为防止产生混乱,我自做主张打算把这些名字都换成真名。”之后,我又听说了雁金和研究所多多罗之间的关系,听说了雁金成功发明了新的酱油,还读到雁金那天晚上写的公开信的草稿,这一切也将我变成了听说者;只有也遇见了久内,也收到了雁金的论文……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称,既出现在小说中成为其中的人物,也通过不同的线索讲述着故事推动故事的发展,而在整个故事里,我其实也可以被抽去,而成为全知全能的人,但是在个人展示内心世界的时候,我又退了出去,成为无主观的存在,失去自己的判断——如此,“我”便是所谓的“第四人称”——在你我他组成的传统人称之外,第四人称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使得小说也脱离了传统,而这个复杂、多元的“我”是不是也在用另一种方式离开单一的现实,离开既定的命运,离开家徽的循环,而进入到一种未明的时代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