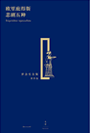 |
编号:X32·2191214·1611 |
| 作者:欧里庇得斯 著 罗念生 译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69.00元当当32.90元 | |
| ISBN:9787208134645 | |
| 页数:436页 |
欧里庇得斯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十八部。对于欧里庇得斯的评价,古往今来一向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也有人说悲剧在他的手中衰亡,无论这些评价如何反复,无庸置疑的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与前辈们不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不再围绕着旧式的英雄主题,而是取材自日常生活,剧中出现了平民、奴隶、农民等人物形象,而剧中所采用的语言也平民化了,很通俗易懂。排除所谓的“苏格拉底式的乐观”,欧里庇得斯的写作风格可谓是对传统悲剧内容的颠覆。他被认为是“蔑视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政策,对人人赞美的荷马史诗中半人半神抱着极端叛逆精神,而对沉默寡言,不求闻达的普通人,则寄予莫大的同情,在这些超尘脱俗的老实人身上,他找到了他的英雄主义理想”。《欧里庇德斯悲剧五种》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欧里庇德斯悲剧五种,包括:《阿尔刻提斯》《美狄亚》《特洛亚妇女》《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酒神的伴侣》。
《欧里庇得斯悲剧五种》:可是神不应该像人
赫卡柏 特洛亚,你先前在东方的城邦里气焰真高,你的好名声立刻就要消失了!他们竟把你烧毁了,还要把我们从这地方带出去作奴隶。神们呀!——我为什么要呼唤神们?我早就向他们祈祷,可是他们哪里肯听?
——《特洛亚妇女》
老普里阿摩斯死了,儿子赫克托耳死了,佛律癸亚的英雄死了,特洛亚的将士也死了,而当经历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随着特洛伊城在火海中坍塌,只剩下可怜的女人们,而这绝不是女人命运的最后终点,“这震动,这震动会倾陷全城!哎呀,这战栗的,战栗的腿啊,快支持我步行,引导我去过奴隶生活。”她们成为了不再受保护的女人,他们不再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她们走向未知之路就是走向非人的奴隶生活。
这是“她们”的宿命?“呀,舞弄铜矛的特洛亚将士的可怜的妻子们啊,可怜的女儿们啊,苦命的新娘们啊,伊利翁正冒着浓烟,让我们齐声痛哭吧!”的确,特洛伊的妇女被战争带向了奴隶的深渊,而其实,造成这一场战争爆发的正是因为女人的嫉妒,甚至和神明有关,那个金苹果不是为了判定谁最美,而是在美的诱惑下决定了“女人为难女人”的悲命循环中,当斯巴达王妃海伦被劫走,希腊各城邦的王者和将领在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带领下进兵特洛伊,由此导致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所以斯巴达国王、阿伽门农的弟弟、海伦的原夫骂她:“全军的将士把你交给我这受过你的害的人来杀掉。”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妻子、赫克托耳与帕里斯的母亲赫卡柏也对墨涅拉俄斯说:“快把这女人杀了,杀得好,这样你就给希腊戴上了一顶荣冠;你还得为其余的女人制定这一条法令:‘凡背弃丈夫者概处死刑’。
杀了海伦,制定法令,赫卡柏就是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一个女人的不忠,但是海伦或许只是一个导火索,“我果真就这样死了,未免不公平。”当海伦被置于仇恨中心,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幸,但是海伦的身后站着谁?那就是阿佛洛狄忒,当阿佛洛狄忒带来了金苹果,当金苹果成为了灾祸的起因,这场灾难的源头似乎就是一个神。当女神为了海伦而发生争吵,当这种争吵变成了特洛伊战争,当特洛伊在木马攻城中陷落,当城市陷落而将士们战士,是不是这一种罪过都指向了神?而起源于女神的嫉妒而造成的人间悲剧,最后却又给女人们带来了灾祸。被分配给阿伽门农的卡珊德拉在特洛亚妇女面前把灾祸指向了希腊联军,指向了男人:“他们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点爱情,为了追回海伦那女人,牺牲了多少性命!至于那聪明的元帅,也为了那最可恨的事情,失去了那最可爱的东西,他为了那女人的缘故,把家庭间父女的快乐为他的弟弟牺牲了,那女人原是她自己愿意,不是硬被拐走的。”
海伦或者是牺牲品,但是当特洛亚的妇女也都成了被分配的奴隶,他们更是这个神制造的悲剧里的牺牲品,甚至如歌队所唱:“黑暗的死罩上了他的眼睛,那敬神的人竟叫那不敬神的人杀死了!”因为最后时刻,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刻的儿子、无辜的阿斯堤阿那克斯被他们从城墙上摔下来死了,赫卡柏这时才将这一悲剧怪罪于神,“你们曾发现残忍的行为不合希腊精神,为什么又要杀死我这无辜的孩儿呢?”神的冤仇,神的嫉妒,让人世间变成了末日,“我敢说,你决不会是宙斯所生,你原是这许多希腊人和特洛亚人的祸害。你真该死,你那太漂亮的眼睛,竟自就这样可恶的毁灭了特洛亚的闻名的郊原!”当她把衣服裹在孩子身上,把花冠戴在他头上,她的悲哀社会看透神的闹剧:“神们并不想作什么别的,只是把灾难降到我身上,降到特洛亚城里,这都城是他们最恨不过的。”所以杀牛献祭又如何?敬神又如何?“若不是神……把我们摔在地下,我们便会湮没无闻,不能在诗歌里享受声名,不能给后代人留下这可歌可泣的诗题。”这是巨大的讽刺,曾经的祈祷不肯听,曾经的呼唤没有回应,特洛亚女人的命运就在这城市的坍塌中成为神的祭品。
但是当赫卡柏拖着战栗的腿“引导我去过奴隶生活”的时候,她或许不知道神正在酝酿着另一种报复,一开场出现的就是波塞冬,他看到了不幸的赫卡柏,看到了苦命的波吕克赛娜,看到了疯狂的卡珊德拉,这些女人悲惨的命运都呈现在他面前,所以他指责希腊联军,尤其是阿伽门农“未免太不顾神意,太不够虔敬了”,而他遇到的雅典娜也抱怨希腊人侮辱了自己的神殿,因为“埃阿斯从那里把卡珊德拉强行拖走了”,于是在不敬神的现实面前,雅典娜希望波塞冬和她联合起来,“为了特洛亚,为了我们这脚底下的都城”惩罚希腊军队,而这种惩罚的目的只有一个:“请你在爱琴海道上激起怒吼的波涛和回旋的流水,用希腊人的尸首填满欧玻亚的海湾,让希腊人日后知道敬重我的神殿,崇拜其余的众神。”
雅典娜因为希腊军队侮辱了自己的神殿,所以认为他们不敬神,而不敬神的一个后果就是让他们是尸体填满欧玻亚的海湾,这是被预设的悲剧,当特洛亚妇女成了奴隶而踏上未知之路的时候,这一场灾难便发生了。但是很明显,对希腊军队的惩罚完全是雅典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特洛亚陷落是而报复他们,所以即使特洛亚妇女在巨大的悲痛中成为奴隶,当她们目睹了希腊军队的尸体填满欧玻亚的海湾,她们也并非是完成了复仇的目的。神的争吵引发了特洛伊战争,神的不满又摧毁了作为胜利者的希腊联军,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一切也变成了神制造的悲剧——当特洛亚妇女一直敬神,他们缘何要承受生命的巨大代价?“我们真是白白的给他们杀牛献祭!”
对神的谴责是对自身命运的喟叹,而对自身命运的喟叹又折射出女人的悲剧,当神对希腊军队的惩罚在这部戏剧中成为一种缺省,是不是神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忽视了人的存在?这是一个英雄时代,是神明时代之后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英雄是不是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九场剧《阿尔刻提斯》里也有神,他是宙斯的儿子阿波罗,他也是睡神的孪生兄弟死神,但是和《特洛亚妇女》中神在缺省中制造了复仇故事不同,在这里,神似乎介入到了人的生活里,阿波罗只是斐赖城的畜牧保护神,是宙斯“逼着我来为凡人服务”,他遇见了死神,而死神告诉他,今天,国王阿德墨托斯的妻子必须去死,因为她要替自己的丈夫到下届去,于是,“一切的礼仪国王都尽到了,所有的神坛上都供满了血红的祭品,这灾难依然是无法挽救。”
灾难无法挽救,到底是怎样的灾难?阿波罗是这场灾难的旁观者,他甚至问死神:“那么,阿尔刻提斯能不能活到老呢?”死神的回答是:决不能,“一个人死得年轻,于我更光荣。”对于死神来说,让一个人死就是让自己享受权利,所以死亡不可避免,但是作为旁观者的阿波罗,并不是想要挽救这一种死亡,甚至这场死亡就是自己导致的,“我曾骗过了命运女神们,救他一命;可是那三位女神却这样答应我:只要有一个死者代替阿德墨托斯到下界去,他便可以逃避这临头的死亡。”他就是斐瑞斯的儿子阿德墨托斯,因为阿波罗为了救他而欺骗了命运女神,命运女神没有让他死却需要有人代替,于是阿德墨托斯的妻子阿尔刻提斯成了代替者,也就是说,阿波罗解救了身为男人的阿德墨托斯却将女人阿尔刻提斯推向了死亡深渊。
面对死,即使是阿尔刻提斯自愿,也是人世间的悲剧,对于阿尔刻提斯来说,她虽然成为了贤淑的符号,但是她必须承受家庭的悲剧:“永别了,愿你们很幸福;我的丈夫,你可以夸说,你娶一个最贤良的妻子;孩子们,你们也可以夸说,你们出自一个最贤良的母亲。”阿尔刻提斯是用自我牺牲的精神让丈夫活着,这是一种成全,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男权的体现——为什么阿德墨托斯不能自己去死?这其实就是一种人间的悲剧,而阿德墨托斯在妻子为他替死的时候,竟也开口骂自己的父母不够伟大不能主动像妻子一样成全自己,“我憎恶那生我的母亲,也怨恨我的父亲:他们只是口头上爱我,不是事实上爱我。”而他的父亲斐瑞斯把阿尔刻提斯的行为也看成是伟大,“她敢于作出这高贵的行为,使世间妇女的生命显得分外光辉。”但是面对儿子的指责,他的回应完全是一种家庭伦理的反驳,“我只是生你,把你养来作这宫中的主子,可没有替你死的义务,因为我并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祖传的习惯,或是希腊的律法:当父亲的应该替儿子去死。”甚至他从阿尔刻提斯的替死行为中反衬出阿德墨托斯作为一个男人的懦弱:“你这坏东西却远不如你的妻子,她替你死了,替你这漂亮的年轻人死了!你发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可以长生不死,只要你劝得动你每个时期内的妻子都替你死;你自己怯懦,却要骂那些不愿替你死的亲人!”
父子之间两个男人的对话,充满了浓浓的家庭气息,他们的这种伦理观完全是人意义上的,而这种讨论把阿尔刻提斯当成是一种伟大,其实也是一种不平等——对于欧里庇得斯来说,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他把妇女的地位提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地步,为的就是成为贤淑忠诚的人,成为牺牲自我的人,但是这种进步隐含着英雄时代的男性思想,而这种男性思想更是神话时代的一种折射:阿波罗自己被宙斯惩罚而为凡人服务,自己解救凡人却得罪了命运女神,在死神实现自己的权力面前又无能为力,倒是赫拉克勒斯,因为来到阿德墨托斯的宫殿听到了这个死亡事件之后,为了报答阿德墨托斯的恩惠,决定将死去的阿尔刻提斯重新带回人间,“我要把她交到你那唯一的右手里。”
死去的妻子重新来到自己身边,这对于阿德墨托斯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幸福,也是对于自己逃避死亡而被人羞辱的一次拯救,所以他感激赫拉克勒斯,并且赞扬宙斯:“至大的宙斯的高贵的儿子啊,愿你有福,那生你的父亲会保护你,只有你才挽救了我的命运!”神的权力超越了命运,神便成为人的唯一主宰,就像歌队所唱的那样:“神明的分配式样多端,他们总是作出许多料想不到的事。凡是我们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我们所期望不到的,神明却有办法。这件事也就是这样结局。”但是当阿尔刻提斯经历了死亡和复活,当阿德墨托斯经历了悲痛和欣喜,当人的命运完全被神主宰,是不是反倒是人间的一种悲哀?
这种悲哀正如复活的阿尔刻提斯没有说话一样,人在神的面前是沉默的,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在“神明的分配式样多端”中成为一个游戏。九场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和《阿尔刻提斯》有着几乎相同的主题,伊菲革涅亚作为阿尔戈斯国王阿伽门农的女儿,却在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远征军去攻打特洛亚时被祭奠给神,“我父亲以为,为了海伦的缘故,在欧里波斯的疾风时常吹动蔚蓝的海水,掀起涡流的地方,在奥斯的闻名的山峡中,已经把我杀死,祭了阿耳忒弥斯。”女儿成了牺牲品,就是为了敬神,但是伊菲革涅亚没有死去,祭奠给阿尔忒弥斯却又被阿尔忒弥斯所救,她用一只母鹿将伊菲革涅亚换走,最后成了阿耳忒弥斯神庙的祭司。
和阿波罗将阿德墨托斯解救出来用了替换法一样,伊菲革涅亚的命运也在替换的过程中被改写了,神主宰着他们的生死,而当在祭司中遇到了自己的弟弟俄瑞斯忒斯,亲人相见让他们格外高兴,也是在灾难频仍的时代看到了幸福,而这一切的到来都是神的作用,所以伊菲革涅亚感叹:“哪一位天神,凡人,或意外的机缘能在这走投无路时指出一条路,让阿特柔斯这两个唯一的后人脱离灾难?”但是俄瑞斯忒斯是陶里刻的敌人,国王也正在追杀他,当亲情降临,他们设计了逃跑计划,而作为女人的伊菲革涅亚希望弟弟带走神像之后能顺利逃脱,“只要救了你,我就是活不成,我也不怕,因为,实际上,只有男人扔下家死掉才可悲;至于一个女人倒是无关紧要的。”也像阿尔刻提斯一样,为了成全男人的事业,自己可以作为牺牲者。但是这并非是最终的结局,当陶里刻国王托阿斯准备追击时,神出现了,雅典娜对他们说:“快停止追捕,停止遣派这潮水般的队伍,因为罗克西阿的神示预先派定俄瑞斯忒斯到这里来,好让他逃避报仇神的愤怒,把他姐姐送回阿耳戈斯,把那神圣的像带到我的土地上。”
这是新的神示,连同俄瑞斯忒斯盗取神像,也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最后让波塞冬让海平面平静,“让他坐船走了。”在神主宰一切命运中,歌队长唱出了这个英雄时代的主题曲:“最尊严的胜利女神,请保护我一生,不要忘了给我戴上花冠!”是因为他们敬神才有了幸福见面的机会,才有了不被追杀的苦难,而当这些都成了命运,也只是神的一个游戏。《阿尔刻提斯》里的女人,是敬神的女人,是得到了保护的女人,《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里的女人,也是敬神的女人,也是得到了保护的女人,似乎女人在神的荣光里才能拥有自己的地位,才能获得自己的命运,而在《美狄亚》里,当美狄亚被伊阿宋所背叛,她是不是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女人?
“但愿阿耳戈船从不曾飞过那深蓝的辛普勒伽得斯,飘到科尔喀斯的海岸旁,但愿珀利翁山上的杉树不曾被砍来为那些给珀利阿斯取金羊毛的英雄们制造船桨;那么,我的女主人美狄亚便不会狂热的爱上伊阿宋,航行到伊俄尔科斯的城楼下,也不会因诱劝珀利阿斯的女儿杀害她们的父亲而出外逃亡,随着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来住在这科任托斯城。”保姆说出了这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当爱情变成仇恨,一个来自外乡的女人,一个杀死了弟弟的姐姐,一个背叛了祖国的人,却在命运中再次成为了背叛的牺牲品,而且,美狄亚面临着被驱逐的困境,所以她悲叹的是一个女人的不幸:“哎呀,我受了这些痛苦,真是不幸啊!哎呀呀!怎样才能结束我这生命啊?”
最开始她希望自己死掉,因为生命随着爱情的死亡已经没有了任何乐趣,而这一切在美狄亚那里完全上升到女人的不平等地位,她说:“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她认为,“离婚对于我们女人是不名誉的事。”她叹息:“男人住得腻烦了可以到外面去散散他心里的郁积,我们女人就只能靠着一个人。”但是美狄亚不是一个臣服于命运的人,正是看透了女人的弱势,所以她要变成复仇者,“就在这一天里面,我可以叫这三个仇人,那父亲、女儿和我自己的丈夫,变作三个尸首。”但这不是最终的报复,她甚至在最后时刻,杀死了自己亲身的孩子——作为一个母亲,要将自己亲身的孩子置于死地,如何下手?美狄亚的回答是:“因为这样一来,我更好使我丈夫的心痛如刀割。”让丈夫心痛如刀割,这是对丈夫的报复,而无辜的孩子成了牺牲品,这无论如何是一种杀戮,即使面对伊阿宋的责难,美狄亚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啊,孩儿们,这全是你们父亲的疯病害了你们!”
孩子死去,对于伊阿宋来说,是最为悲痛的事,这和死去的另一任妻子格劳刻不同,伊阿宋对他们有着真感情,当这些可爱的孩子不再有生命,这是多么悲痛的事,所以美狄亚的这一复仇计划得到了满意的后果,但是孩子的死去自己也是罪人,“我要把他们带到那海角上的赫拉的庙地上,亲手埋葬,免得我的仇人侮辱他们,发掘他们的坟墓。我还要规定日后在西绪福斯的土地上,举行很隆重的祝典与祭礼,好赎我这凶杀的罪过。”即使她想要赎罪,这一种杀戮式的报复似乎也掩盖了对女人命运把握的伟大,而其实,美狄亚能够成为最极端的复仇者,正是因为她救助了神的帮助,“只要神明帮助我,我要去惩罚那家伙!”即使复仇女神没有出面,美狄亚也在这种敬神的祈祷中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性,而歌队长又唱出了对于神的赞美:“宙斯高坐在俄林波斯分配一切的命运,神明总是作出许多料想不到的事情。凡是我们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而我们所期望不到的,神明却有办法。这件事也就是这样结局。”
复仇女神,胜利女神,命运女神,波塞冬,阿波罗,雅典娜,这些神在人的上面,敬神或不敬神成了他们判断的一句,也成了人生或死的标准,而女人几乎都是在这样一种神的安排中生活,欧里庇得斯为什么在这些悲剧中依然给了神这么大的权力?一个反对内战同情穷人和女人的诗人,一个反对虐待妇女拥护民主的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对神充满了怀疑,普洛塔戈刺斯曾读到过他的一段论文,“关于神,我就不能够断言是否真的有神存在。这点的认识有许多障碍:第一,是对象本身的不明确;其次,是人类寿命的短促。”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种不敬神的态度,但是在悲剧里,当人的命运无法摆脱神的控制,这种怀疑论是不是变得空泛?而其实,当神制造了人世间的游戏,当神着意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实际上这些神都是人的一种投影,他们在喜怒哀乐中制造了神示,他们在悲欢离合中主宰人的命运,这样的神何来威严?无非是另一种人的写照,当他们自己打破了神世界的规则,不仅神话时代终结了,而且英雄时代也失去了崇高性。
所以在人的时代,狄俄倪索斯降临人间,唯一要做的事是证明自己是一位天神,“卡德摩斯把他的宝座和王权传给了他的外孙彭透斯,这人反对我的神道,不给我奠酒,祷告时也不提我的名字,为此我要向他和全体忒拜人证明,我乃是一位天神。”作为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狄俄倪索斯承受着污名化的命运,“说我狄俄倪索斯不是宙斯所生,她们诽谤说塞墨勒同凡人结了私情,却把失身的罪过推在宙斯身上,又说这是卡德摩斯说诳;她们还狂妄的说,宙斯因此把她杀死,都只怪她隐瞒私情,说了假话。”所以他要要给不敬神的人以惩罚来做这一道证明题。于是他让忒拜人狂欢作乐,在酒神的世界里丧失自我。而这自然遭到了忒拜国王彭透斯的反对,他认为这是奇怪的祸事:“据说我们的妇女都出了家门,去参加巴克科斯的虚伪仪式,在山林中到处游荡,狂歌乱舞,膜拜新神狄俄倪索斯,不管他谁;每个狂欢队里都摆着盛满酒浆的调缸,她们一个个溜到僻静地方,去满足男人的欲望,假装献祭的狂女,其实是把阿佛洛狄忒放在巴克科斯之上。”
狂欢是释放了人的欲望,但却违背了神的尊严,但是这一切不正是酒神狄俄倪索斯制造的?而且狄俄倪索斯还诱惑了彭透斯,让他加入了狂欢队伍,而且从树上跌落致死,并且让那些狂乱的女人撕扯他的尸体,“她们把彭透斯的肉抛来抛去,每一只手都染了血。”彭透斯的母亲阿高厄在狂欢中甚至没有认出那肉是儿子的尸体,“忒拜地方有美丽望楼环绕的都城的居民啊,你们前来看看这猎物,这是卡德摩斯的女儿们猎获的,我们使的不是忒萨利亚的缠了皮带的标枪,也不是网,而是我们的白嫩手掌。”这是一场悲剧,以狂欢的形式上演的悲剧,而悲剧的制造者是那个为了证明自己是天神的狄俄倪索斯,所以忒拜城的建立者卡德摩斯目睹了这一悲剧,他一方面对阿高厄说:“因为你们侮辱了他,不相信他是神。”一方面又质问狄俄倪索斯:“我们认罪,但是你也未免太严厉了。”当狄俄倪索斯说因为我是神,受到了他们的侮辱,卡德摩斯的回应是:“可是神不应该像人,动不动就生气。”
这或许是欧里庇得斯代表人类对于所谓的神发出的质疑,当神动不动就生气,是不是就是一般的人,甚至是没有威严的人?而卡德摩斯最后的选择是离开:“女儿呀,我们全都陷进了可怕的灾难中,你和你的姐妹们很悲惨,我也不幸:我老了,还须到外夷地方作客;此外还有一个神示,说我会引导外夷的联军来攻打希腊:我将化作一条龙,带着我的蛇形的妻子,阿瑞斯的女儿哈耳摩尼亚,引导戈矛来袭击希腊人的神坛和坟墓。哎呀,我不能结束我的灾难,也不能渡过那流入下界的阿刻戎河,从此安眠。”这是看透了一切所谓神的预言的人最大的痛苦,而卡德摩斯的这种态度完全是对于神的蔑视,甚至就是对制造而来神话的人的批判。神产生了嫉妒,神制造了战争,神设计了游戏,神不是为了让人敬神,是神自己摧毁了神殿,于是神变成了人,而人的悲剧就在于这样一个悖论:“那敬神的人竟叫那不敬神的人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