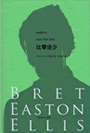 |
编号:C55·2181014·1502 |
| 作者:【美】B·E·埃利斯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42.00元亚马逊18.50元 | |
| ISBN:9787532766772 | |
| 页数:224页 |
《比零还少》是埃利斯的成名作兼代表作,已被公认为二十世纪“邪典文学”经典。小说以大学生克莱回洛杉矶度圣诞假为主线,通过电影分镜头般的画面,电子乐般的节奏,面无表情的语调,锋利简短的章节,切割出18岁的克莱和他的朋友们——一群天使之城的富家子弟,一群堕落天使——的迷乱生活,“我没有把你变成婊子。是你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婊子。”这场埋葬青春与纯真的葬礼式派对从另一个极端的角度,提示了在后工业化时代,在物质极度丰富的表相下人性的脆弱与异化,即我们拥有一切,所以我们一无所有;这是最好的人生,所以这也是最坏的人生。《比零还少》出版于1985年,这一年奥威尔《1984》的时代似乎刚刚成为过去。
《比零还少》:因为死神总是在的
男人压到朱利安身上。
不知道他人卖不卖。
就此消失。
我没有闭上眼睛。
男人压在男人身上是猥亵,“不知道人卖不卖”是还债的质问,“就此消失”是逃避和虚无,当暴力和羞辱上演的时候,我应该选择不看,可是我没有闭上眼睛,当一切不应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是更为痛苦的存在,是更无从躲避的面对,甚至要从一个旁观者变成见证者——那时费恩看看我,又看看朱利安,说了一句话:“你别无选择。你明白吗?你走不了。你在不可能走。你要去找妈咪还是爹地,啊?”
对朱利安说的话,就像是对我说的。因为朱利安欠钱,因为朱利安无法还清,因为朱利安一次次失约,所以费恩在圣马奎斯的那个房间里让朱利安付出了代价,“一年前你欠了那些毒贩子一屁股债跑来找我,我给你工作,帮你吹捧,带你见人,你所有这些衣服,你吸的他妈的所有可卡因,都是我给的,你回报了我什么?”有付出需要有回报,这是一个规则,朱利安因为破坏了规则,所以被压在下面,所以一切的尊严消失,所以人变成了商品,肉体可以出卖,朱利安“你把我变成了婊子”的喊声已经无力,而这只不过是开始,接着费恩拿出了针头,然后把针头戳进了朱利安的胳膊,我在没有闭上眼睛的时候看到血充满了注射器,听到说:“你是个很美的男孩。这才是关键。”心中问的是:“不知道他人卖不卖。”——斜体的字,分明是我的内心挣扎,和“就此消失”一样,“不知道他人卖不卖”变成我永远的疑问。
卖不卖或许还是一种可选择的答案,就像无论是压在身上猥亵,还是血注入胳膊的惩罚,至少是一种代价的偿还,可是当我没有闭上眼睛离开朱利安被处罚的现场,那个吸毒过量死去的人被看见,却是一种卑微生命的丧失,“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具死尸。有飞蛾在他头上飞,绕着挂在他上方的灯泡打转,灯光照亮了下面。”那个十二岁的少女被注射器推进胳膊,是一种彻底的沦落,“女孩没睁开眼睛。”而我起先跟着朱利安进去的房间,更是带来了记忆之中死亡的复现,“我讨厌宾馆。我伟大的祖父就死在宾馆。拉斯维加斯的星辰宾馆。他死了两天才被发现。”
十八岁,回来,回到洛城,回到曾经生活的地方,回到有朋友家人的地方,四个月之后回来到底意味着什么?“洛城人怕在快车道超车。这是我回来听说的第一件事。”为什么怕在快车道超车?因为必须加快速度,因为危险无处不在。快车道提供的是一种城市场景,它是对外的,是社会化的,是一种规则,我以为回来就是回到家,就是重温记忆,就是远离快车道,“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发现什么都没变。墙还是白的,唱片还在原处,电视机没搬走,百叶窗开着,一如我走的时候。”但是这个如乌托邦存在的房间更像是自我的臆想,当一切都通向了快车道,回来意味着“我没有闭上眼睛”而看见了一切。
回来听说缪丽尔患了厌食症正在医院里,回来听说拉奥是双性恋,回来知道克里夫跟所有人睡,听说和知道,似乎我还在现实之外,但是当“洛城人怕在快车道超车”变成了回来之后听说的第一件事,似乎自己也在这种极度恐惧的状态下开上了超车的快车道。起先只是和特伦抽烟和百事可乐,只是和丹尼尔和潘趣酒,只是和布莱尔谈论四个月钱的分手,甚至只是听到缪丽尔患厌食症而感到恶心,但是,当和那一些曾经好友在一起,回来改变了一切。瑞普用刀片在粉末上划出四条粗线,那一张卷起来的二十美元变成了工具,“我弯下身吸了一条。”格瑞夫把我带进房间,然后慢慢脱掉了内裤,事情发生之后,我盯着镜子里的裸体看了一会儿,“然后趴在洗手池上,打开龙头把冷水泼到脸上。”我开始戴墨镜,开始理头发,开始戴围巾,却带来了另一种不安,“我不停地看后视镜,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谁在跟踪我。”
“我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映出我放荡的、可卡因式的傻笑。”这便是我回来没有闭上眼睛而看见的自己,当那个放荡的、可卡因式的傻笑留在镜子里的时候,是不是仅仅是一种镜像?看见的一切还有那本色情杂志,封面的薄膜照片上两个女孩手里握着马鞭;还有杀人的暴力电影,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被割开喉咙扔进游泳池;还有充满了死亡的新闻报纸: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意外开枪射死了他兄弟;印第奥的一个家伙把他孩子钉在墙上,然后近距离用枪射他;一幢老人之家起火死了二十人;一个家庭主妇开车从学校接孩子回家时,从八十英尺的路堤上飞落而下,自己和三个孩子都当场死亡;一个男人镇定自若地来到前妻家,把她活活掐死,“那段时间我收集了许多这样的剪报,那是因为,我想,有太多这样的事情。”
或者,镜子、杂志、电影,以及后视镜里可能的跟踪者提供的仅仅是镜像,那么在现实意义上,我一样是不能闭上眼睛地看见了一切:缪丽尔闭上眼睛,注射器里慢侵充满血液;萝莉告诉我:“我该怎么改变这一切?于是我想,如果我做点什么,比如说,给耳朵穿孔,改变一下形象,染染头发,这世界就不会融化。所以我就染了头发,染成粉红色。我喜欢这种颜色。它能保持很久。我想这世界不会融化了。”因为吸可卡因上瘾,和瑞普斯宾去马里布买可卡因,而那个人的名字就叫死神,就像瑞普所说,“因为死神总是在的。”死神无处不在,死神就是每个人的名字。而当看见这一切,当死神无处不在,还有什么救赎?电视里的宗教节目无非是一种象征,“天父啊,让这些囚徒获释吧。他们,他们身处牢笼,教诲他们吧。感谢我主。让今夜成为解脱之夜。对主说,‘原谅我的罪’,你会感到无法言喻的欢乐。愿你杯中酒满溢。以基督之名,阿门……哈利路亚!”它一样提供娱乐提供消费提供虚妄的镜像现实。
但是,在这一切发生在回来的故事里的时候,对于我来说,似乎还希望寻找到一些东西,和布莱尔之间的爱情,是不是在分开四个月之后重归于好?我知道布莱尔还喜欢我,还保留着曾经在海滩俱乐部的美好,但是当回来,这种美好却变成了肉体之间的交媾,“我躺在布莱尔床上。地板和床脚全是毛绒动物玩具。”我在朋友面前说的是:“我跟布莱尔已经没关系了。我们已经结束了。”而当我最后决定回新汉普郡的时候,面对布莱尔的发问,我终于说出了“我没爱过”,彻底将一种所谓的爱情埋葬在肉体的世界里。
和父母之间的亲情,是不是还可以维持?父母在我眼前,但是他们本身就活在一种疏离的世界里,而我夹在中间似乎再没有回去的可能,于是,我想到了那年夏天的棕榈泉,想起了阳光和酒吧,想起了在一起的故事。但是充斥其中的还有烦闷,还有炽热,还有无法摆脱的压抑。不同字体插入的回忆里,祖母说:“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死去”,于是两个月后祖母死了,“在漠边上一个空荡荡的医院房间里,一张高高的大床上。”不同字体插入的回忆里,大家说起的是一个十三岁小孩买海洛因,最后吸毒过量死了,说起父亲的生意伙伴死于胰腺癌,母亲认识的网球搭档刚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不同字体插入的回忆里,是青春在无聊里的释放,“我和妹妹们会开着车半夜在沙漠里乱转,一边听佛利伍德·麦克或老鹰乐队,声音开得很响。”
十五岁已远,去年夏天的棕榈泉已远,四个月前和布莱尔的爱情已远,甚至真正的青春也已远,走进自己的小学校园,看见曾经像自己一样的孩子,看见曾经认识的老师,却不再打招呼;那架弹过的钢琴保存着一点记忆,“我弹过这架钢琴,同一架钢琴,在二年级的圣诞音乐会上。我又敲了几个和弦,就是当年我弹的曲子,它们在空荡荡的礼堂里回荡。”如今却剩下恐惧,却换来逃避,就像祖母的死,就像酒吧里的白化病人,就像日落大道的“就此消失”的广告牌,回来看见的一切都意味着从此消失,那个梦中反复出现的男孩,“还没死,横躺在火焰上,燃烧着。”也是我的一个噩梦般的镜像。
没有闭上眼睛而看见,记忆和现实,臆想和当下,以前和现在,其实根本无法分开,而当我决定要离开,有一种“回去”的决定,是不是可以将这一切放在身后?在离开的一个礼拜,反反复复听关于这桌城市的歌,呆在房间里看一个下午的电视秀,和朋友一起去穆赫兰道兜风,但是在走之前,一个女人被割开喉咙从行驶的车上扔下来,一个男子试图活埋自己因为“实在太热”而放弃——而那时,我的两个妹妹正在装溺死,“比谁死的时间长”。现实和游戏混合在一起,死在某种意义上去除了恐惧感,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同的字体是回忆是酒吧是海滩,不同的字体是“不知道人卖不卖”,不同的字体是“你是个很美的男孩。这才是关键”,不同的字体最后是“好像从未离开”,疯狂的派对,暴力而血腥的电影,色情的杂志,圣诞节吸飘了的状态,触目惊心的死亡事件,梦中被火烤着的自己,这便是十八岁的青春,便是回来的世界,死神无处不在,“没爱过”却成为常态,回来是为了离开,离开也是为了回来:
在那些场景里,我看到这座城市里的人被生活逼疯。看到饥饿贪婪的父母要吃自己的孩子。看到那些跟我一样大的年轻人,在柏油路上仰头张望,被阳光刺盲。即使在我离开以后,那些场景也挥之不去。它们那么恐怖,那么残暴,那么邪恶,几乎成为我很长时间里唯一的参照。在我离开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