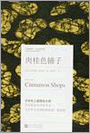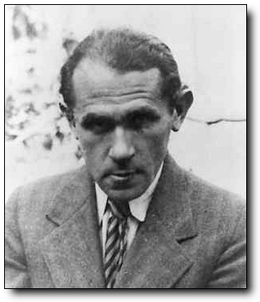|
编号:S38·2130126·0942 |
| 作者:【波兰】辛波斯卡 著 | |
|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09月 | |
| 定价:26.00元 | |
| ISBN:9787540457228 | |
| 页数:201页 |
“每个开始/毕竟都只是续篇,/而充满情节的书本/总是从一半开始看起。”有时候,很难对“静默”的万物一见钟情,而20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当辛波斯卡溘然长逝的时候,那本书或者真的只有一半了。甲虫、海参、石头、沙粒、天空;安眠药、履历表、衣服;电影、画作、剧场、梦境等等,在这些静默的万物中,辛波斯卡似乎找到了深藏其中的诗意,用笔让它们焕发出新的诗意,让人们重新认识生活中常见的事物。“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最为迷人的诗人之一”、“《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图书,作品曾被收入国内高中语文教材”……这腰封上的注释,其实已经将日常生活的“万物”隔离开来了,只有“辛波斯卡”的名字如谜呈现。这里收录的75首诗歌,包括激发知名绘本作家幾米创作出《向左走,向右走》的《一见钟情》,收录高中语文教材的《底片》,网上广为流传的《在一颗小星星下》被选入韩寒杂志“一个”的《种种可能》等等。
噢,甜美的短歌,你真爱嘲弄我
因为我即便爬上了山丘,也无法如玫瑰般盛开。
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别的不能。那毋庸置疑。
——《企图》
是的,那封面盛开如艳的花真的不是玫瑰,宽阔的叶面和怒放的花朵,在灰色的调子里吟唱,但是“万物静默”,听不到那盛开时的声音,默默如被“嘲弄”一般,所以,不管是“爬上山丘”,还是“企图长出枝叶”,蜕化成玫瑰都是一种“无情”的遐想而已,甚至也只是无法抵达的“企图”。“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而封面里的那个暗喻只是走向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体:
甜美的短歌,你对我真是无情:
我的躯体独一无二,无可变动,
我来到这儿,彻彻底底,只有一次。
这便是辛波斯卡,她的名字后面是一串有关纪念的数字:1923-2012,中间的连接号是过程,是生命,是成为玫瑰的“企图”,是“只有一次”的彻彻底底的躯体。2012年2月,辛波斯卡溘然长逝,而在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封面那朵不是玫瑰的盛开中,仿佛读到了那些无情的“甜美短歌”。或者阅读也是一次中间插着连接号的过程,从过年之前打开而合拢,到过年之后再度翻阅,被停顿的过程里是一个时间的段落,或如生命一般。而阅读的体验,对于我来说,也是在接近辛波斯卡的一次企图,玫瑰如玫瑰,而“我即便爬上了山丘”,即便长成树丛,也不是真的接近了辛波斯卡玫瑰的世界。
《企图》,诗集里的第一首,收录在1957年的《呼唤雪人》之中。而对于辛波斯卡来说,这样的“企图”,这样不是玫瑰的玫瑰,却开在她的一生里,那“彻彻底底,只有一次”的“甜美的短歌”一直在生命中响起,“我就是我。/一个令人不解的偶然,/一如每个偶然。”2002年出版的诗集《瞬间》里的这首《在众生中》,依然能感受到对于生命的某种偶然情愫,而这种“令人不解的偶然”不是她的无奈,也不是宿命,是众生之中寻找到的个体意义,“我也没有选择/但我毫无怨言”不是逃离离群的努力,而是做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是回归自我,回归生命的表态。而这“一无惊奇而言”的我,也一如“植物的沉默”:“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一些东西”,那种生长的自然状态或许是辛波斯卡的一生都在寻找的。
其实对于生的“企图”,对于死也一样只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在《墓志铭》里,辛波斯卡也是用淡然地笔触为自己写下了人生的总结:
这里躺着,像逗点般,一个
旧派的人。她写过几首诗,
大地赐予她长眠,虽然她生前
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
她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
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珍物。
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
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用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这似乎显得很无情,那短歌也仿佛没有声响,那玫瑰更是一种传说而已,“逗点般”的旧派的人,不加入任何文学派系,墓地里也只有“小诗、牛蒡和猫头鹰”的静默万物,命运到最后也只是一串数字而已。但是这样的短歌,这样的人生和自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辛波斯卡的自我认同?“在我仓促的人生中,如此急促/却被永远搁置。”这或许是在“植物的沉默”中,偶然闪现的一丝无奈,甚至不妥协,而这种“永远搁置”的遗憾在辛波斯卡的命运轨迹和诗情中似乎能找到一些痕迹。
诗集《万物静默如谜》收录的是1957年至2002年的诗作,而延至一九五二年出版,名为《存活的理由》的诗集并未收录,那时波兰共产党政权得势,主张文学当为社会政策而作。辛波斯卡于是对其作品风格及主题进行全面修改,而这样的修改对于辛波斯卡来说,越来越远离自我,远离生命和诗歌的意义,未被收录或许就是一种拒绝的态度,而在其他诗作里,一样可以读到辛波斯卡对于现实的无奈。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布鲁格的两只猴子》里“用叮当作响的轻柔铁链声”;现实是的“手输给了手套。/右脚的鞋打败了右脚。”的《博物馆》;现实是“内在背离你”没有门的石头;现实是“气味让我反胃”的医院;现实是一只隐形的手“一把抓向我的喉咙”的剧场;现实是“透过窗帘的缝隙/窥探外面的街景”的“色情文学”……
现实是现实,现实也是历史,现实当然是不在场的一种日期而已,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里,不再引起共鸣的日子“诸如此类”,而“我当时潜藏于何处,/隐匿于何处?/在自己的眼前消失/可是相当不错的幻术。”这是消除历史某种证明和在场的努力,是自我逃避的开始,也是对于宏大的叙事的不屑,“比思想更淫荡的事物”充斥着,而每个人似乎也没有了自己的方向,“每个人交合的只是自己的双腿”,所以在更多意义上,辛波斯卡是害怕现实的淫威,是《有些人》里的那个世界,有枪响,有飞机,有敌人,“有些人逃离另一些人。/在某个国家的太阳/和云朵之下。”在她看来,这个世界应该是透明而简单的,如植物的沉默一样,没有太多的肮脏、淫荡和压制,世界“无非是整整一秒钟”。甚至历史也只是每一个人有关的童年,在《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里,便把那个独裁者的童年描绘成一个简单而充满善意的初点,是可爱的小天使,是妈咪的阳光,是甜心宝贝,“这里听不见狗吠声或命运的脚步声”,而这一切在历史那里却变成了另外的模样,“历史老师松开衣领/对着作业簿打哈欠。”
在辛波斯卡看来,这又是另一种“企图”,是用历史绑架现实的企图,是用恶绑架善的企图,是叶子绑架玫瑰的企图,是“人物是捏造的,急促是虚拟的”的企图,而她一定是要告别这样的沉重,告别这样的压制,告别这样的嘲弄,对于她来说,世界就是一粒沙一样的存在,“它存在于这个世界,无色,无形,/无声,无臭,又无痛。”,而自我则是浪花,“对浪花本身而言,既无单数也无复数”:“它们听不见自己飞溅于/无所谓小或大的石头上的声音”,浪花只是浪花,只是一种存在,一种不因时间而改变的世界原态而已,而既无单数也无复数,就是即不在众生之中,也不在孤独的自我里。
这是人类寻找自我的实践,辛波斯卡是一粒沙看到的世界,是浪花的飞溅,是逗点般的人生,所以“他不太能分辨梦想与现实,/仅能勉强弄清他便是他(《一百个笑声》)”他便是他,浪花便是浪花,而那个曾经想建立的思想岛屿也只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寓言”:“既不会太晚也不会太远。这个名叫‘这里’的岛屿无处不在。”这是第三个渔人的话,而”这里“便是此在,便是生命的意义,便是没有单数也没有复数的浪花,那么就抛弃那些病态的医院,充满杀戮的剧场,让自己成为人类的失物:“一个暂且归属人类的独立个体,/昨天遗忘在市区电车上的不过是一把雨伞。(《失物招领处的谈话》)”在这里,“我的兄弟姐妹都死了”,那些建立起来的关系和现实都幻灭了,而剩下的就是“我体内的一根小骨头陪我欢度纪念日”。
一把雨伞支撑起没有欲望,没有压制,没有历史的自我,那是没有差别的植物,那是无处不在的天空:
即使最高的山
也不比最深的山谷
更靠近天空。
任何地方都不比另一方拥有
更多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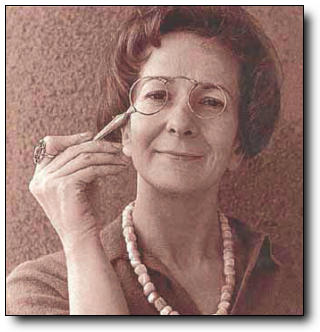 |
| 辛波斯卡(1923-2012) |
天空之于天空,就是自我之于自我,没有分别,没有昨天和今天的历史困扰,没有现实和理想的企图,“我早该以此开始:天空。/一扇窗减去窗台,减去窗框,减去窗玻璃。/一个开口,不过如此,/开得大大的。”一个开口,却是另一个大大的天空,世界也只是一种容纳,而辛波斯卡恢复一个人的诗意,而回归到“彻彻底底,只有一次”的人生,回归到“一如每个偶然”的自我,她便是走向了“一群人”的反面,成为“在众生中”的叛逆者。而这种自然意识、自由意识,对于辛波斯卡来说,则是对于玫瑰的无限接近,在这里有爱情,有自由,有诗歌。
一个女人的爱,是“一个女人的画像”:“她若非爱他,便是下定决心爱他。”而在《家族相簿》里,她说:“我的家族里没有人曾死于爱情。/令人欣慰的是,他们都死于流行性感冒。”这是对于一种家族宏大历史的反叛,而归于爱情的永恒,是“下定决心爱他”的毅然决然。在辛波斯卡的诗里,爱超越了很多东西,包括政治、历史和种族,在《越南》里,是和越南妇人的对话,所有关于名字、出生、害怕、战争等的问答,都是同一个答案:我不知道。而在连续九个不知道之后,最后的问题是:“这些是你的孩子吗?”回答是:“是的。”否定和肯定,是不是女性对于一种爱的坚持,但也是对于那些爱的缺失的无奈。爱是脆弱的,在《金婚纪念日》里,辛波斯卡描述了一对金婚爱人的行尸走肉的生活:
这两人谁被复制,谁消失了?
谁用两种笑容微笑?
谁的声音替两个声音发言?
谁为两个头点头同意?
谁的手势把茶匙举向两人的唇边?
谁剥下另一个人的皮?
谁依然活着,谁已然逝去
纠结于谁的掌纹中?
活着和逝去,身体和爱情,以及“性别模糊,神秘感渐失”的无奈,当所有的激情消失,剩下的或许都是“被褪成了白色”的生活。所以在这个爱情渐渐消失的生活中,辛波斯卡要唤回的仅仅是一种存在着的状态,一种最原始的力量,万物静默的背后,则是生命的意义。在她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说: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个字词的日常言谈中,我们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轨”之类的语汇……但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块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个白日以及持续而来的任何一个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任何一种存在都是生命的意义,不管是单数还是复数,不管是叶子还是玫瑰,都是抵达一种意义。而对于辛波斯卡来说,抵达意义的方式则是诗歌,“当代诗人对任何事物皆是怀疑论者,甚至——或者该说尤其——对自己。”怀疑就是抵达,抵达善,抵达我,“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而这种荒谬一方面是消除现实的无奈,另一方面却是构筑在“众生”视野之外的自己,写作是一种喜悦,在书写的森林里抵达爱的终点,“那么是否真有这么一个/由我统治、唯我独尊的世界?/真有让我以符号的锁链捆住的时间?/真有永远听命于我的存在?(《写作的喜悦》)”,而这是一种“保存的力量”,是“人类之手的复仇”。而写作的终极目的也就是接近现实,接近自我的存在,和妹妹“全部的文学作品都在度假的明信片上”不一样,诗歌里的那股“在亲人间掀起可怕的旋风”是间离着家族历史,而这正是一种可贵的荒谬,一种被称为“这里”的岛屿,所以在《我们祖先短暂的一生》里,那个不管是家族还是自我,都是人生之一种,都是“无论有多长,始终短暂”,甚至“短得让你来不及添加任何东西”。
不添加任何东西的人生也就是返回一次偶然,成为彻底的一次,而高贵的玫瑰依旧在那里开放,甜美的短歌再次响起,只是诗人已逝,“原谅我,虽然你已成为标本”,那岛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的乌托邦,只是一个人的浪花,只是一个人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