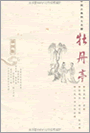 |
编号:X23·2160121·1252 |
| 作者:[明]汤显祖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63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20.00元亚马逊18.50元 | |
| ISBN:9787020051816 | |
| 页数:319页 |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有揣菱花,偷人半面,施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摇漾春如线”如何?“便把全身现”又如何?《游园》而《惊梦》,《寻梦》而《离魂》,《闹殇》而《还魂》,最后依然是破碎的“临川四梦”,强烈的反礼教、反封建色彩,追求个性由的光辉理想,是汤显祖对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的一次改写,而杜丽娘将《诗经·关雎》从对于“后妃之德”的歌颂到青春恋歌的怀想,也是一次彻底的改写,从此便走出闺房,在“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感叹中,唤醒了自己的青春活力。只是逝去的并不只是自由,无力的不只是青春,在游园之后,只能和情人在梦中幽会,而幽会以后《寻梦》,终于使得那一个隔绝的女子将郁积在心中的热情全部爆发,她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牡丹亭》:前亡后化,抵多少阴错阳差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作者题词》
生命“闹殇”而为死,死亡“回生”而还魂,生生死死所跨越的不止是梦境和现实,是花神和冥判,更是一种至情主义的写照,“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一阙《蝶恋花》的标目就已经为那情作了注解,白日消磨的是绍接诗书,是经世之学,世间所有的是“知书知礼,父母光辉”的婚姻,是“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礼德,而这并非指向至情的爱,即使情不知所起, 而一旦一往而深,便是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便是将梦中之情变成真切的现实,没有障碍,没有约束,在那牡丹残梦里延续最深情、至真的生死之恋。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汤显祖在作者题词里就已经划出了这种至情主义的对立面,那就是“理”,“理”便是当时大行其道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所以汤显祖的疑问在于,如果只是按照理学的意义来定义情,那这种情便是一个假命题,理之无,从来不会产生情之有,也就是说在灭人欲的现实里,即使“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也都是形骸之论,也都无法抵达至情的境界,所以,“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分明是一种打破理学禁锢的宣言,分明是在追寻一种跨越生死的至情。
杜丽娘作为有情人,从她身上体现着一种叛逆精神,生于名门宦族之家,从小受到的便是严格的儒学教育,父亲是南安太守杜安,他的人生理想便是“想廿岁登科,三年出守,清名惠政,播在人间”,而他“管治三年,慈祥端正,弊绝风清”留下的口碑也是理想的一种实践,而在金寇南窥时奉圣旨升安抚使镇守淮扬便也是对于政治生活的一种追求。而在子女教育中,她和妻子提出的便是要像古今贤淑一样,“多晓诗书”,目的就是“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甚至对于丫鬟春香,也是提出“知书知礼,父母光辉”的目标。所以他们给杜丽娘请的老师就是自幼习儒的陈最良,这个曾经参加乡试四十五年的儒生虽然是一个“凡杂作,可试为;但诸家,略通的”的读书人,但“陈绝粮”的名号仿佛又是一种讽刺。而他对于杜丽娘的教育也无非从礼仪道德方面入手,“《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从《诗经》入手,就是因为这经典是宣扬“后妃之德”,“《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螈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而最终的意义便是“有风有化,宜室宜家”。
但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却打开了杜丽娘另一个天地,那是“圣人之情”,在今古同怀的转变中,却也有了新的感触,“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书要埋头,那景致则抬头望。”埋头读书,是一种被定义的人生,而抬头眼望,则是看见了新的风景,所以消遣而游后花园,后花园而有“惊梦”,惊梦而有云雨之事,云雨之后而有感伤,“因春去的忙,后花园要把春愁漾”其实便是杜丽娘在稳重、矜持和温顺的生活中看见了苦闷,也开始了她对于现状的不满和怀疑,“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留下的是“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的感叹。
接受柳梦梅的爱情,就是她通往至情之路的第一步,也是她对于自身命运的第一次超越,而从惊梦到寻梦,也从南柯一梦的偶然变成了追求幸福的必然,而在现实的矛盾里,杜丽娘的梦似乎难遂人愿,八月十五团圆之日溘然长逝,便是这种矛盾的极致发展,而杜丽娘之死,是追求至情主义的另一个开始,在“冥判”中,杜丽娘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梦见一秀才,折柳一枝,要奴题咏。留连婉转,甚是多情。”这多情伤春,这多情也是一种抗议,最终她的游魂和柳梦梅相会,继续着以前梦中的美满生活,“妾千金之躯,一旦付与郎矣,勿负奴心。每夜得共枕席,平生之愿足矣。”但是毕竟是游魂,共枕席却也还是遗憾,所以杜丽娘对于幸福的追求更进一步,在和柳梦梅结合之后,又要求让她还魂复生,“妾若不得复生,必痛恨君于九泉之下矣。”她在“冥誓”中说:“奴家虽登鬼录,未损人身。阳禄将回,阴数已尽。前日为柳郎而死,今日为柳郎而生。夫妇分缘,去来明白。”生是为了至情,是也是为了至情,而最后复生而成婚,杜丽娘发出了“柳郎,今日方知有人间之乐也”的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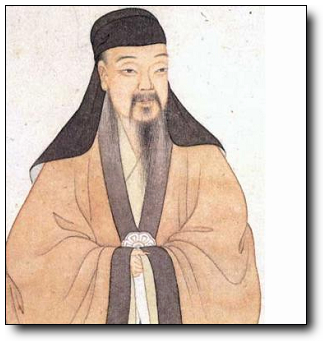 |
| 汤显祖:“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
杜丽娘在伤春之梦中与柳梦梅云雨,又在身死之后以游魂的身份幽媾,对于她来说,这都是在现实之外的情感表达,而复生的意义是回到现实生活,也就是在生生死死的过程中,她从一个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发展到痴情暮色一梦而亡的痴情女子,从伤春的柔弱女子到勇于寻找自身幸福的还魂女子,“一灵咬住”,其最终极的目标便是对感情决不放手,“生生死死为情多”,最终历经劫难,终得团圆。“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在杜丽娘生死追寻自己幸福的过程中,从最初对于陈最良关于《诗经》第一章的质疑,到后来要将自己葬身在梅树之下,从在冥府里与判官据理力争,到后来对抗父亲杜宝对柳梦梅弹压的淫威,都展现了杜丽娘历尽艰阻为情而复生的反抗精神,体现了“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的反叛。
但是,杜丽娘生生死死的经历所追求的至情主义,反对的是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权力体系,但其实,在这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浪漫故事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曲折经历却又陷入了一种悖论中。杜丽娘的父亲杜宝自称是唐杜子美之后,这不仅是一种家族式的续承,其实更是将人生使命纳入“清名惠政”的儒家思想体系里,而柳梦梅也自称是司马柳宗元之后,父亲是朝散之职,母亲是县君之封,他的朋友韩秀才也是韩退之之后,也就是说,不管是杜宝、陈最良,还是柳梦梅韩秀才,都追求着相同的经世之学,柳梦梅曾经就感慨:“凭依造化三分福,绍接诗书一脉香。能凿壁,会悬梁,偷天妙手绣文章。”而韩秀才也说过:“不患有司之不明,只患文章之不精;不患有司之不公,只患经书之不通。”读书做学问的意义一目了然,所以他们不成功名的原因就在于时运不济,而“岂非时乎,运乎,命乎”的疑问并非是否定这样一种读书的意义,而在于等待一种机会。
而作为至情写照的那个梦,不管是对于柳梦梅还是杜丽娘,也并非是自我主动追寻的结果,柳梦梅是在读书疲惫之时情思昏昏,最终在梦中看见梅树下立着的美人,于是改名,这种命名的背后是对于无法实现命运理想的喟叹,“梦短梦长俱是梦,年来年去是何年!”而其实,梦并非是虚幻,在《惊梦》中,杜丽娘走入后花园进入梦境之中,就是花神的姻缘安排,“吾乃掌管南安府后花园花神是也。因杜知府小姐丽娘,与柳梦梅秀才,后日有姻缘之分。杜小姐游春感伤,致使柳秀才入梦。咱花神专掌惜玉怜香,竟来保护他,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花神安排入梦,安排搂抱,安排云雨,也最终使得杜丽娘一梦而亡。
而在冥府之中,当杜丽娘述说自己的遭遇时,判官便拿来婚姻薄,一查才知道他们早就被写好了结局,“有个柳梦梅,乃新科状元也。妻杜丽娘,前系幽欢,后成明配。相会在红梅观中。”这“不可泄漏”的命运对于杜丽娘来说,无非是亦步亦趋地遵命就行,“我今放你出了枉死城,随风游戏,跟寻此人。”判官让游魂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相遇,所以杜丽娘对此充满了感激:“喜遇老判,哀怜放假。”而也正是这样的安排,才使得两人完成了“幽媾”的传奇,“梅边柳边,岂非前定乎!因而告过了冥府判君,趁此良宵,完其前梦。”
但这也只是一个生死之隔的梦,所以他们需要返回现实,回到真实的夫妻感情里,而还魂的安排也是一种神助,土地公公说:“今日开山,专为请起杜丽娘。不要你死的,要个活的。”于是那还魂丹便让杜丽娘重返人间,这“天开眼”的传奇也终于让生死之隔的遗憾变成至情的现实,“伴情哥则是游魂,女儿身依旧含胎。”从花神到冥府判官,再到土地公公,一切天注定,而这天注定的背后便是冥冥中被写好的人生命运,所以杜丽娘和柳梦梅无非是在神助之力下实践着自己的幸福梦想。
而促成这一段传奇婚姻的除了神助之外,还有两一种力量,那就是皇帝的圣旨之命。柳梦梅“偷天妙手绣文章”的目的是争取功名,所以他从广州到南安,遇见杜丽娘的鬼混,就是在赴试途中,而在金兵与宋兵对阵中,他所提出的“可战可守而后能和。如医用药,战为表,守为里,和在表里之间”的思想也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最后得到皇帝的赏识,也终于使他成为新科状元。杜丽娘和柳梦梅成婚之后,柳梦梅要去淮阳见自己的岳父岳母,但是杜宝却不相信这段姻缘:“前日有个棍徒,假充门婿。”所以要进行审问,而最终做出判决的还是皇帝,一是从“看花阴之下,有无踪影”来判断是人是鬼,二是杜丽娘的自身陈述,“臣妾二八年华,自画春容一幅。曾于柳外梅边,梦见这生。妾因感病而亡。葬于后园梅树之下。后来果有这生,姓柳名梦梅,拾取春容,朝夕挂念。臣妾因此出现成亲。”这阴错阳差最后终于感动了皇上,那圣旨上写到:“据奏奇异,敕赐团圆。平章杜宝,进阶一品。妻甄氏,封淮阴郡夫人。状元柳梦梅,除授翰林院学士。妻杜丽娘,封阳和县君。就着鸿胪官韩子才送归宅院。”
“姻缘诧,姻缘诧,阴人梦黄泉下。福分大,福分大,周堂内是这朝门下。齐见驾,齐见驾,真喜洽,真喜洽。领阳间诰敕,去阴司销假。”这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一个生死的悲剧最后变成一个喜洽的婚姻喜剧,其中虽然有对于父权的反抗,有追求自身幸福的勇气,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论是回生以后想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完成她和柳梦梅的婚姻的传统思想,还是在神助体现的神权、皇帝最后决断所拥有的君权,都无非是不彻底的反抗,是归于妥协的至情主义,是一场痴情暮色的梦,正是:“梦短梦长俱是梦,年来年去是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