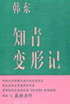 |
编号:C28·2100929·0789 |
| 作者:韩东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28.00元 | |
| 页数:230页 |
腰封和封底很变态,夸耀的头衔和密密麻麻各类人的评价,显得杂乱和轻佻,我忽然发现韩东早就在变形了,从诗人开始,从小说作者结束,他的“口语诗歌”主张颠覆“朦胧诗”的精英化写作,1998年,他与朱文发起“断裂:一份问卷”的调查,言辞激烈地与现存的文学秩序宣告决裂:“如果我们的小说是小说,他们的就不是;如果他们的是小说,则我们的就不是”。在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其实那时的激情和反叛恰恰暴露了韩东的迷失,我之前不喜欢他的诗歌,后来我也不喜欢他的小说。但是他想他一定在不停地寻找突围的方向,在不断的进行蜕变,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生活中真正的荒谬和真实,触摸,并且有痛感。《知青变形记》第一句:“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拉车的牛只有一头,有二十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就是六十多。”
罗晓飞其实早就死了,和那只”闺女“耕牛一样,只是一个符号的消亡,“死了八年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尽管他还活着,还在罗晓飞的墓前鞠躬,还在用阿Q胜利法安慰他,而在这之前,他一直想把自己恢复到罗晓飞的知青身份,一直想回到南京,回到记忆之中的那个城市和那个自己,从物化到人化的渴求如此强烈,当最后回归到范为国的时候,他只能将一切都埋葬,虽然他拥有土地、妻儿和安全,但他还是一个符号,接下来的所有命运只能是一个被制度驱逐的悲剧。
我之前没有看过韩东的小说,有限的只是他的一些诗歌,作为一个对汉语进行反叛的作家,韩东的文字里有着和精英写作背道而驰的东西,这些东西被称为口语,在群体上是汉语诗歌“第三代”和“他们”,在与知识分子诗歌写作之争中充当着先锋者甚至导师作用,在转型之后,韩东开始写小说,从中短篇到长篇,乐此不疲,但是在小说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那个作为诗人的韩东,审慎、严谨和冷静的韩东,平淡、写实和安全的韩东,不管在语言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韩东没有多少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把一个寓言讲得更像故事,仿佛近在眼前就可以触摸。
我并不想说这是韩东的进步,或者是突破,尤其在《知青变形记》这样一篇长篇小说中,还是有着明显的口语诗的影子,有着日常生活诗意解构的欲望,当变成长篇之后,故事就变得更加荒诞而缺乏必要的逻辑性,甚至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难过,它颠覆了故事应该的结构,颠覆了小说必要的想象,也颠覆了阅读的必要体验,在一个符号和隐喻表达的空间里,你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
其实,故事的内核很简单:来自大城市的中学毕业生罗晓飞一夜之间成了知青。为争取回城,积极表现,他要求饲养生产队唯一的一头耕牛。谁知耕牛因病趴窝,竟将他卷入一个充满谎言和报复的政治旋涡,跌入噩梦般的深渊。然而,命运在极其偶然中出现转机——村里一对农民兄弟争吵打架,致使哥哥误杀了弟弟。村民们为保哥哥脱罪,集体决定让知青罗晓飞来冒顶弟弟的身份。于是瞬间,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罗晓飞变成了范为国,知青变成了原住农民,同时也接收了范为国的一切——包括老婆孩子房子和所有的亲戚与乡亲。
当罗晓飞变成了范为国,一个符号便代替了另一个符号,知青变成了农民,村妇便是女友,乡村便是城市,今天便是明天,生便是死,他人便是自己。而这一切却是那么悄无声息,那么顺理成章,罗晓飞逃避了政治罪责,打死弟弟的范为好逃避了刑事处罚,所有的生活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而唯一改变的是罗晓飞的符号特性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物,我们悲凉地看到的,并非偷生的庆幸,而是那个顶着农民“为国”名字生存的人,事实上在起死回生的那一刻,已经失去了灵魂:
此时村子上的人声渐渐远去,就像随着那个名字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具躯壳,轻飘不已,不由得一阵眩晕。继芳慌忙伸过两只手来,被我一把抓住,我抓得很紧很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这是命运的妥协,一夜之间,难逃的宿命之下,他似乎获得了温暖与安全,也淡漠了生死、身份的纠缠与焦虑,他再也不会问“我是谁?”身份的转移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物物的交换,“她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呀?”“我不也是失去了一个女人,又得到了一个女人?邵娜不是也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 生活变成简单的算式,所有的荣辱与尊严,所有的欲望和人性,都在这荒诞的一夜泯灭了。抛却故事的内在混乱逻辑不讲,这种无物交换的荒诞感其实在复制着卡夫卡《变形记》里传达的那种西方式的想象。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就是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泯灭了幻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虚幻与现实难解难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了。
和《变形记》不同的是,卡夫卡试图传递的是超越时空的限制,对事件的交代极其模糊,不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深邃的寓意体现人类的某种常常被遗忘的存在状态。而在韩东的小说中,这样的寓意是明显带着时代特征,是特殊时代下特殊制度的产物,身为南京的曹寇说:
在罗晓飞的命运轨迹里,不难发现,他完成了以下几次“变形”:由城里人变为农村人(下放制度),学生变为农民(知青制度),男人变为女人(工分制度),无辜者变成奸牛犯(司法制度),罗晓飞变成范为国(宗法制度),被迫的范为国变为虔诚的范为国(道德制度)。变化的最终结果是,二者融为一体,归位于一个“人”而已。
但其实,罗晓飞变成范为国,逃脱政治罪责和制度扼杀,成为一个牺牲品本身就是带着对那个时代制度的全面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是不彻底的,甚至是一种悖论。当邵娜来信,希望他回城的时候,那种物物交换后的生活泛出了“死水微澜”,回城、争取知青证明,这一切虽然看起来是挣脱物化,回到人化生活的一次努力,但其实在本质上还是希望把自己纳入到另一个制度中,只是当纳入制度的所有渴求仍然是以牺牲那个稳固的农村生活为代价,他还是最后选择了妥协,并且很坚决的和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符号告别:他来到“知青罗晓飞之墓”,对着坟包三鞠躬,说:“听好了,罗晓飞,你已经死了八年了,也应该安息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也没有你这号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或长或短,都是一样的,都得死,死了以后就再也不分彼此了。”
卡夫卡《变形记》里,成为异类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在变形后被世界遗弃,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他的等待只有死亡,从这种等待死亡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也看到了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世界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才是它的真实状态,而在韩东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批判,我们所看到的是灵魂在制度下不会复活的生存,在反抗制度无果的情况最后只能屈从于制度,妥协于制度,是一只苟活着的甲虫,连死亡的勇气也没有,看起来是超越生死,其实是一次沉沦。
封底的乱弹评论和腰封的荣誉罗列,使这部小说看起来有些浮躁,我只相信韩东是个优秀的诗人,《知青变形记》故意把时代属性凸现出来,无非是想把罪责全部归于历史,归于制度,而弱化了人性中的那种逃避和妥协,韩东无法超越的正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这种宿命,而这也正是他本质上作为一个诗人的宿命。“我1961年出生于南京,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都住过。”对于知青生活,韩东不是亲历者,只是知情者,所以在这部“只是其中一个人的一次努力”的小说中,韩东希望通过一个诗人的想象还原那一段历史,“真实历史总是比单纯想象更加精彩纷呈、复杂吊诡、充满意韵,这就给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趁这一茬人还没死,尚有体力和雄心,将经验记忆与想象结合;趁关于知青的概念想象尚在形成和被塑造之中,尽其所能乃是应尽的义务。”“连接历史与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的构想使整部小说大面积的细节只能源于韩东的少年经验,在情节推演和叙事动力上,则全部依附他的诗人想象。我们或许能够在这首早期诗歌中找到韩东在小说中的影子:
在桥上
你将我领到一座桥上
我们看见架在同一条河流上的另一座桥
当我们沿着河岸来到它的上面
看见我们刚才俯身其上的拱桥
和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完全不同
有两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身影
伏在栏杆上,一个在看粼粼的水波
一个在闷热中点燃了一支烟
与我们神秘地交换位置
当你俯身于河水的镜子
我划着火柴,作为回答
我们是陌生人的补语
亲密者的多义词
只有河上的两座桥在构造上
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