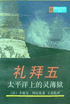|
编号:C38·2120822·0910 |
| 作者:【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06月 | |
| 定价:28.00元 亚马逊18.20元 | |
| ISBN:9787020091393 | |
| 页数:264页 |
“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重复规律,星期、四季、节日、年份。一种幸福的生活应该懂得如何在这些重复的模子中度过而不感觉到闭塞。”否定重复是不是走向了幸福,而对于重复的否定是不是也在否定时间否定规律否定日常生活?“新寓言派”作家的代表,米歇尔·图尼埃一定在寻找非日常生活的表达,寻找现实之外的寓言。而在《爱情半夜餐》中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童话,或者以第一人称讲述生活中残忍而肮脏的片段,二十个故事以薄伽丘《十日谈》的方式展开,每个人都必须讲一个故事,到天亮时由丈夫向朋友们宣布两人分手的消息……于是,故事不断开始了,像永无止境的时间,又走回到起点。收录有《沉默的恋人》、《诸圣瞻礼节的蘑菇》、《德欧巴特之死》、《蒙特的纪念日》、《布莱丁和她的父亲》、《非洲奇遇》、《露西和她的影子》、《站着写作》、《公路幽灵》、《危险的怜悯之心》等作品。完成了一次“私人化写作”。
《爱情半夜餐》:如何返回饥饿的阴道
因为我找到的不只是一名厨师,而是两名。
——《两场盛宴与纪念》
一个厨师和另一个厨师,一个露西和另一个露西,以及一种现实和一面镜子,是镜像,是映射,是对应,还是模仿?“露西刚刚在露西坟墓的脚边埋葬了露西最心爱的玩偶。”在一个绕口令般的故事里,住在房子里的词语纷纷出来,像小动物走出饥饿的阴道,在一个像是愚蠢像是幸福的爱情道路上,寻找另一半的阴影,“当缺乏爱情的滋润时,饥饿的阴道便会离开它的洞穴,就像饿狼走出森林一样。”中世纪的“阴道理论”隐含着一个男人和女人欲望和爱情的寓言,只是,当这一切以哲学的名义变成一种光、影和颜色之间的讨论时,最后的问题只会简单到这样的命题:到底是女人战胜了男人?还是在爱情的虚拟中变成另一个自己?
如果按照那部沙米索的小说的主题来看,彼得·史勒密尔出卖给魔鬼的是自己的影子,以为可以得到一笔财富,但其实是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为了财富失去最重要的灵魂,这是不是一种隐喻?而女人也是男人的阴影,没有阴影庇护的女人,是不是会比彼得·史勒密尔更加悲惨?“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无论男女,无论智商高低,缺少了阴道的阴影,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没有灵魂的可怜鬼。”魔鬼在哪里?在那些没有阴影庇护的爱情里?所以在一对充满着爱情波折的夫妻身上,阴影逐渐被噪声和沉默代替,伊夫·乌达尔和娜黛姬,一个是退役船员,一个是像鳕鱼一样的船主女儿,因为属于同一个秘密世界,才成为夫妻,但是这正是他们最后走向分手和离婚的原因,人际关系最后被某些空虚和厌恶代替,而沉默变成了伊夫·乌达尔对抗社会的一种方式,实际上也在消除着爱情的阴影,和娜黛姬之间也被长时间的等待和冷漠所代替,甚至他们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生活只剩下鼾声和故事的编码,鼾声代替了对话,代替了阴影,所有的一切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没有了任何的激情,“你往桌子上放了一个小录音机,按钮一按。然后听到各种声音,有哨声、咳声、抽风一样的声音、呼声、鼾声。”声音的诗学最后变成了声音的折磨,机械而毫无意义。所以他们最后选择分手,“一顿半夜餐,就如西班牙语说的那样。”在分手之前,他们邀请朋友“来享用一顿通宵达旦的晚宴”,依次来见证一场爱情的真正结束。
仪式而已,其实“爱情半夜餐”是一个寓言的起点,充满未知的世界,那匹恶狼能从森林里走出来?就像从饥饿的阴道寻找到男人的精液,所谓“正大光明的分手”就是在开始一个《十日谈》的叙述仪式,“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开场了,那间“充满词语的房间”打开了,那里有新鲜的蘑菇,有爆炸的烟花,有香水和绘画,有面包和乞丐,也有一个厨师和另一个厨师,一个露西和另一个露西,以及一种现实和一面镜子,就像男人和女人,就像阴道和精液。他/她的二元关系从这样一个镜子般的关系开始,而维系这种关系的是爱情。图尼埃“站着写作”的姿态就是为了看到更多的标本,更多的词语,更多的夫妻“万灵药”,对于这位“新寓言派”作家来说,发现爱情的纯洁和真实,似乎正是他所要寻找的高度,所以在他的“十日谈”结构的故事序列中,总是在追求那种简单、真实和纯洁的生活,欧内斯特的“蘑菇”情结就是一个返回自由的渴望:“事实上,我试图想象,如果我像他一样留在这片童年的土地,生活又将会怎样呢。”而当最后变成一种想象般的结局时,“塑料袋,里面有一小撮蘑菇,已经开始腐烂。扔进了垃圾桶。”这是宿命,美味的蘑菇变成了垃圾,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所谓的金钱和权力。而蘑菇般的纯洁童年或许就是最高的理想,德欧巴特·博尔特教授身上的也是这样,“可是这样—个男人,却出人意料地拥有—个浑身散发着美和健康,对生活和爱充满欲望的妻子。”,而最后妻子的背叛,就是欲望击败纯真的结局,出轨行为或许是推向悲剧的最后原因;而在《安古斯》里,是那种“骑士爱情”:“首先必须要做到的,他解释道,就是洗去爱情关系中所有世俗物欲的污点。”但是情欲杀死了柯伦贝尔,也让一种悲剧以孽子弑父的形式出现。
爱是蘑菇,是浪漫,是健康和美,而被玷污的却是金钱、欲望、权力,而每一种在爱面前呈现的恶都会以悲剧性的“复仇”为破坏方式,德欧巴特·博尔特教授“美和健康”的妻子出轨,“当我光荣地跨在我的瓦尔基丽身上时,房间的门打开了。”这是一种对爱的亵渎,而最后教授必死的结局看起来是一场爱人和她情人苦心设计的谋杀,但却是一次对自我的复仇,甚至成为一种关于繁衍的悲剧,“我难以治愈的创伤源自泰蕾丝拒绝为我生一个孩子。”这是一种解脱还是陷入更深的自戕之中?孩子,这种家族的繁衍往往暗喻着爱情的美好结晶,所以在图尼埃的笔下,完全成为一种纯洁之爱覆灭的理由。在《安古斯》中,柯伦贝尔和她的未婚夫奥特马追求的是那种浪漫的骑士爱情,“骑士爱情恰恰对繁衍后代的需要采取极为超然的态度。脱离了肉体欲望,没有后代的束缚,才能得到纯粹的精神之爱,才是最纯洁的爱,就如同冬天覆盖在本尼维斯顶峰那清澈的蓝天或洁白的云朵。”而这种纯爱最后完全被暴力所取代,帝费纳强奸了柯伦贝尔,在致柯伦贝尔怀孕之后死去,而出生的孩子背负着罪孽,在农家成长,对于失去女儿的安古斯来说,他的复仇计划就是用罪孽的后代来偿还:“要么让帝费纳犯下第三个罪行: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要么反过来,让孩子战胜这个威武的巨人。”儿子杀死父亲,或者父亲杀死儿子,这个被称为“上帝面前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的选择其实就是一种赎罪,这个有点像中国“赵氏孤儿”的寓言其实在用亲情来扼杀亲情,无人性的背后是无法理,无人伦。在《蒙特的纪念日》里也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受伤“总在八月十一日”的吉勒,在写给阿德里安娜的信里写到:“等我长大,我要杀了你”。烟花灿烂的深处是一种爆炸的震撼,复仇是为了“纪念”,安吉·科赫维和吉勒·热尔布瓦被炸死在那个现场,而一切的纪念也都以死亡的形式作为终结。
人伦意义上的复仇,更具悲剧性,而这似乎是图尼埃在建构的一种真正振聋发聩的悲剧意识,而目的无非是建立一个充满纯洁、简单和真实的爱的世界,《危险的怜悯之心》中医生要放弃一切,却是为了将一个病人“娶回家,终日陪伴左右,一分钟都不离开。”这是一种无边的爱还是可笑的闹剧?《皮埃罗或夜之秘密》中白昼和黑夜无法走到一起的男女其实是被“化学的人工色彩迷惑”,遮蔽了真实的味道和感情;《东方三博士之法斯特王》中,帕加马国王儿子死了,父爱使他追随那颗象征儿子的彗星,“我在朝廷中供养了那么多占星家、手相家、巫师和相骨师,他们却再一次集体证实了他们的无知。”那些宫廷无知的人,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权力,但是却不能获得真正的爱,而国王的追随也无非是一种仪式和象征,到最后依然是一无所有,只能感慨:“正因如此我追随这颗神奇的星星,希望看到我儿子的灵魂。我请教您,主啊:真理在哪里?”
真理在哪里?爱在哪里?这或许也是图尼埃的疑问,而在小说里,男/女、父/子构成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纯洁、有如童年的爱,相反,却是一种复仇、罪孽和背叛,那么到底如何去寻找那种真爱,那种不会被亵渎的神圣的爱?图尼埃似乎要从现实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寻找那个庇护的阴影,就像男人天生对于女人的爱护,就像神谕一般开始的亚当夏娃之爱,“纯洁的三个标志:植物、森林以及动物。”而一切的纯爱似乎只有返回到最处的地方,从人的诞生开始,洗净污垢,涂抹香水,“每一款重要的香水就是一扇打开着的通往我们从前伊甸园时光的大门”,从此走入一个如伊甸园般的世界。或许这一切太过于完美,而图尼埃对于现实的抗争并不是逃避,而是改造,就像他对于文本的改造一样。从经典的《鲁滨逊漂流记》到《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图尼埃就是在这样一种文本的实践中,建造“充满词语的房间”。
而这个改造可以从《露西和她的影子》的阅读开始,第121页和第126页的同名故事,可以合在一起,像是一面镜子,映照着现实和虚幻,映照着小说的“词语”,而这面镜子从一开始就是被创造的:“故事的女主人公并不叫露西,但是出于谨慎,我给起了这个名字。”露西是另外的露西,露西是“他者”的露西,或者说,露西是一面镜子里的露西,而改造就是从一种“神修导师”的净化开始:“一次对她身上所有污浊不洁的东西的洗涤,最终使她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女人,率直、干练、健康。”所以,露西只是一个被改造出来的符号,“我的露西,我们的露西,她只是一个候补,替身,在她姐姐生病去世同一年出生,独自开始自己人生的旅途。”而这样的改造重新唤回了那份爱,那份纯真,那份被阴影庇护的男女之爱,一边是死去的露西,一边是被改造复活的露西,现实被搁在远处,而从这一面镜子里发现了那些真实的东西,那些纯洁的东西。
露西之于露西,就是一个真正的影子,一面映射的镜子,“只是在墙上安置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从地面一直到天花板。”所以绘画会超越现实,比现实更为美丽,而《两场盛宴与纪念》里两个厨师的竞争中,第二个厨师对于第一个厨师,看起来是模仿,是照搬照抄,但却是架设了一面镜子,一种映射,“第一场盛宴是一起事件,但第二场盛宴则是一次纪念。”从事件到纪念,也就是从现实到仪式,从叙述到寓言,从物质到精神:“你将成为厨房的大祭司,负责传承烹饪和餐饮仪式,给每一餐饭赋予精神上的意义。”
十九个故事讲完,“爱情半夜餐”也完结了,而伊夫·乌达尔和娜黛姬说好的离婚结局呢?没有站起来宣布,当人群散去,当故事最后沉淀,沉默的人生观和被编码的故事彻底成为一个过去式,其实所有一切都在某种爱的终结中被改造了,故事是文学,是一种万灵药,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些“很久很久以前”或者和“我”这个第一人称有关的故事中,发现了那些被忽视的阴影,那些“里面住着圣人,传奇故事为它添光增彩,圣歌在那里回荡”的庇护所,看起来是宗教的属性,但其实是完全自我的救赎:“其实我们缺少的,是一个能让我们住在一起的充满词语的房子。”
离婚在别处,而爱情的真正意义就是做那个镜子里的厨师,那个从事件到纪念,也就是从现实到仪式,从叙述到寓言,从物质到精神的厨师:“你将成为厨房的大祭司,负责传承烹饪和餐饮仪式,给每一餐饭赋予精神上的意义。”一句话,前后呼应,合二为一,故事以“最图尼埃”的方式结束,而腰封上的图尼埃正以一种童话般的微笑注视着我们:“我们能触碰这些不可触碰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肮脏,相反是因为他们的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