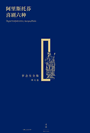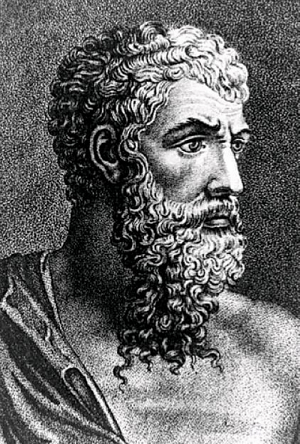|
编号:H79·2200521·1656 |
| 作者:阿里斯托芬 普劳图斯 维吉尔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2月第1版 | |
| 定价:65.00元当当31.80元 | |
| ISBN:9787208155466 | |
| 页数:248页 |
本书集合了杨宪益翻译的三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经典作品:阿里斯托芬的《鸟》、普劳图斯的《凶宅》和维吉尔的《牧歌》三篇作品组成。《鸟》讲述了两个厌恶城邦生活的雅典人带领群鸟建国,使众神挨饿,人类称臣,被誉为“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最机智的作品,同时,这篇作品也具有深刻的现实讽刺,当时雅典人正身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泥潭,此剧即是以“云中鹁鹄国”的绮梦嘲弄西西里远征的无妄。《凶宅》是古罗马最重要的剧作家普劳图斯的代表性计谋喜剧,剧中人物个性突出,节奏紧凑,不断反转,以一方“凶宅”讽尽罗马社会的寄生、享乐与僵化,还原当时的家庭矛盾与爱恨纠葛,是后世家庭剧、计谋戏剧的先声,影响了莎士比亚等众多大家。《牧歌》则是古罗马田园诗的代表、拉丁语文学典范,更是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的扬名之作。田园、领袖、爱情、神意,这些主题在其中都有体现。杨宪益先生最早全译了《牧歌》十首,译本精到畅达、不蔓不枝,完美还原了古典诗歌的繁缛与朴拙。
《鸟·凶宅·牧歌》:你们就以我们为神
塞奥普辟德斯 我说你带坏了我的儿子。
特拉尼奥 那么你听我说吧。我承认他在你不在家期间,喝了点酒,赎买了他的女朋友,借了点钱,又把它花掉了,这我承认,可是他做的这些同别的贵族少爷做的又有什么不同?
——《凶宅》
赎买妓女,喝酒,花光了家产,当少主人菲洛拉切斯在这样一种花天酒地中生活,身为奴隶的特拉尼奥竟然认为这是一种正常举动,是那个时代“贵族少爷”都会干的事情,这是一种对罪责的解脱?还是根本不算是一种过错?而特拉尼奥当时面对的是离家三年而回来的老主人,甚至面对的是老主人的质问,特拉尼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古罗马最重要,也是第一个有完整作品传世的戏剧作家普劳图斯创作的计谋戏剧,取名为《凶宅》似乎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身为奴隶的特拉尼奥在老主人从海上回来之后面对少主人挥霍的现实,设计制造了不让他进门的“凶宅”,他让少主人菲洛拉切斯和醉酒的朋友加利达马提斯关在房子里,然后锁上门,当老主人塞奥普辟德斯不停敲门时,特拉尼奥告诉他,这是一所凶宅,已经有七个月没有住过人了,当塞奥普辟德斯问里面发生了什么事,特拉尼奥便虚构了一起凶杀案,说家主人捉住了一个客人,然后把他杀死了,而这个人就是当初把房子卖给塞奥普辟德斯的人,特拉尼奥为了增加这个虚构故事的恐怖型,还绘声绘色描绘了那个人死后说出的话:“我是狄阿彭提斯,海外来的客人。我住在这里,这所房子是给我住的,因为阴间不许我去,由于我不到该死的年岁就丧了命,我被朋友出卖了:罪恶的房主为了金子害死了我,把我偷偷地埋在这所房子里,不给我坟墓。你现在走开吧,这所房子有罪恶,不利居住。”
这是“用一年时间也说不尽”的怪异事情,正因为此,塞奥普辟德斯喊着“老天爷,救命啊!”逃离了现场。“凶宅”完全是特拉尼奥的虚构,是为了实施自己的计谋,那么,他便是“凶宅”的命名者,既然把正常的房子命名为凶宅,特拉尼奥只能继续编织这个谎言,而在这其中的转换中,也的确可以看出特拉尼奥的智慧。之后出现了一个高利贷者米沙居里德斯,他是来向少主人讨还所欠下的四千四百块钱,塞奥普辟德斯遇到了他,问起了经过,似乎只要米沙居里德斯说出实情,这个谎言就可能被戳穿,于是特拉尼奥继续编织谎言,一方面老主人遇到了卖给他房子的人,却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另一方面米沙居里德斯的出现,又增加了老主人的疑问,但是特拉尼奥见招拆招,“我现在怎么办?除非我把这件事推到隔壁邻居身上,就说少爷买了他的房子。真的,我听过人说,最高明的谎话都是火热的。神指示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他欺骗说少主人因为这里的凶宅,又购买了邻居西摩的房子,而那些欠米沙居里德斯的钱就是买房所用。这个计谋规避了两个风险,既可以让塞奥普辟德斯把欠下的钱还给高利贷者,又不让原先说的谎话被发现。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新买的房子就是隔着一条街的西摩的房子,那么塞奥普辟德斯自然要去看一下新房子,为了不让他发现破绽,特拉尼奥再次想好了计谋,他提前去了西摩那里,告诉西摩老主人要来看看他家的房子,西摩也没觉得不对劲,同意他们来看房子。但是即使这个计谋环环相套,毕竟是谎言,毕竟是虚构,所以总会被发现的时刻,当少主人朋友加利达马提斯的两个奴隶来找主人,这个连环计才得以真相大白,奴隶方尼斯库斯直接告诉塞奥普辟德斯,他们就在里面,而且每天都是大吃大喝,“从来没有两三天间歇过,吃酒玩女人,过希腊方式的生活,有弹琴的,有吹箫的。”塞奥普辟德斯还知道了自己儿子用了三千块钱赎了妓女,当他得知了这一切,气愤地大叫:“他把他父亲给毁了。”而正是这句话,将“凶宅”又变成了另一种隐喻。
老主人买下了房子,又出海做生意,三年时间为了积累财富也是遭遇了奉献,所以回来之后塞奥普辟德斯发出的感慨是:“我很感谢你,海神,让我留着一口气重返家园。从今以后,我要是在水上再迈一步,你愿意怎么处治我都可以。从此以后,去你的吧!我已经相信你足够了。”但是对于他来说,躲过了凶险回家并不是可以享受生活,而是游手好闲的儿子欠下了债。菲洛拉切斯曾经把人生比喻成一所新盖的房子,而新盖房子的功劳当然属于父母,他认为,父母就是孩子的工匠,他给孩子的一生打下了基础,“把孩子带大,费尽心思,叫他长得结结实实,使他成为有用而且体面的人,不吝惜工本。然后加以修饰,教他文学、政法知识,花费钱财劳力,以赢得旁人的羡慕。这样准备好了,就送到军队里当差,并在亲戚当中给他找个靠山。这样他就离开了工匠的手。”但是能对父母的功劳又如此清晰认识的少主人却也像其他贵族少爷一样挥霍一空,“可是等到一个没出息人,一个懒家伙,龌龊而又游手好闲的人,搬进去以后,那房子就倒霉了,好房子给毁了。”
这便是“凶宅”的第二层含义,菲洛拉切斯似乎对这个自己制造的“凶宅”有着理智的认识,但是理智似乎也难以阻止享受的欲望,“懒劲上来了,那就是我的风暴,带着冰雹向我打过来,把我的道德和羞耻的外衣都给打烂了,整个给剥光,从此我也懒得再穿它了。紧跟着来了一阵爱情的骤雨,一直淋到心坎里,把我的心都浸透了。现在,财产、信誉、名声、道德、体面,全完了;我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将好房子给毁了的年轻人也是社会“凶宅”的一部分,他有理智,却懦弱,在欲望的世界里毁掉了一切。从表象的凶宅到人生的凶宅,再到社会的凶宅,普劳图斯就像剧中设计了计谋的特拉尼奥一样,层层递进,揭示了古罗马的社会现实——不仅少主人游手好闲,他手下的奴隶更是诡计多端,就像加利达马提斯的奴隶方尼斯库斯所说:“最坏的是他的一个奴隶,名叫特拉尼奥,那人能把天神的产业都败光。”而这也正是特拉尼奥为什么想方设法要编织谎言的原因,因为他在其中也是一个享用者,在开场时,特拉尼奥就看不上另一个奴隶戈鲁米奥,他认为戈鲁米奥是种庄稼的奴隶,自然低人一等,“呸,你管我的事干什么?我问你,你庄子上没有牛好管吗?我爱吃喝玩乐,找妓女,这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瞎操心。”其实他和少主人一样沉浸在花天酒地中。
面对这样一种“凶宅”式的生活,塞奥普辟德斯自然要成为秩序的维护者,而他针对的也只有这个谎话连篇的奴隶,认为是他带坏了自己的儿子,于是他要惩罚特拉尼奥,“你要被悬起来,用鞭子把你打个稀烂。”即使特拉尼奥表达了惭愧,塞奥普辟德斯也不放过他:“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你的命!”但是在要处罚他,甚至要杀死他的时候,塞奥普辟德斯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有趣的转折,当时的特拉尼奥说了一句:“干什么还迟疑不决呀?好像我明天不会再犯错误似的,下次再犯错误,两件事一起算,不就得了吗?”特拉尼奥的这句话是不是另一个计谋?处罚一次是一次,但是处罚根本没有用,因为少主人不会改变习惯,因为贵族少爷都是如此,也因为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凶宅,所以多犯一次错误结果还是一样,在这样的“计谋”下,特拉尼奥保住了而自己,而塞奥普辟德斯甚至也放弃了处罚权,“好了,走吧,走吧,我不处分你了。”最后面向观众说到:“观众们,戏到此结束,请鼓掌吧。”
面对观众,就是回到了戏剧舞台,回到了一种普劳图斯的虚构中,这个结尾意味深长,或许在普劳图斯看来,一切都无济于事,计谋还是会产生,谎言还是不会终止,整个社会的凶宅也都这样合理地存在着——“计谋戏剧”拉下了帷幕,“凶宅”里的寄生生活还在继续,在喜剧的氛围里却具有了讽刺的效果。如果说古罗马的普劳图斯用不变性来讽刺社会的顽固性,用喜剧来反衬计谋的荒诞性,他展现的是一种现实生活,那么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的《鸟》则完全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来讽刺古希腊的民主政治。《鸟》所设置的时间是现实意义的,“公元前四一四年,这时雅典人民都已厌倦战争,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其中的两个雅典人也是现实中的人,他们是欧厄尔庇得斯和珀斯特泰洛斯,这两个人的身份是“国家公民”,“我们是国家公民,有名有姓,也没人吓唬我们”,不像当时的悲剧诗人阿克斯托尔,他有一个“游牧人”的外号,这个外号也是他生活的写照,因为他没有国家,想方设法要取得公民权。
两个拥有国家公民权的雅典人,两个生活在强大富足国家里的公民,为什么要听从鸟市上卖黑鸟的菲罗克拉提斯的说法,被一只乌鸦和一只喜鹊带去找一个特柔斯?因为特柔斯原本就是鸟市上一只鸟,后来变成了头上有三簇毛的戴胜鸟,而戴胜鸟去的那个地方比雅典更让人能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两个人找到戴胜鸟时,他问他们来自哪里时,两个雅典人就说来自“头等海军国家”,戴胜说他们是雅典的陪审公民,欧厄尔庇得斯否认说自己是另外一种,“是反对陪审义务的公民”。是国家公民却不是陪审公民,而是反对陪审的公民,也就是说,他们反对所谓的雅典民主政治,他们只想要一种享受的生活,“那树上的知了叫个把月就完了,而雅典人是一辈子告状起诉,告个没完;就因为这个我们才走上这条路,路上带着篮子、罐子、长春花,游来游去,找一个逍遥自在的地方好安身立业。”所以他们寻找特柔斯就是在寻找这样一个享乐国度,“我们能痛痛快快地睡个大觉,就像睡在大皮袄里那么舒服。”
是国家公民却放弃自己的权利,而要像戴胜一样过鸟类的生活。当他们寻找到戴胜,一种颠覆人类社会秩序的“伟大计划”便产生了,那就是要建立一个理想国家,“就是说,区域;在这儿天体运行,一切随之转动,称为中枢。你们占据这里,做起城堡,建立国家,你们就可以像蝗虫那样统治人类,而且就像墨洛斯人的饥荒那样毁灭天神。”鸟类建立国家并不是鸟类自己的乌托邦,这个计划的伟大性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统治人类”,在他们看来,人类是可恶的,以鸟类组成的歌队这样唱道:“尘世上的凡人呀,你们庸庸碌碌与草木同朽,好像木雕泥塑,好像浮光掠影,不能飞腾,朝生夕死,辛苦一生,有如梦幻……”另一方面则是要毁灭天神的统治秩序,在他们看来,鸟类才是真正的天神,珀斯特泰洛斯说鸟曾是“万物之王”,他们甚至比宙斯的爸爸还要长一辈,比大地还要老;“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宙斯头上立着一只鹰作为的标志,他女儿带着一只猫头鹰,阿波罗侍候着他带着—只隼。”而对于人类来说,鸟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王更有充足的证据:远在大流士跟墨伽巴左斯两位大王之前,波斯人是由公鸡统治,所以现在公鸡还被称为波斯鸟;鹞鹰曾经是希腊的王;整个埃及和腓尼基从前都是鹁鸪鸟做王,“只要鹁鸪一叫‘布谷’,所有的腓尼基人就都下地割大麦小麦啦。”
所以在希腊人的激情言说中,众多的鸟类同意这个伟大的计划,并且开始建设这个“云中鹁鸪国”,恢复主权,“然后在整个大气和空中一带的四周修起一圈巨大的砖墙来,就像巴比伦一样。”不让神轻易从这里通过,而且要让人类向鸟类献祭,之后才轮到天神:
墙造好了,就跟宙斯要回王权;他要是否认,不情愿,不屈服,就对他进行神圣战争,不许天神从你们国界通行,像从前他们跑来跑去跟阿尔克墨涅、阿洛佩、塞墨勒通奸那样。他们要是再下来,就在他们那东西上盖个戳子,让他们不好奸淫女人。再派一只鸟到人间去通知他们,鸟类现在是王,今后要向鸟类献祭,完了才轮到天神。
鸟的王国便建立起来了,这是有六百尺高的城墙围起来的国家,这是人类必须献祭的天国,这是天神也无法通行的王国:人类的诗人、预言家、历数家、视察员、卖法令的人都被赶走,下面的人类尊这个国家的建造者珀斯特泰洛斯为神:“他们都模仿着鸟的一切行为,并以此为乐;早上一起床大家就跟你们一样,飞到发绿(谐‘法律’)的原野去,然后就钻到草岸(谐‘草案’)里去,然后咀嚼那些菖榛桃李(谐‘章程条例’)。他们的鸟病甚至使他们拿鸟作名字;一个跛脚的做生意的叫作鹧鸪,门尼波斯叫作燕子,俄彭提俄斯叫作不长眼睛的乌鸦,菲罗克勒斯是云雀,特奥革涅斯斤是冠鸭,吕库尔戈斯是紫鹤……”而天神那里,因为这堵高高的墙,天神无法通过,必须要敲盖印戳才能通行,珀斯特泰洛斯说:“现在鸟是人类的神了。人类要向鸟献祭,不敬他妈的宙斯了。”于是绮霓女神、波塞冬海神都只能遵守这个规定,普罗米修斯甚至蒙着脸怕宙斯发现而向他们告密“外国神”因为没有烤肉而向宙斯开战……
鸟类说,“你们就以我们为神。”这是站在鸟类的角度而言,实际上新一代的统治者珀斯特泰洛斯却让这句话重新成为人类的角度。统治着可恶的人类,废除天神的地位,当这个“云中鹁鸪国”建立起来,当然不是无忧无虑的理想国,而是成为另一种权力象征,当波塞冬等三位天神向珀斯特泰洛斯致敬,珀斯特泰洛斯却在抹酱,而他正在吃的肉是“反抗民主党被处死刑的鸟”——当死刑还在,当反抗民主的鸟被处死并成为统治者的食物,一种拥有王权的鸟类王国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折射,而建造者珀斯特泰洛斯成为最大的统治者自然享受着人类和天神的最高待遇:“幸福的飞鸟种族呀,欢迎你们的王回家呀。他来到金殿上比任何明星还要灿烂,比太阳远射的光辉还要光明,他带来了美得无法形容的新娘,掌握着宙斯的有翼的霹雳,香气弥漫上达天庭,美妙的景象呀,微风吹散了缭绕的肉香;他来了;让女神放出圣洁的吉祥的歌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