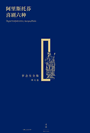 |
编号:X32·2181021·1511 |
| 作者:【古希腊】阿里斯托芬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5月第1版 | |
| 定价:69.00元亚马逊25.80元 | |
| ISBN:9787208134584 | |
| 页数:504页 |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最勇敢的和平战士,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四十年创作生活中,不断为雅典城邦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据说他写过四十四部剧本,其中有四部,是否他的作品,在古代就发生了疑问,他的创作大部分已经散失,到如今只剩下十一部完整的罢了。阿里斯托芬约死于公元前385年,柏拉图曾经替他写过一首墓志铭:“秀丽之神想要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毕竟在阿里斯托芬的灵府里找到了。”本卷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包括:《阿卡奈人》《骑士》《云》《马蜂》《地母节妇女》《蛙》,为《罗念生全集》第五卷。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喜剧也懂得是非黑白
埃斯库罗斯 我对我所处的境地感到愤慨,一想到我必须同一个家伙对吵,我就起反感。但是为了不让他说我无对答,(突然转向欧里庇得斯)你回答我,人们为什么称赞诗人?
——《蛙》
为什么称赞诗人,其实问题应该是:诗人有什么作用?当埃斯库罗斯向欧里庇得斯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对真正的诗人做了一种评价:“人们为什么称赞诗人”完全可以剖解为两部分:一是诗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在问题本身里:他们是被称赞的人,那么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诗人被称赞不是自我标榜,而是由“人们”做出判断,也就是说,人们才是见证者,才是这场“对驳”甚至是整个古希腊文艺学的评判者。
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同样是古希腊的诗人,当他们站在“众神之父”宙斯与塞墨勒的儿子狄俄倪索斯面前进行辩驳的时候,一切都是向“人们”展示诗人的意义。欧里庇得斯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才智过人,能好言规劝,把他们训练成更好的公民。”诗人的目的是训练公民,使他们成为更好,但是埃斯库罗斯却认为,欧里庇得斯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把善良高贵的人训练成了大流氓,他认为,以前的那些“身长四腕尺”的高贵人物反而变成了今天市场上的懒汉、歹徒、无赖和逃避公共义务的懦夫,而埃斯库罗斯认为自己塑造的是“一些发出枪杆、矛头、白鬃盔、铜帽、胫甲气味的英雄,有着七重牛皮的心”
一个是写出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悲剧,《七将攻忒拜》里都是英勇作战的英雄,所以埃斯库罗斯认为,“赞美是一件最崇高的功业,使你们永远想战胜你们的敌人。”这是诗人的作用和意义,俄耳甫斯、穆塞俄斯、赫西耳德以及神圣的荷马都传授了有益的教诲。正是因为埃斯库罗斯崇敬的是英雄主义,所以他认为欧里庇得斯写出的那些诗是被男女私情害了,“你叫那些高贵的妇人、高贵的功名的妻子看了你创造的这些柏勒洛丰忒斯而感到羞愧,服毒自杀。”但是欧里庇得斯认为,自己是写了“真事”,他认为诗人“应当说人说的话才对”,而对于这一点,埃斯库罗斯认为,诗人“应该把这种丑事遮盖起来”,“教训孩子的是老师,教训成人的是诗人,所以我们必须说有益的话。”
这是一场被歌队形容为“狂野的战争”的对驳,而狄俄倪索斯为了评判两个人的观点,又分别让他们让他们各自念出开场诗,又把诗放在秤上称重,最后提出的标准是:“你们两人谁对城邦提出更好的劝告,我就迎接谁。”他征求两人对亚尔西巴德的看法——亚尔西巴德在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出师后,因渎神案被召回受审判,他竟于归途中逃往斯巴达,雅典人后来再次任命他为海军将领。他作战有功,在公元前407年回到雅典,大受炊迎:但当他不在军中时,海军作战失利,雅典人又在公元前406年将他免职。对于如此一个人物,狄俄倪索斯所要考察的是诗人在对城邦安全上的看法,对此,欧里庇得斯说:“我憎恨一个对祖国援助何其迟、伤害何其快、对自私事有办法、对城邦公益束手无策的公民。”而埃斯库罗斯的说法是:“不可把狮崽子养在城里,既然养了一头,就得迁就它的脾气。”
延伸开来,欧里庇得斯的观点是:“当我们认为现在所不信赖的可以信赖,现在所信赖的不可信赖”,也就是说,要起用那些未被弃用的人,“我们就有救了”,而埃斯库罗斯认为:“只要把敌人的土地当成自己的,把自己的土地当做敌人的,把战船当成财富,把财富当成贫穷。”两种观点,一个是巧妙,一个是透彻,一个是用言语驯化,一个是行动实践,一个是实用主义,一个是英雄主义,最后狄俄倪索斯“嘴上立了誓”,挑选了埃斯库罗斯。
两个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辩论观点最后在歌队的演唱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胜利者是展示了智慧和知识,是拥有了美德,是对城邦有益处,而败者是“喋喋不休”的人,放弃了高雅的悲剧意识,没有意义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是“再清楚不过的愚蠢行为”,而埃斯库罗斯最后向地狱之王普路同提出了忠告:“千万记住,别让那坏东西、那撒谎的人、那卑鄙的家伙坐在我的位置上”。无论是歌队的唱曲,还是埃斯库罗斯最后的忠告,都在阐释什么是真正被赞美的诗人,这个诗人与其说是因“人们”称赞而获得的荣誉,“别为了观众而担心,因为他们,可都是哲人。”不如说,这个哲人就是阿里斯托芬本人。
歌队所讽刺的那个“喋喋不休”的人是那个叫“苏格拉底”的人,在《云》这部戏剧中,阿里斯托芬就讽刺了在“思想所”里的诡辩家苏格拉底,斯瑞西阿得斯因为儿子赛车赛马而欠下了债,为了打赢那些官司,他想送儿子去学苏格拉底的诡辩术,“只要你肯给钱,他们会教你辩论,不论有理无理,你都可以把官司打赢。”而坐在吊筐里的苏格拉底把云神称作是女神,“她们是天上的云,是有闲人的至大的神明,我们的聪明才智、诡辩瞎说以及欺诈奸邪全都是由她们赋予的。”而云神的作用就是养着那些假诗人,“你一定不知道她们喂着一些先知、诡辩家、天文学者、江湖医士、蓄着轻飘的长发、戴着碧玉戒指的花花公子和写酒神颂歌的假诗人——这便是云神养着的游惰的人,只因为他们善于歌颂云。”同样,在《阿卡奈人》里,阿里斯托芬笔下就有欧里庇得斯,当主张与斯巴达人议和的农人狄开俄波利斯想向他借一件破烂衣服的时候,刻菲索丰说了一句:“他在家也不在家。”这无疑是绝对欧里庇得斯矛盾用于的讽刺,在《阿尔刻提斯》里就有“她活着也不活着”的说法,对此,刻菲索丰的解释是:“他的心思不在家,到外面采诗去了;他本人在家,高高的跷起两腿儿写他的悲剧呢。”在这种矛盾的说法面前,狄开俄波利斯进行了讽刺:“你写作,大可以脚踏实地,却偏要两脚凌空!难怪你在戏里创造出那么些瘸子!”
喋喋不休的苏格拉底,两脚凌空写作的欧里庇得斯,无疑就是阿里斯托芬认为不能被称赞的诗人,而这些不被称赞的诗人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就只有一种命运:被讽刺。虽然阿里斯托芬写的是喜剧,但是在他看来,一样具有讽喻的效果,就如他在《阿卡奈人》里借用狄开俄波利斯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诸位观众,请你们不要见怪,我这样一个叫化子,不揣冒昧,要当着雅典人在喜剧里谈论政事,要知道喜剧也懂得是非黑白啊。”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当一部喜剧展开,从开场到进场,从第一场到第二场,从插曲到合唱,再到最后的退场,关于是非,关于黑白,其实就是一种戏剧冲突,而这些冲突在就是在最重要的“对驳”里得到了体现。
《阿卡奈人》里本来狄开俄波利斯想要在公民大会上陈述和斯巴达人议和的观点,但是阿菲忒俄斯讲话时竟把他赶走,并以“天有预兆,已经有一颗雨点打在我身上了!”而宣布散会,本来公民大会只有遇到风暴、地震等异象才能停开,而现在“有宙斯的预兆”变成了一滴雨,这无疑是一种笑话,而这个笑话的深层意义便是讽刺,也就是说,主和派狄开俄波利斯被公民大会排挤在外。当时雅典和斯巴达已经打了六年内战,而这场内战其实对于城邦来说,并无什么好处,主战派的克勒翁其实以减轻贡税为条件,接受了盟邦五个塔兰同的贿赂,为此,狄开俄波利斯讽刺说:“嗨,我想起有一样东西我一看见就开心,那就是克勒翁吐出来的五个金元宝!这事情可叫我乐了,为此我真爱那些骑士——‘无愧于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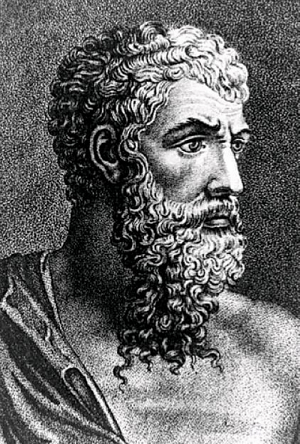 |
|
阿里斯托芬:我的诗没有随我而死 |
所谓主战派“无愧于希腊”无疑不是为了真正的和平,而狄开俄波利斯气愤之下,私自派阿菲忒俄斯去同斯巴达人议和,他议下了三十年海陆和约后,便带着他一家人举行乡村酒神节游行。但是那些被斯巴达人割掉了葡萄藤的阿卡奈人说他是叛徒,用石块击打他,于是狄开俄波利斯好阿卡奈人长老进行了对驳,他认为自己也痛恨斯巴达人,希望海神将他们全部压死,但是他又反问长老们:“我们这样受罪,为什么全怪斯巴达人呢?”那个军官拉马科斯到来,狄开俄波利斯就开始对他进行了讽刺,作为一名军官,拉马科斯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我要同所有的伯罗奔尼撒人永久打下去,我要尽最大的力量用海陆军从各方面去困扰他们!”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拿官俸的人,甚至在现场和狄开俄波利斯对打也败下阵来,这无疑是另一个笑话,那些主战派的人只不过是“拍马屁、献贿赂、行诈骗、耍无赖”的人,而主和的狄开俄波利斯不仅用行动免于战争,而且开放了市场,让伯罗奔尼撒人、墨伽拉人和玻俄提亚人一起交易,最后在酒神节上,大家一起庆祝和平,而狄开俄波利斯更是向观众照杯:“哈哈!胜利啦!”
《阿卡奈人》讽刺的是那些所谓的主战派,而在《骑士》里阿里斯托芬将矛头对准了政治家,意谓“人民”的德谟斯有两个仆人得摩斯忒涅斯和尼喀阿斯,他们诉苦说主人新进买了一个叫做帕佛拉工的奴隶做管家,而实际上,这个善于欺骗主人、压迫同伴的管家就是克勒翁这个所谓主战派的化身,他争取霸权的目的,压迫寡头党的用意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他愚弄人民。所以德谟斯的仆人想办法要教训帕佛拉工,他们用偷来的神示策划将帕佛拉工赶走的计划,那就是用那个卖腊肠的人将他撵走,一个卖腊肠的如何会成为管家?得摩斯忒涅斯告诉他,这是神示里写着的寓言,“你会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什么是大人物,无非是成为一个政治家,而政治家不是正人君子,不是有教养的人,而是无知的、卑鄙的人,而统治人民的做法是:“把一切政事都混在一起,切得细细的,时常要用一些小巧的、烹调得很好的甜言蜜语去哄骗人民,争取他们。”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是粗野的声音、下流的出身和市场的训练,所以,“凡是一个政治家所必需的你都不缺少。”
卖腊肠的小贩具有政治家的一切能力,所以他用“一个俄玻罗斯的香菜叶把议院拉拢过来”,而在面对帕佛拉工的时候,他也展示了对驳的能力,一方面他声称自己爱着主人德谟斯:“如果我不爱你,不敬重你,你可以把我切成碎肉煮来吃;若是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摊桌上把我的肉刮下来,掺一点干酪制成杂烩,再用铁钩钩住这肾囊,把我的尸骨拖到坟场上去。”在表达忠心的同时,指出帕佛拉工的诡计:“他最卑鄙不过,干过许多坏事情,每当你傻张着嘴的时候,他就把查账的‘油水’挤出来喝掉了,他还双手舀过公款呢。”在一步一步的驳斥中,在充分的证据面前,帕佛拉工终于现出了原型,而卖腊肠的小贩终于代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新的管家,而实际上在揭露帕佛拉工丑事的同时,也让主人德谟斯也感到了羞愧,更讽刺了当时所谓的政治家,这一箭三雕的效果完全展示了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天才。
同样,《云》里揭露的是“喋喋不休”的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只不过教人以诡辩,最后非但斯瑞西阿得斯的想法没有得逞,而且自己反而被学习了诡辩术的儿子斐狄庇得斯打了一顿,而理由竟然是:“告诉我,你既然说为我好而打我,我如今也照样为你好而打你又有什么不对呢?怎么啦?我的身体应该挨打受罚,你的身体就不应该吗?我不是生来也是个自由人吗?”《马蜂》讽刺的是那些像蜇人的马蜂一样的陪审员,“他们个个屁股上都有一根非常尖锐的刺,用来螫人;他们一边嚷,一边跳,他们的刺象火花那样发射。”而这些“马蜂”其实是法律上的独裁者,就像菲罗克勒翁所说:“我一开始就能证明我们的权力不在任何王权之下。世上哪里有比陪审员——尽管他已经上了年纪—一更幸运、更有福、更安乐、更使人畏惧的人?”最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菲罗克勒翁只得向布得吕克勒翁求饶:“我愿意同他和解;我承认打过他,向他扔过石头。”然后向控诉人说:“到这里来。是你让我提出我应赔偿的钱,从此和你言归于好呢,还是由你告诉我一个数字?”而在《地母节妇女》中,阿里斯托芬再次把欧里庇得斯请上台,他是一个说女人坏话的人,“我担心这日子会把我毁了。妇女们在谋害我,她们今天要在地母庙开会,判处我死刑。”所以他让自己的亲戚涅西罗科斯扮演女人,试图混淆视听,让自己免罪,但是对驳中涅西罗科斯被人发现,甚至沦落到要被处死的地步,于是,欧里庇得斯最后只要求饶:“诸位女士,只要你们愿意同我讲和,从今以后,你们再也不会听见我讲你们的坏话了。这就是我的建议。”
讽刺主战派,讽刺政治家,讽刺诡辩者,讽刺陪审员,讽刺说女人坏话的人,以及讽刺那些虚伪的诗人,阿里斯托芬在这些喜剧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些喜剧都折射出他对当时政治的评判,“喜剧也懂得是非黑白”,在对驳中可以明晰是非和黑白,而这也正是时代对诗人的呼唤,《蛙》里的埃斯库罗斯其实已经死去,他是从冥府中回到了辩论现场,在某种意义上,阿里斯托芬是在呼唤真正的诗人,如狄俄倪索斯所说:“我想得到作诗的灵感。好的诗人全死了,活着的全是不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舞台上,阿里斯托芬塑造了拥有知识、智慧、美德的人,他们的最大意义是“对城邦有益”,如歌队所唱:
地下的神灵啊,诗人正动身回到阳光里。
请赐他一路顺风,赐他高明的见解
为城邦早就莫大的幸福,今后我们
再不会有巨大的忧患和痛心的刀兵交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