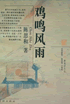|
编号:C28·2030411·0673 |
| 作者:陈思和 主编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00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25.00元 | |
| 页数:2757页 |
“世纪末”对文学来说似乎是一个恒久的主题,在这套冠名为“逼近世纪末”的丛书中,我们对世纪末的理解仅仅为一个世纪的九十年代,难道九十年代就一定带有世纪末的征候?显然,陈思和的目的不是把世纪末仅仅限制在时间概念中,他希望在这些文本中能让读者看到启蒙,看到民间,看到知识分子。卷一为1990-1993年本,卷二为1994年本,卷三为1995年本,卷四为1996年本,卷五为1997年本。
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点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
——王朔《动物凶猛》
时间总是以错乱的方式在记忆中显现:那时应该是1994年,根据王朔的《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杭州路演,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亲见了宁静、夏雨等主创人员,当然姜文并没有现身。这是一部刺激了我感官的电影,对于里面所传递出来的政治隐喻似乎并没有多少被解读出来。这便是1994年微弱的一点记忆,当过去了27多年,当《阳光灿烂的日子》都已经三刷的时候,重新进入电影的原始文本,对于《动物凶猛》却完全是陌生的,甚至连电影本身也在这种对小说的阅读中模糊了——就像王朔在小说中写道的:“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
从真实到虚构,“技术”似乎是一座桥梁,在王朔的文本中,“技术”又指什么?似乎指向了记忆本身,“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尽管故乡是一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是在技术化的处理中,它呈现的是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的功用,而想象式书写无疑具有这样的功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叫“米兰”的姑娘,当我用“万能钥匙”打开了那间少女的闺房,里面的世界完全构成了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的虚构致敬,“丰满,更加红润,发育得像个白种女人”,于是我成了她的弟弟,和她同居一室,保持着亲密无间的纯洁关系;当然在青春期的萌动和懵懂中,除了对“米兰”进行虚构之外,我也对这个世界进行了虚构,“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被摧毁,战争英雄将诞生;破坏欲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青春之歌》、《苦菜花》之中涉及性爱描写的张页被翻得格外旧。
米兰、闺房、世界大战、战争英雄,以及发白的性爱描写,这是青春期荷尔蒙下的书写,但是这一切都在记忆这一“技术”的世界里完成,所以当走出那扇门,无法还原真实便成为“动物凶猛”式的自囚,“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小说《动物凶猛》,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都被关在那里欣赏时才是安全的,而当在27年之后再次返回“技术”的虚构世界,错乱的时间里已经安放不下很多东西,甚至曾经有些狂热地拥抱的“世纪末”也变成了一个苍白的词汇——跨过了如杨克所形容“短暂的进入/那美妙的一瞬啊”的世纪之交,进入了全新的21世纪,甚至一〇年代都拉上了帷幕,在疫情肆虐而看不到希望的2021年,回到世纪末并“逼近世纪末”,是不是连记忆本身都无法还原真实?
五大本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是从某个被灰尘覆盖的角落里重新找出来的,它们平整,它们静止,它们沉默,它们早就消解了那仿佛即刻发生却又手足无措的“逼近感”,是不是如主编陈思和在第一册“序言”中所说的那种状态:“一旦时代跨越了这道门,极大值又会回复到极小值”?但是很显然,1995年在黑水斋写下序言的时候,陈思和是和当时很多作家那样处在“逼近”的位置上,一个问题是:为什么90年代会有“世纪末”的情绪以及情怀?所谓的逼近是不是只是对于时间的一种人为虚构?以及那道世纪末的门是不是也如王朔所说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设置?显然,那篇序言是陈思和对于中国小说未来可期的某种预言,他认为,长期以来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只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成了时间上相交替的符号,成为当代文学教科书编写的捷径。”所以他自设的问题是:“世纪末中国小说的多种可能性是否存在?”
这个问题也是他编选这套小说选集的原因,他乐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世纪末小说具有的多元性特点打破了现代小说自身的城市化,使得小说的生命力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无数次魔方式的演变中经受住了考验”,即使小说未来的前景变得有些暧昧,文学的可能性依然成为了文学与人生关系的一种象征,小说集存在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小说本身的作用”。无疑,他认为世纪末小说的可能性带来的多元性意义是小说以及文学立足于自身发展而做出合理的评估。但是他赋予了世纪末小说在时间意义上新的可能,“世纪回眸的悲怆和当下况景的沮丧所构成的尖锐冲突把人的精神无情地逼向一座绝壁,随之而起的是轰然爆发如焰火绽开,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精神现象”,或者绝望颓败,或者脱胎换骨,或者百无聊赖,或者发现生存智慧,最终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依然一往无前地探寻新的安身立命原则”。这种寻找在“大文化前提”的层面来说,表现的是“极端个人化的多元并存”,是对文学研究者沾沾自喜的思潮、流派、风格之类概念的解构,所以以“逼近”的方式,世纪末小说创作就是一个“永远存在于过程”的状态,自身永远无法明确界定自己,也没有终极的理论界定,甚至当跨过而来那道门,极大值又会回复到极小值,但所有这一切构成的是“时代总体精神现象”。
世纪末小说打破了程式化,世纪末文学具有迫近感,世纪末文学创作表现个体性和多元性,这就是站在1995年的陈思和面对世纪末的逼近对文学以及小说做出的判断,由此他认为,“对编选历史性或者时下性的某些文本来说,根本的意义似乎在于使自己获得再造一次生命的机会,从而也是对自己曾经消失了的生命的再一次挽留。”这是一个逝去和诞生、去蔽和解蔽的时期,而以“小说选”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关照和审视,无疑也是一种标本化的尝试,所以对于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中“元故事”写法的赞誉,无疑就是一次佐证:在“1994年卷”中,陈思和如此评价:“真正揭开九十年代小说序幕的,我认为是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这篇小说发表于1990年底的《收获》杂志上,在当时一片荒芜的文坛上突然树立起一个新的航标。”
揭开90年代小说序幕的《叔叔的故事》到底具有怎样的航标意义?“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小说开篇就说到,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一部分则来自于传闻和他本人的叙述,另一部分来自“我亲眼目睹”,这两部分都是作为文本而存在的,所以,“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这无疑是一种技术手法,王安忆也做好了无法还原真实的准备,但重点不再这里,选择如此技术化,就在于把这个故事写成了“充满主观色彩的故事”,从而一反以往客观写实的特长,“我选择了一个我不胜任的故事来讲,甚至不顾失败的命运,因为讲故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而除了这个不胜任的故事,我没有其他故事好讲。”这是讲故事的悖论,这是技术书写的“反噬寓言”,而“叔叔”之存在,在真实和虚构中就是一个悖论和反噬的存在,就像叔叔的那句警句:“”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首先由叔叔来“书写”的故事,在描写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小说中,叔叔用一头小驴子的第一人称表达了从个体农民到公社社员成长的过程,第一人称的小驴子具有了充分的自觉性。但是叔叔自身的经历却在悖论和反噬中逐渐被涂抹了:一个右派青年死了,一个关于“流氓的问题解决了”,于是他新生了——当文革结束,叔叔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这种新的生活更像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原先小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叔叔可在小说的世界里满足他心情上的某种需要;如今现实则变成虚拟的世界,为小说的现实提供依据和准备。”离婚以及发现孩子“要杀他”都在他新生之后发生了,于是,“叔叔的故事的结尾是:叔叔再不会快乐了!”而我讲完这个故事,也就意味着再也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从快乐到不快乐,从死亡到新生,是时间的两种行进方式,它们构成了完全逆反的命运,那么,这个关于故事的故事,这个纯粹技术性的处理,是不是在悖论和反噬中反而变得真实?
“叔叔的悲惨遭遇,人性受到的压抑,以至屈辱、丑陋的阴暗心理,都与当时的时代有关,但后来时代变了,他终于苦尽甘来,成了一名知名作家,可是在这个光辉的年代里 ,又出现了腐烂的东西,后来他的儿子出现了,他从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丑陋一点也没有消失掉。”陈思和在小说之后做了这样的点评,从小驴子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到叔叔新生的故事,到我充满主观色彩讲述的故事,故事在技术上形成了嵌套结构,但是嵌套并没有形成相异性,虚构和真实也没有走上隔阂之路,它以返回的方式关照了时代、社会、人性,甚至意识形态上的痛苦历程。这样一种在时代中体会反噬之痛苦的还有陈染的《无处告别》,还有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还有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陈染小说中的黛二作为一个女性,被困于闭经、阴道痉挛、经前期紧张、性感缺乏等女性压力症中,看起来都是和肉体有关的体验,但是这种肉体正是女性“无处告别”的象征,麦三和丈夫墨非“像秋天里金黄的麦浪起伏跌宕”的做爱、缪一与“谁谁的儿子”同居选择,以及黛二的出国、结婚,都是在技术层面上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而问题之症结在于“这一代人”无法自我突围,和母亲争吵时,母亲骂她:“中国的未来要全是你这种人接班那就完蛋了。”而黛二的反唇相讥是:“中国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才有希望。”
观点的争锋,却没有换来实践意义上的胜利或失败,回国式的回归在象征意义上代表着一种茫然,而最后在气功大师前“把自己封闭了许多年的心灵交付出去”无疑是另一种囚禁,身体完全变得赤裸,“这种突然而来的全身心的投降与缴械之感立刻将她吞没……”反噬的悲剧在于告别于“无处告别”之处,“然而却永远无处告别;她知道自己在与世界告别的时候,世界其实才真正诞生。”《老旦是一棵树》中也是一种无处告别的告别,当老旦让儿子大旦娶了环环做他的女人,实际上也只是自己命运的延续,而环环和仇人赵镇的通奸,更是将这种无处告别推向了新的深渊,“大旦一连贴了二十七贴膏药,伤口终于长出了新肉,但被狗咬断的懒筋再也没长在一起。他成了瘸子。”而一棵树的成长需要的是粪堆里的养分,“老旦说你儿子一打开柜子箱子闻到的全是我老旦的气味。”宿命一般,是无法回到完全独立的个体层面的,黛二是女性集体受难者的代名词,老旦是男人权力阉割的代名词。而在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灾民也成为了一个集体名词,甚至在一九四二这个宏大历史中被抹除了,“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想从时代的禁锢中冲出来,想以仪式的方式自我命名,但最后都是“叔叔的故事”,只是完全技术意义上的逃离和消失。但是在另一些文本里,它直接以虚构的方式解构现实本身,孙甘露的《忆秦娥》构筑了“双重虚构”的文本,就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阿斯彭手稿》和索尔·贝娄的《贡萨加诗稿》形成的是平行结构,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是抄袭,但是,“庸人模仿,天才抄袭”,无疑“忆秦娥”之“忆”就是带向一种天才般与成人世界相去甚远的平行世界,旧时代完全成为了背景,“她像正午的沙漠灼热而又荒凉,彻底地袒露在哪儿,遥远而又切近,没有玄学的意味,却又使我执迷于此,正如别的事物,别的人之于其他的个人。”而残雪的《饲养毒蛇的小孩》则以寓言的形式描写了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异相:拥有一张空洞洞的脸,声称自己生来就是捉蛇,能听懂小动物的声响,肚子里的花蛇就是自己养的,最后连父母都忘记了“砂原”这个名字到底来自于何处——这仿佛是真正的告别,告别出生,告别命名,告别人之存在规则。
“无处告别”的告别,是“1990-1993”这一卷所构筑的主题,这是陈思和《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的第一卷,将四年刊载的小说汇集在一卷之中,本身就具有某种“逼近”的整体性,而从1994年开始,选集完全按照“年度小说选”的方式推荐和编目,似乎又回到了以时间命名的结构中,而它所呈现的文本也趋向了单一化。在“1994”卷中,陈思和也对年度创作态势做出了总结,“我们在94年度的选集里有意偏重这一类作品,除个别的(如蒋子丹、叶曙明、王小波等)以外,大多数作家都比较年轻,被称作‘晚生代’或‘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这种时代式的命名就组成了“他们”,“他们的创作力多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不仅没有领教过以往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的制约,也没有感受到知识分子广场的荣耀与辉煌,他们一开始就是以赤裸裸的个体生命来直面人生艺术的双重语境,但他们恰恰没有比那些以过来人身份出现在文化市场充当弄潮儿的作家更虚无更潇洒。”这里就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新”特点,一个是他们已经慢慢离开了意识形态的书写,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创作,另一个则是市场对文化的约束渐渐形成了气候,他们无法更虚无更潇洒地面对,但是这两种特性带来的是启蒙主义和精英文化的逐渐淡化、民间立场的不断强化——但实际上从选本中的小说来看,“他们”更为共同的一个特点是:在文本中抵御着现实的种种劫难。
蒋子丹的小说《桑烟为谁升起》就是关于萧芒“消失”的文本创作,“故事定然关于女人,同时定然关于爱情。”小说中描写萧芒不用婀娜多姿、千娇百媚的字眼,小说让萧芒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喜欢暮春,小说安排了萧芒的职业、爱情和婚姻,设计了她去西藏天葬台,而所有围绕萧芒的情节,目的只有一个:“萧芒最终都离开这里。”离开,便是消失,即使“我”最后希望她看到小说后主动和我联络,“我将一直等待她的消息,直到我自己的面容与岁月同样苍老。我不甘心她的命运永远没有结局。”所谓等待也只是自我预设的一个不断死去的循环——萧芒其实被囚禁在文本里,她的到来和离开是造物主的设计,而作者就是那个造物主,“上帝赐给献身生活的女人一杯蜜糖说,快去享受爱的甘甜,然后给献身理想的女人一杯苦酒说,快去做爱的苦役。”
北村的《最后的艺术家》更像是一个纯粹技术层面的寓言。艺术家叫杜林,和《反杜林论》里的杜林一样,其他的艺术家包括画家柴进、诗人谢安和经纪人王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命名背后是对历史、经典的消解,而“当年风云变幻的樟坂”就是一个所谓艺术家的乌托邦,在他们逃避的命运中,在他们对艺术的“捍卫”中,解放同时就是囚禁,“最后的艺术家”所透露出来的荒诞就是艺术之死的悲剧性时代主题:“我现在知道啥叫后现代了。杜林说,就是他娘的没意思,生不如死。”孩子叫“畜生”,瓶子里放着的是月经带和风干的大便,诗歌的题目叫《0》,而柴进死于那只“创作”了后现代艺术绘画的猪,最后杜林疯了,“杜林的故事到此结束,所以叫他最后的艺术家。”像是一个时代的荒诞挽歌,“最后的艺术家”或者也死于自我的命名。而鲁羊在《九三年的后半夜》中对和“世纪末”这个敏感词一样的“后半夜”做出了解释,“我说过,后半夜是怎样的时刻,后半夜是明日灾祸的发源地,而且我说后半夜本身就是灾祸,我说出了貌似判断的一种感觉,然而癸巳日的灾祸,马车撞崖或者最强烈的毁容幻觉,都发生于阳光充足的白天。”在后半夜的大柴垛顶部,是一个来自虚无、归于虚无的苏轼,作为一个行无定处的老游子,苏轼是和“白痴”联合起来被命名的,而他在后半夜所想要到达的是一个叫“故乡”的地方,但在世纪末根本没有故乡,“故乡”只是一个词,就像“苏轼”一样,完全不具备经典的意义——当最后经典被解构,小说创作也变成了“闭门造车”,而对当下的关注也成为了一种彻底的虚无,“苏轼在涌向未来的人群中已无立足之地,趁着后半夜的夜色,他独自返回大柴垛顶部(没有帮助,他是怎样爬上去的呢),从今以后的灾祸与幸福都成为遥远景象,他和他的寓言底座将焚毁于当下的感觉中,这话我说过么。”
柴进死了,杜林疯了,苏轼在“闭门造车”,这就是书写的“世纪末”病症,而到了年度的“1995”卷,陈思和用了一个明确的词形容当年的小说创作:平淡,在他看来,这种平淡折射出的是“文学的无名状态正在形成”,时代的大镜子所折射出的是“共名”状态,但是在镜子碎成碎片和粉末之后,这种共名变成了无名,对于小说创作的知识分子来说,他还是要直面人生直面时代,他也必须以“无名”之名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和心声。李锐的《无风之树》像是对时代批判的一次返回,关于“矮人坪清理阶级队伍”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出摧毁人性的闹剧,最后一段的六十三“呜哇哇哇哇……啊哇哇哇哇……呀哇哇哇……”便是时代的“无名”和“失声”。而朱文的《食指》以真实存在的诗人“食指”为原型,构筑了一次“秘密的诗歌旅行”,放置在他已经死去的一九八九之后的一九九四年,这场诗歌旅行本身具有的启蒙意义也完全变成了行为艺术,“现在是一九九四年,我仍然活得好好的。天啦,你不知道,对每个人而言,这都能算上是一个最大的奇迹。”邱邱华栋带着揶揄的方式对时代提出了批评,《环境戏剧人》中说:“我只放先锋戏剧,我是一个环境戏剧论者,我将我的戏拉出了舞台,彻底地改变了舞台与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静止关系。从而可以把戏剧放到社会的各种环境去演出。因为每天发生的各种现实事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世界变成了一出戏剧,现实就是一幕环境,而每个人无非是上面的演员,生死都已经被写好了,“在这样可怕的城市里,如同回不到爱达荷一样,我们永远都不能卸妆,并准备再一次登场。”
1994年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的,1995年不卸妆的我们“准备再一次登场”,而1996年到了,在陈思和所说的“艺术的真正诗意来自朴素的叙事和个人的民间立场”中,所谓的诗意在民间立场中是不是更具个体性?郭平在《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中构筑的就是一个1996年的异托邦,《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是一部来自外域的电影,方小虎对李艳说,宣传画没有把字写错吧,“库”字丢了个“衤”旁,而李艳说,是人名,又不是裤子,要什么“衤”旁——去除了衣字旁,就是远离了现实的诗意,小提琴、三幕戏剧以及爱情,能拯救没有“衤”旁的生活?“《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叙事曲》洞穿了方小虎,他以为自己的昂然之物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耷拉下来,但它并不理会他,似小提琴,骄傲地翘着。”翘着和欲望无关,它只是身体的一次行为艺术,或者是行为的一次“身体艺术”,于是许辉的《碑》中的悲剧意识和古典主义,李凡《临时诊所》的寓言结构和先锋语系,都变成了和身体有关的行为艺术,甚至变成了单一的身体叙事。
到了1997年,陈思和以两篇序言总结了这一年的文坛特点,他认为作家的立场变得复杂和多元,语言更具个人化,甚至预言1997年的文体变革将是“第二次实验浪潮的来临”,所以撸起袖子准备在理论上做出准备和呼应。但是,无论是严歌岑的《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对现实问题的批判,还是李洱《鬼子进村》中枋口村史怪事连篇的寓言结构,或者叶兆言在《王金发考》中对历史的考证,都没有呈现出陈思和所说“新的批判力度”,似乎“逼近”的动力在渐渐靠近那个“世纪末”确切的时间点中反而丧失殆尽。甚至,大门还没有打开就已经关闭——从“1997卷”之后,陈思和再没有续编《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当1998、1999或者2000都成为了缺失,当“逼近”以中断的方式终结,“最后的艺术家”之后可能真的没有了艺术家,小说创作、文学书写、文本选编都回到了无处告别的告别——也许《王金发考》也是对于“逼近”命运作出了最后的寓言:“王金发毫不犹豫地革了别人的命,偏偏忘了革自己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