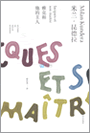 |
编号:C38·2160920·1328 |
| 作者:【捷克】米兰·昆德拉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1月第一版 | |
| 定价:35.00元亚马逊28.50元 | |
| ISBN:9787532767175 | |
| 页数:171页 |
《雅克和他的主人》剧本完成于1971年,先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搬上舞台,被公认为当代戏剧杰作之一。这部剧作改编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小说《宿命论者雅克》。故事从雅克和他的主人的漫游经历开始,主仆二人在途中不但对当时社会的流行话题,从宗教、阶级到男女关系、道德伦理,不断加以反思和辩论,而且以调笑的口吻讲述了各种各样的趣事。这些应接不暇的主题、层出不穷的插曲,以及大量涌现的离题发挥,使整个剧本情节错综复杂,也构成了阅读剧本的最大乐趣。米兰·昆德拉说:“代替作者署名的是我散置于字里行间几许和旧作有关的回忆……整出戏正是要向作家的生涯告别,一个‘娱乐式的告别’。”而这一个娱乐式的告别是“我在一个小小的西方国度里,经历了西方的终结”。戏剧的仪式,是一场盛大的赋别。
《雅克和他的主人》:那么,请给我一个方向
小葛庇 (自豪地)这还用说吗!为了要纪念你,我们给他取名叫雅克!
——《第三幕》
第一个问题是:雅克是谁?他是一个叙述的雅克,站在第一幕的第三场,雅克转身指着楼梯,看到老葛庇站在楼梯底下,而小葛庇和朱丝婷正爬上楼梯,然后叙述一个关于阁楼上的欲望故事:“前天晚上,小葛庇和朱丝婷纵欲过度,结果早上爬不起来。”其实那时雅克在开始讲述小葛庇和朱丝婷的故事之后,就开始把雅克也放在了故事的后半部分,朱丝婷躲到了床底下,小葛庇便在送完车后跑到了雅克的家里,雅克就对他说:“你先去村子里走一走,你父亲就交给我,我会想办法让朱丝婷找机会跑出来。”
雅克是说话的雅克,是帮忙的雅克,是看见故事的雅克,是作为叙述的雅克。而雅克也是被叙述的雅克,因为在妓女家里过夜,然后失去了贞操,然后喝的烂醉,然后被父亲揍了一顿,然后去当了兵,让后在战争中膝盖吃了一颗子弹,然后发生了一连串的艳遇,“钥匙没有那颗子弹,我看我是根本不能坠入情网的。”
叙述的雅克,和被叙述的雅克,我看见的雅克,和看见我的雅克,到底哪一个先出现,哪一件事后发生?是因为在小葛庇和朱丝婷之后阁楼上失去了贞操,然后当兵吃了子弹坠入情网?还是先当兵受伤坠入情网,然后看见了小葛庇和朱丝婷的故事,然后自己上了阁楼,然后失去了贞操?先后秩序是时间里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按照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和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的时间顺序展开叙述,那么雅克还会刺倒圣图旺,然后关进监狱,然后吊死,然后成为一个宿命论者。
叙述和被叙述,以及宿命论者,在那“一个月后”的故事里最终变成了时间的终点?“就在我去当兵一个月以后,你们才知道朱丝婷怀孕了吗?”那时小葛庇在颇有深意的停顿之后说:“ 我父亲就没话说啦。他只好答应让我娶朱丝婷,而九个月以后……”是九个月长过一个月,还是一个月注定了九个月之后的结局?终于在雅克面临进入监狱以及最后吊死之前,小葛庇自豪地告诉他,“为了纪念你,我们给他取名叫雅克!”
纪念一个人,纪念一种岁月,最后是命名——所以当雅克告别了一个月的宿命论者,告别了九个月的叙述和被叙述,他其实才第一次被命名,这是关于时间的最后终点,却是人物出场的最先暗示,而在命名之前,那个叫雅克的人,其实是“上天注定”的宿命论者:“请告诉我,难道我可以不要存在吗?我可以当别人吗?还有,如果说,我已经是我了,我还能不能去做该我做的事情呢?”不被命名的时候,一切都是宿命的,可以是别人,可以不是我,可以不要存在,可以不和朱丝婷在阁楼里发生故事,可以不将圣图旺刺死,可以不被关进监狱,当然也不会最后吊死。但是当一切发生,当雅克就是雅克的时候,这种宿命论的真正意义是:必须有一个主人在。
主人当然是一个命名者,主人骂他蠢,主人不断打断他的话,主人让他讲故事,主人引导他走路,主人是雅克的主人,雅克当然只能在主人面前叫雅克:“如果我想说你是什么叫作雅克的,你就只是个叫作雅克的。”就像他对客栈老板娘说的那样:“我想说你是我朋友的时候,你就是我朋友。”这是“上天注定”的关系,失去贞操、当兵受伤、刺杀圣图旺,关进监狱、最后吊死,都是上天注定的,“我们在人世间所遭遇的一切幸与不幸都是上天注定的。”
但是主人又是谁?谁能为主人命名?雅克在主人面前才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客栈老板娘在主人面前才能成为一个朋友,而所有的故事在主人的听说中才变成吸引人的故事,是不是主人就是上天?就是安排了一切的那个控制者?主人当然经历了故事,当然保持着欲望,当然渴望着爱情,而主人从一开始也是被叙述的那个主人,当圣图旺说“我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主人矢口否认说:“您不是!”而圣图旺的故事里,那个一起交往的女孩却被别人爱上了,虽然女孩爱着圣图旺,但是他依然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那个人是他的朋友。
“请你拥抱我,因为我背叛的那个朋友,就是你。”朋友是主人,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主人变成了故事的主角,女孩阿加特不会同时爱上圣图旺和主人,在这个混杂着欲望和爱情的故事里,正是朋友的相似性模糊了两者的关系,也让主人在一次有限的命名中成为另一个圣图旺。“我了解您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那次是圣图旺说:“我们一起进屋子,一起在小房间里脱衣服,然后您先出去,上阿加特的床。您准备好的时候,给我打个暗号,我就出来跟您会合!”因为是朋友,因为身材差不多,在黑暗中他们就是一个人,但是这样的汇合计划最后却变成了主人一个人的占有,他在阿加特身旁躺下,以双臂环抱着她……
取代圣图旺?还是去除命名?一个故事里主人其实只是一个听众:“我们一起把这瓶酒喝光,然后你说阿加特的事给我听。我们喝酒,你负责说故事,我呢,我就在那儿幻想……”这是主人对圣图旺说的话,可是在这个幻想的故事里,在一个听说的遭遇中,主人却以主人的身份占有了阿加特,当汇合变成一个虚构,在房间里在黑暗处的主人便在圣图旺的叫喊声中被阿加特的父母、被警察局的督察抓住,于是被带进了监狱。
似乎和雅克的故事开始了某种重合,但是即使主人也和雅克一样有一个孩子,但是当主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一个故事想象得到的、最悲惨的结局就是这样了”——主人要还清欠款,主人要送孩子去当学徒,主人要背负照顾的职责,但是主人从来没有获得过命名。这是不是一种隐喻,雅克在一个月的故事里被命名,在主人的身边被命名,但是主人呢?没有命名者,主人永远只是主人,永远没有自己名字的孩子,永远只是在像朋友一样的他人那里获得存在感。
主人是不是最大的宿命论者?“上天注定这回该我讲了。”客栈老板娘在片刻黑暗中讲述了阿尔西侯爵和拉宝梅蕾侯爵夫人的故事的时候,主人似乎已经真正退场了,但是当客栈老板娘成为侯爵夫人又在讲述侯爵的夫人的故事的时候,当侯爵把客栈老板娘叫做侯爵夫人又对她抱怨侯爵夫人的时候,上天注定的故事其实带入了一种重叠、交错和变异的世界里,当主人退场,其实也是主人进场,侯爵爱上侯爵夫人,侯爵爱上做不光彩职业的母女,甚至把那个女儿当成侯爵夫人的时候,一直是雅克在参与这一个话题,他像主人那样打断她的叙述,他像主人一样以客栈老板娘朋友的身份解读这个故事,而最后,雅克甚至也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当那个女儿对侯爵说:“求求您,至少给我一线希望,让我知道您会原谅我!”但其实抱着的是雅克的腿:“只要您高兴,您怎么对我都可以。我什么都愿意接受。”而雅克终于以一个主人的身份对她说:“我也一直把您当作我的妻子啊。请对我诚实、对我忠诚,请您快乐一点吧。也请您让我和您一样诚实、忠诚、快乐。我对您的要求就是这些了。起来吧,我的妻子。侯爵夫人,起来吧!起来,阿尔西夫人!”
所以主人退场雅克出场,其实只是一种叙述的技巧而已,主人其实一直在故事中,一直在“上天注定”的故事里,而最后他在听说这个故事之后,却带出了另一个主人:“雅克,我不喜欢你给这个故事收尾的方法!这女孩没有好到可以变成侯爵夫人啊!她简直就让我想起阿加特!这两个可怕的女人都是骗子!”另一个主人才是真正的叙述者,一个改编了《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的作者,一个把雅克和主人从18世纪带入20世纪的主人。
主人是作者,主人是改编者,“上天老早就注定,有一个人会在人间写我们的故事,而我想问的是,这个人写得好吗?谁知道他是不是多少有点天分哪?”这是主人的不满,作者只是在莫名的冲动中写出蹩脚的诗句,只是在大师面前的一个烂诗人,但是不管如何,主人意味着命名,意味着创造,意味着另外的可能性:“那您觉得,换作另一个主人来创造我们的话,我们就会过得比现在好吗?”但是不管是何种可能,不管是伟大还是蹩脚,总之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中的雅克和主人,小葛庇和朱丝婷,圣图旺和阿加特、侯爵和侯爵夫人,母女、客栈老板娘、老葛庇,一切的人物,一切的故事,一切的叙事,其实都活在作者笔下,都被作者命名,都是在作者的世界里成为宿命论者。
正如雅克所说:“我们应该敬爱创造我们的主人;我们爱他的话,就会更快乐,更安心,也会对自己更有自信。可是您,竟然想要拥有一个更好的创造者。老实说,这简直是在亵渎神明啊,主人。”这是逃避不了的宿命,“创造我们的那个主人,决定让您有权力,而让我有影响力。”但是如果仅仅是宿命论的再现,仅仅是18世纪故事的改写,主人只能是蹩脚的诗人,所以主人的真正意义不是改写,不是命名,而是像自己只有身份没有名字的意义一样,是在创造可能性。主人和雅克退出和进入故事,成为叙事者也成为被叙事者,主人和朋友被混淆而干着不属于自己的事,雅克在一个月的故事里创造了九个月的生命,而侯爵和侯爵夫人、客栈女主人之间的互文和变异,则把背叛的故事引向无限多的可能。
所以从18世纪到20世纪,从宿命论者的故事到创造论者的故事,从不被命名的主人到任意命名的主人,可能只一种,是游戏之一种,游戏之一种,是变奏之一种,变奏之一种是技巧之一种,所以即使当主人和雅克走上舞台的时候,他们在观众期待的命名中也走向了无限可能的游戏场景里,“你们就不能看看别的地方吗?那好,你们要干吗?问我们打哪儿来?(他把手臂伸向后方)我们打那儿来的。什么?还要问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是站在台上的主人和雅克,是被写在18世纪故事里的人物,而“你们”是观众,是读者,当我们遭遇你们,不是命名和被命名的关系,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去往哪里,不知道该骑的马在何处,也不知道“上天”如何注定着接下来的命运,而这种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的命名正是无数命名的可能性存在,正是圣图旺为主人,主人为雅克,雅克为葛庇,小葛庇为朱丝婷,朱丝婷为阿加特,阿加特为客栈老板娘,客栈老板娘为侯爵夫人,侯爵夫人为女儿的一个不断命名的循环。
主人命名一切,也是主人取消一切的命名,“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来交换,我要当你。”所以雅克不是主人的雅克,“因为我那时候的主人,我的主人也就是丹妮丝的主人,把我送给布雷伯爵,布雷伯爵又把我送给他那个当连长的大哥,连长大哥又把我送给他那个在图鲁兹当代理检察长的外甥,后来,检察长又把我送给杜维尔伯爵,然后杜维尔伯爵把我送给贝卢瓦侯爵夫人,她后来跟一个英国人跑了,这事在当时还挺轰动的,不过在她跟人家跑掉以前,还来得及把我推荐给马第连长,没错,主人,就是他,每次都说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那个人。”
瓦解主人,就是把主人带向只有可能的存在,而在20世纪的现实里,这样的命名也意味着取消命名的努力。当一九八六年苏联人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在“你就只是个叫作雅克的”的命运里,苏联似乎成为了命名者,成为了主人,“俄国人的说法和这位军官如出一辙:他们的心理并非出自强暴者虐待式的快感,而是基于另一种原型-受创的爱:为什么这些捷克人(我们如此深爱的这些捷克人)不想跟我们一块儿过活,也不愿意跟我们用同样的方式生活呢?非得用坦克车来教导他们什么是爱,真教人感到遗憾。”主人命名这一个叫雅克的人,命名着必须的秩序,但是主人是蹩脚的烂诗人,甚至他自己也不被命名,所以在何去何从的20世纪的舞台上,主人变成了一个隐喻,“苏维埃这个词让人以为……俄罗斯(真正的俄罗斯)……可以不必对这一切的控诉负责。”
主人必须死去,必须取消,而宿命论者雅克在九个月新生的孩子身上开始了另一种命名:“俄国人于一九六八年占领我的祖国。”终于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关于“俄罗斯黑夜无尽的幽暗”的舞台上出现了另一个雅克,他对着我说:“我亲爱的主人,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要往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