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C38·2160820·1320 |
| 作者:【德】马丁·瓦尔泽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6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0元亚马逊7.90元 | |
| ISBN:9787532155859 | |
| 页数:168页 |
“在发动机的噪声和飞机的影子消失之前,我们拥有花园、房子和女孩们。可我们习惯了拥有一切,我们连复仇都不会。”拥有和失去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两面?作为德国战后最重要的作家,瓦尔泽以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德国社会现实,他通过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人物的自我内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这些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寻找个人幸福以及在事业上的奋斗中,在面对各自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纠葛中,也一直处在拥有和失去的巨大矛盾里。本集收入《屋顶上的一架飞机》《充满危险的居留》《寻觅一妇人》《乔迁》《方法不当》《收藏家的归来》等十四个短篇小说,除《安内玛丽的故事》之外,均创作于1955-1964年间,其中《充满危险的居留》和《藤普罗内的终结》系首次翻译成中文。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我要卖掉这个故事
我真想编一个海尔加和利策和解的故事。为了利策的圣徒称号,我放弃了这个念头。个人的圣徒称号是第一位的,这我承认。可是利策的死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允许人们说:这是一个牺牲者的死。
——《利策的讣告》
一个人,是夏季的整整一天,一天里的精致布娃娃,一天里的煎肉饼,一天里的咖啡口袋,一天里的一场大暴雨,终于像是被设计好的情节,也像是随时准备被破坏的故事,在确定日子里,成为一个宛如交通事故的惨案。具体而微,这个一天其实可以细化成八月的一天,可以更细化为大约五点般的时候,可以细化到那条艾格街,当然最主要的在一天里有人死了,像在一个故事里一样死了。
公园园长福尔伯丁格的女儿被一辆货车撞死了,在这个死亡的一霎那,还混杂着煎肉饼被揉碎时的香味,还夹杂着被扔进芦苇丛时的喘气声,雷雨终于没有下起来,却变成了冰雹,还有闪电和雷声,仿佛一切都在毫无准备,却又有着无法逃避的预兆,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七岁的女孩被撞死,不知道名字,不知道后来应该有的赔偿和处罚,甚至连事故发布会的诸多细节都可以省略掉,但是在这具体而确定的一天,关于女孩被撞死的讣告到底该由谁来写?
这对于利策来说,是一个绝好的题材,出事了,牺牲品,七岁,把这些可怕的事情描述一遍,然后登在报纸上,便像利策曾经的讣告一样,会变成关于死亡的一个故事。可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利策早就不写讣告了,他特别关注的是惨案报道,特别是交通事故,“好像他不但在场,而且还是亲自、故意策划了这场事故。”在利策的笔下,一场交通事故变成了一局以死亡结束的棋,和那些他描写过形形色色的自杀者一样,利策仿佛亲手递给了他们绳子,或者是拧开了煤气开关一样——他在事故的里面,他在事故的现场。
所以,当那篇在报纸上出来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利策要坐下,他一坐下就显得很胖。”开头这一句就把自己包含在文章里,关键是,是利策自己写了关于利策的文章,还是别人看见了一个名叫利策的人,在那里,利策是“他”,是在我面前的一个人,举手投足模仿斗牛士,尼龙衬衣黏糊糊地贴在身上,闪亮的脑袋上顶着几根头发,以及患有糖尿病,如此等等,在文章中是一个他。而其实,在所有被写出来的文章里,无论是讣告还是惨案报道,里面都只能是一个有这名字第三人称的他。
他是被描写的,被叙事的,所以自然变成了故事里的人物,而那个在故事之外的我呢,有一个叫文岑茨的名字,在利策或者海尔加那里,总是被称为“您”或者“你”,看起来,文岑茨是我,是第一人称,是独立在讣告和惨案报道之外的人,也就是和所有的故事和文章无关,先生利策,姐姐海尔加,把这些身份属性又加在他们身上,于是便有了和这一天的许多情节,比如那些利策寄来的精美礼物,是海尔加退给我的,比如海尔加有可能会成为我的秘书,比如在利策有关的生活里,打扰海尔加的女人一定是我,比如爱我和我爱的利策,我会折断一支枯萎的观赏植物作为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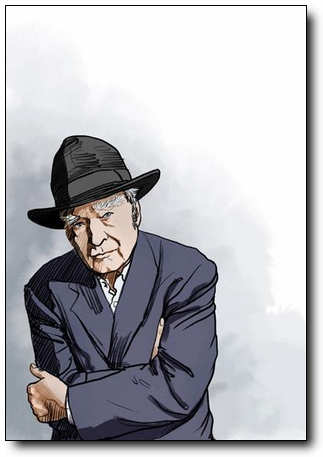 |
| 马丁·瓦尔泽:飞掠的影子拖着我们 |
可是,这是确实的还是虚无的,这是某一年里的一天,还是在虚幻中的一个场景?或者说,利策到底出现在哪里?血腥,牺牲品,七岁,关键词没有能成为一篇讣告,并不是因为利策不再写关于死亡的讣告,不再亲自递给他们绳子,而是他自己完全成了文章里的人物,他走进了属于自己的死亡,“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西装,一件纯紫色的西装,然后,用他那根弯弯的包金晾衣线,就是他总喜欢瞟上两眼的晾衣线,上了吊。”还是在文章里的他,还是亲手递出绳子,还是亲自、故意策划了这场事故,于是他留下了应该给自己的讣告。
自己的死亡,“夏季的这整整的一天,他让自己占用了。”死亡属于他,不是带走了很多东西,是带来了象征物,关于煎肉饼,关于汽车轮胎,关于直升机,关于咖啡口袋,关于晾衣线,关于包金,其实,没一个象征物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死亡,只有在象征物面前,才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的意义,也就是说,利策只不过是导演了另一个人的死亡。就像曾经利策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在世的时候越坏,他的死越让别人舒服。而反过来说,一个人的死越悲哀,就代表他越像一个圣徒,这并非是关于生和死的悖论,实际上是关于亲历者和旁观者的错位,只有站在死亡的对面,只有亲自策划到导演事故,才能真正看见死亡的本质,而利策之死,他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让自己看见了自己,让自己评价了自己。
但是,死亡之后,谁为自己写讣告?转而写惨案报道,似乎是利策对于死亡的更深体会,而利策自己死在故事里,留下我写一篇讣告的时候,我如何找到活在故事里的自己?像一个仪式而已,“而今天,既然利策已经死了,我可以承认,为利策做事时,在某些时刻,我觉得自己像个新教派的丈夫,为了取悦自己信天主教的妻子去做弥撒,却压根儿没学会礼拜仪式,分不清化体和献祭。”甚至死亡本身当脱离了现场的情景之后,也无非变成了一个故事,写讣告变成了描写死亡,而所描写的死亡实际上又让利策背向了死亡本身,甚至成为了一个牺牲者,关于爱情,关于误解,关于权力,关于愤怒,以及关于生命,都在描写的故事里被解构,“奇迹发生了:他的死让所有人满足,他们在安静和平中生活,直至弗拉基米尔回家,雨终于下起来。”
雨终于下起来了,是不是对于这个八月一天五点多的事故的一种呼应?是不是对于利策用晾衣线的包金吊死自己的解构?那雨曾经是被模仿的,就像每一次惨案都是亲自、策划现场的一次模仿,而在被模仿的雷阵雨停下来的时候,那一架直升机飞过,和煎肉饼、汽车轮胎、咖啡口袋、晾衣线和包金一样,成为一个象征物,被模仿的场景里,被象征的关键词,直升机是不是从我们的头顶飞过,直升机是不是变成死亡的预兆?直升机是不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屋顶上的一架飞机》就是在那里响起而飞过的,“这几年来,我们的城市深受其害,飞机轰鸣时,我们碗橱里的餐具日夜都叮当作响,我们的房屋在它们飞掠的影子下呻吟。”确定的城市,确定的故事,确定的日子,但不是确定的死亡,甚至在那个比大街还要吵的花园里,还在举行毕尔嘉十七岁的生日聚会,男人和女人,张开嘴巴,露出牙齿,挥舞胳膊,然后像是狂欢一样庆祝生日。
但是生日是不是可以遗忘死亡的威胁,是不是可以忘记屋顶上的飞机,是不是像模仿的雷阵雨?邀请参加聚会,没有争议的不是疯狂地庆祝,反倒是“将我们处死”,所以那门窗是被关起来的,那铁质的遮阳棚是被放下来的,像是主人死亡或者逃避的现场,可是在这现场里,却也有人从窗户里挥着手,挥着手意味着活着,而活着却像是一个诅咒,一个“肯定差不多有一百岁”的老人是毕尔嘉的舅公,他大声说,毕尔嘉的父母不再相信拯救,而把她卖给了你们,但是当有人招手的时候,我冲了出来,因为我不相信不可能的事情。
谁在招手?跟胳膊相连自由由地飘舞着的手?还是在飞机的轰炸中血肉横飞的手?飞机在头顶,老人在远处,生和死,就在被模仿的现场变成了一个寓言:“一架飞机紧贴我们上方飞过,让我们离开了台阶;它飞掠的影子拖着我们,让我们推开舅公,冲向桌子。”拖着我们的飞机,是把我们带向了另一个现实,其实那里一直有密集飞舞的虫子,有叮当作响的声音,有赤裸的胳膊,以及主人不再的荒废房子,当死亡的影子笼罩着的时候,我们却当成了聚会,当成了狂欢,“可我们习惯了拥有一切,我们连复仇都不会。尽管如此,在我们的上方,舅公还是站在阁楼窗前轻声哭着,一直哭到未来。”
这是关于模仿的现场,这是关于死亡的房子,这是“充满危险的居留”。我为什么要安静卧床?为什么静卧变成了瘫痪?只不过在一种模仿的场景中,看见自己成为故事里荒诞的主角,制冰厂的男人进来,电厂的职员进来,送牛奶的骗子进来,在这间屋子里他们没有看见我,或者说他们有意避开我,而我以瘫痪的方式躺倒床上,只不过是体会一种让别人进来的感觉,“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我静静地躺着也可以成为一种武器”,一种武器,是避免在充满危险的居留里成为被害者,而实际上,不管是制冰厂的男人,还是电厂职员、送奶工人,都是在这模仿的房间里,把死者当成活着的人。两个世界都在寻找一种逃避的方式,但是,“要是我的房间空了怎么办?他们的怨恨将去往何方?即使我逃脱了这种危险,又该如何逃脱这栋房子的其他居住者每天给我带来的危险呢?”
制造危险,其实是为了在场,默默地躺着,默默地制造怨恨的对象,默默地保留危险的环境,如果房间里的东西取之不尽,那么就意味着这种荒诞性就不会终止,但是官方医生却终于来了,他下了一个确定的结论,“您还是承认吧,您已经死了!”本来是一个“伟大的试验”,在被召唤的死亡里,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也就是官方医生把我从故事里拉了出来,给了我命名,危险的居留留在故事里,而我终于要在自己的承认中死去。
荒诞而残酷,屋顶上是飞机,屋子里是死亡,还有谁能真正站在故事之外?还有谁能旁观一个自己?《方法不当》里的我成了玩具厂的看门人,严格执行厂子规定是一种进入故事的做法,但是在队伍越排越长的现实里,有一个被我拒绝而预约的男子最终找到的是人事部长,结果是它代替了我成了门卫,“我一直为自己只做了个看门人感到惭愧。现在我认识到了,做看门人也需要有储蓄所抢劫犯的勇气。这是我仍然徒劳地在我身上寻找的那种勇气。”悖反的逻辑里,自己永远在那长长的队伍里;《寻觅一妇人》里我很想看看前面一个女人的面孔,以确定她是不是我们团体里的成员,但是没有偶然机会,没有擦肩而过,甚至要一一结识所有的女人也完全不可能,当最后放弃的时候,我却在演说中说:“不管是从大街上迷路而来,还是怀有什么样的用心,统统可以参加会议!”因为,“团体一定要保持强大,强大到足以同化外来者的程度!”一个女人,是用团体来同化她,还是在寻觅中被她同化?悖反的逻辑里,自己永远在找不到的结局里。
自己被人代替,自己被人同化,自己没法像利策那样,拥有一个进入故事的机会,就如《假如没有贝尔蒙特,我们会怎样……》里那样,我们只是围着贝尔蒙特,只是睡在大厅里,只是一种特殊的狗种:“贝尔蒙特毕竟是认识这个世界的。他根据这一点办事,他根据这一点对待我们。我们顺从他,服从他,因为:假如没有贝尔蒙特,我们会怎样……”就如《西格弗里德之死》里,送信人成为长长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成为半圆圈里不说话的人,变成无计可施连革命都没有意义的群体,卢齐乌斯·诺德那句“朋友们,我们还有什么愿望呢?”无非把所有人都变成了死去的西格弗里德。
利策之死,西格弗里德之死,其实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那晾衣线是利策一直喜欢的,那八月的一天是被自己占有的,他把自己写进了故事,他成为故事里的自己,所以对自己之外而写的讣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而西格弗里德之死呢,他是被人像影子一样拖出来的,他无法进入房间,无法谈及革命,当然也无法成为有意义的死,而在这屋顶上有飞机的危险居留里,似乎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自己成为被关注的那个人,那就是游戏,躺着而瘫痪,就是一种被制造的病态,能激活愤怒,能成为一种武器,而在《安内玛丽的故事》里,武器是“奥古斯堡烟囱事件”:一位被解雇的员工爬上工厂的烟囱,用铁链和铁锁,将自己锁在最上面的铁梯上,然后把钥匙扔进到了烟囱里,当数千人跑拢来观看的时候,工厂只好动用好几名消防队员,才用电焊机把铁链割断,将那人接了下来。
被解雇就是像影子一样被赶出了房间,所以必须模仿一种游戏,自困的游戏,危险的游戏,然后在数千人的围观中,在消防队员的解救中,结束这一事件。那个站在工厂门口、等着工厂主弗洛恩德博士的赫尔伯特·西恩茨是不是就是那一个制造“奥古斯堡烟囱事件”的人,是不是用危险的武器把自己带进故事中的人?他的兄弟马克斯被解雇了,所以他要找工厂主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本来这事一个正常的交涉事件,甚至是友好的,和善的,为着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但是在这个模仿的故事里,却到处是缺席的自己,十一个礼拜前被解雇的马克斯根本没有把解雇的事告诉妻子,而在工厂门口马克斯的弟弟赫尔伯特见到的以为是工厂主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的兄弟马丁·弗洛恩德博士,而其实就是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也就是说,在这个场景里,“这位为他的兄弟马克斯求情的赫尔伯特·西恩茨将他当成马丁·弗洛恩德博士,要他将他告诉他的一切转告公司老板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而他本人就是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
谁在场?谁是自己?其实这不是最尴尬的,在安内玛丽调查后,才知道,马克斯根本没有一位名叫赫尔伯特的兄弟,他其实把自己叫做兄弟赫尔伯特,然后在老板面前为自己求情,另一方面,老板赫尔穆特也没有一个叫马丁的兄弟,在门口见到的就是最高老板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本人。缺席的自己,缺席的他者,所以这必将是一个缺席的会面,缺席的故事,甚至完全变成了虚构。但是虚构的故事真的就如此发生的?那无非是安内玛丽写的一篇报道,或者是他在咖啡馆里对我讲述的一个故事,安内玛丽和弗洛恩德博士分手,我又爱上了安内玛丽,在和弗洛恩德博士分手之间,安内玛丽和他的席勒式的英雄父亲有关,但是在除夕夜去世之后,这个关系的链条似乎走向了断裂,而我爱上了她,却在我的想象中,变成了所有人的情人。安内玛丽是从弗洛恩德博士那儿听说赫尔伯特·西恩茨的事,然后又写出了《西恩茨兄弟》的报道,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也就是说,只有安内玛丽是这个故事的作者,里面的虚构,里面的错乱,里面的尴尬,都是安内玛丽设计的。
安内玛丽变成了利策,亲自策划和导演了惨案事故,亲自送上了绳子,亲自拧开了煤气开关,但是她会像利策那样,亲自把自己放在那确定的一天里?安内玛丽没有死,她制造的是不在场的尴尬,所以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让作者死去,不是作为我爱着的安内玛丽,而是写作了《西恩茨兄弟》的作者安内玛丽,“因此我要实现我在咖啡馆里讲过的话,好让安内玛丽和我之间亲近起来。我要卖掉这个故事。就像人们想摆脱一个厄运似的。”
卖掉一个故事,和编写一个故事,看起来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只不过在编写的故事里有确定的人,确定的日子,以及确定的死亡,即使不能成为圣徒,只能成为牺牲品,但也在讣告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卖掉一个故事,就是把根本没有马丁这个兄弟,根本没有赫尔伯特这个兄弟,又变成了根本没有作者的结局:“她的名字,我再也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