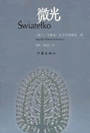 |
编号:S38·2140224·1060 |
| 作者:【波兰】马莱克·瓦夫什凯维奇 著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36.00元亚马逊27.00元 | |
| ISBN:9787506371025 | |
| 页数:308页 |
马莱克·瓦夫什凯维奇(1937— ),波兰诗人、翻译家。曾从事广播电台和报刊记者工作30余年,也曾担任《新词》、《诗歌》等文学刊物以及《女性与生活》周刊的总编。2003年开始担任波兰文学家联合会理事会主席。瓦夫什凯维奇的诗歌创作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他的诗歌创作涉及的题材广泛,既包括爱情、生命、时间等永恒主题,也包括一些与当代社会紧密相关的重大课题。本书是诗人的自选集,从这本诗集中,读者还可以看到作者诗歌语言的演变过程,从早期的跳跃感和打断词语内在联系的不懈尝试,到晚期归于自然平实的语言风格,从而折射出作家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
《微光》:每条河都叫冥河
今天,我已年近七十
望着我年轻的母亲
她比我大
只隔一个死。
——《* * *》
2006年,马莱克·瓦夫什凯维奇说到了“今天”,说到了“年近七十”的自己,从1937年出生的那一刻起,生命似乎就在某种计算中,尤其是迈过四十年花的时候,他瞥见了眼见的母亲,只是在“相片撒谎”的诗歌里,他看见的不是衰老的老妇人,而仅仅是超强超越我只有数月之差的那个“善良和慧黠”的母亲,那么生命是不是变成最后不用计算都可以抵达的终点,成为只隔着一个死的距离?那不是省略号的《* * *》像是无题的沉默,在不断逼近的时间里发出叹息。
用母亲作为一个生命的意象,用“***”作为对死亡的注解,不管是1960年的《在沙粒上作画》,还是1968年的《再远些》,不管是1977年的《鹌鹑的心脏》,还是1984年的《竟会如此》,不管是1990年的《关于爱情》,还是2006年的《生命的极限》,瓦夫什凯维奇总是用这一帧帧诗歌的相片,来构筑那“只隔着一个死”的生命,而凸显出来的“母亲仪式”成为生命的另一个注解:“在某些时刻,当我们已经和希望作别,它却带着年轻的力量重新造访,这是一种期望之外的、我们受之有愧的命运恩赐。”作别不是遗忘,而是重新造访,,是抵御时光流逝的情感,比生命更重要,而且“持续的时间比一秒钟略长一点儿。”在《怀念母亲》的自序里,瓦夫什凯维奇用这样的方式寻找命运的恩赐,寻找年轻的力量,像是微光,预示进入一种光明的隧道。
而这种找寻,这样的微光出现之前,必定有过疼痛,有过分离,有过误解,也有过无奈。在岁月的肖像画面前,即使“抹平你的平滑”,即使“在无梦地入睡之前把纸片放入信封”,即使完好地粘好,那年华还是有过痕迹:“也许明天,我看到你的画像已经改变。(《肖像画》)”,改变是什么?改变是泛黄的钢琴,是泛黄的键盘,是人骨的颜色,是风钻入琴弦之间发出的声音,“琴键焕发生机,尽管能让骨头酥软”只不过是一种李斯特艺术般的想象,而在埃拉·菲兹杰尔德的诗歌意象里,想象必须面对死亡的无奈,因为“世界已不是先前的模样”,“湖泊在入暮时分闪着紫红和金色的光,/虽说白天,青春和爱逐渐变得暗淡/匆忙而又艰难。(《埃拉——献给斯塔舍克·斯霍恩·沃尔斯基》)”就像《诗人穿过田野朝密林的方向狂奔》里,只有“风,腐烂物和十二月的严寒”,即使“汗流浃背的诗人朝密林的方向狂奔”,即使“回忆和不可救药的生存/像德国的牧羊犬跟在他身后追赶”,但依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诗歌像是在风、腐烂物和严寒中渐渐老去。起初是在时光的流逝中对你说“人呀,想想,树叶”,因为它可以再次出发,可以再次拥有,但是在那里,分明看到了发黄的桦树上掉落的一片树叶,是突然掉落,“那时我们明白,/什么是生命的极限。(《生命的极限——致伊雷娜和彼得·昆采维奇夫妇》)”
“河水依旧流淌/我现在出去/自由自在,听不到你身后的哭泣/我寻找它,如此徒劳/那些回声早已死去/(《* * *》)”是的,回声就住在时间里,只是再也寻不着它。这是河水之外的分离,这是告别的挽歌,“我会在旅途中入眠/没有目的地的旅程,没有意义,梦会不同/没有上面的黑暗,风景也会不同/渴望在清晨来临,而我已不在/我将渴望你,不是这个,完全是另一个(《告别的挽歌》)”在饭店的房间里给你读诗,变成了一种永远回不去的意象,所谓挽歌便是听不到你身后的哭泣,那么离开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在墙皮很快掉落的地方,在小玻璃窗破裂的地方,在常春藤凋谢的地方,彻底战败的不只是那座老剧院,那场有关人生的演出,即使相信没有告别,但是人生就像一出戏剧,最大的困惑依然是:“谁是那个沿着地面奔跑的、提词的驼背人(《戏剧》)”离开是一种黑色的疼痛,而在戏剧之外,是另一种和身体有关的疼痛,“十一年前我搞断了腿/打着石膏躺了半年/我的膝关节彻底冻僵/没有任何回暖的迹象(《矫正——致克日什托夫·贡肖洛夫斯基》)”冻僵的身体,其实需要一个回暖的刺激,但是当朋友向我讲述古老的真理,讲述从爱到恨的道路,以及中间经过的车站,讲述“装着铁轨的平缓隧道”,但是这讲述却不是遗忘,而是造成了巨大的空虚,结果是“而我已经不喊了/因为我根本不疼。”那么是从疼痛中走出来了,还是已经完全麻木了?那些人生历经的爱和恨,那些真理和现实,都在矫正我们的冻僵的心情,而不痛的另一个可能是失去希望,所以在《石头上的文字》里,瓦夫什凯维奇似乎更愿意拥有不停止的疼痛,因为那里有“光尘汇成的溪流”,有“金属制成的宁静”,有像石头一样的词语,所以我的要求是“给我的剧痛还能更猛烈些吗”,猛烈的疼痛,是刺激,是思念,是超越自我的存在,是比“那些喂养躯体的,石缝里的荒草”更加永恒和持久,“骨骼来自你们的骨骼,/指甲来自你们的手指,/肝脏来自你们的痛苦,/头发来自头发(《晚餐》)”,因为在挚爱的人中,在至亲里,“我坐到你们中间”。
这一些的生命过程,是和自己有关,和自己的疼痛,和自己的诗歌有关,所以找到亲人,做到你们中间成为一种超脱的方式,而亲人的故事最强烈的是母亲和父亲,是亲情。那个只隔着一个死的母亲其实生命早就消逝,但是却是“年复一年更加年轻”:“她安葬了和她生了六个孩子的丈夫/她教育子女。获得华沙花样滑冰冠军。/她总是能赢首都最大的老千儿。/然后给十六个人做午餐。/她活着。避免用刀敲东西。/她看电视,尽管什么也不懂。/她安葬了两个儿子。咒骂儿媳。/她安葬了第三个儿子。/已经只会数到三了。(《名叫玫瑰的老女人——致母亲》)”她死去,她活着,她“活了这样一辈子后死去——这是秋天的微笑”。母亲的微笑里是对于孩子的培育,是对于生命的尊重,或者愚昧,或者粗暴,但是总是微笑,总是寄托着希望:“她说着什么。我调大了音量旋钮。/“我很幸福。”她说,‘我问候我的女儿万达。’/”幸福是因为“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她赢得了一万米”。这是回报,母亲像一朵玫瑰的开放,绽放出最美丽的颜色。而与玫瑰的母亲一样,父亲则像“山谷”,在《怀念父亲》的诗歌里,时间区分了“真正人的姿势”和“真正非人的姿势”,在“伯爵作家、商人、骗子、农夫、工匠”这一系列关于先人们的标签里,只有父亲还留存着记忆的气息,“哦,我的山谷,/哦,不存在的岛屿,/我看到你,就要回去。/长长的队伍中,又多了一个/这些人无法得到/丝毫拯救。/哦,我的山谷、我的希望——”不存在的岛屿,却存在着一个港湾,在流逝的时间里活着。
玫瑰的母亲,山谷的父亲,是恒久的希望,是不逝的感情,而在爱情世界里,瓦夫什凯维奇似乎看到了含混着欲望和激情的女人,含混着梦幻与错觉的爱,“女人和她无力的手/慢慢在记忆的反光灯里熄灭。/只是仍能听到那抽泣。/而这并非错觉。(《可能是幻觉的一幕》)”说是不是错觉,却又是幻觉,美妙的那一刻,那残缺世界的和谐,那粉红色的光晕,但是“在你强烈的呼吸里,在两嘴之间不断交替的/零散话语里”,爱情是不是一种完美?“我问你:在梦中你是否看到我们在一起/我最亲爱的你?”可是,“作答的不是你,而是你的梦:/嗅,是的。(《描写爱之夜》)”作答的仅仅是梦,最亲爱的你也仅仅是一种想象,那所有的动作也可能是“空洞的手势”:“在错觉的前室里。/在某人陌生之吻的味道里。/在任何人也不能替代我们的信念里。/在令人赤裸的镜子面前。/在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相信的陌生目光面前。/饥饿。空洞的手势。空洞的手势。(《空洞的手势》)”陌生的目光,饥饿,以及空洞的手势,对于爱情的注解,充满着某种感伤,而这种感伤慢慢变成了某种欲望,多次面对赤裸裸的自己,也面对赤裸裸的欲望,“韦恩·马致年轻女诗人埃莉诺·怀利”的信里,韦恩听到的是坠落的衣裙声,看到的是“肩膀、两胯、大腿和两胯之间的私处”的光芒,“我的双目顿时可怕地失明,/我们只能悄悄说出这个小东西的名称。”,可是只是想象,只是听见或者失明地看见,而最后的结局是:“可现在晚安,最珍爱的,我会梦到你/这梦像篝火飘出的烟一样芳香,/篝火里桦树枝和干枯的野草/在欣喜之中慢慢死亡。”另一封信是埃莉诺·怀利致韦恩·马的告别信,“随着我们肉体的交谈将要发生点儿什么,/会比已经发生的更多。”但这是早前的事,现在她说,不要给我写信,也不要来,因为我的合法丈夫是威廉·罗斯·贝内,“在上帝和众多见证人面前举行过婚礼,/唯有他对我的肉体享有权利。”但是在这婚姻面前,在丈夫面前,在这拒绝面前,“请把我忘怀。不,别忘记我。/可能在许多年后我们又匆匆相见/在肉体的脆弱,在阳光或在雪中/积雪将消除一切。罪过和誓言。”希望用积雪消除罪过和誓言,消除肉体的脆弱,对于爱情来说,欲望无非是背叛,却也是虚构,在附笔中说:“埃莉诺,怀利七年后去世,享年四十三岁。实际上威廉·罗斯·贝内是她的第三任丈夫。韦恩·马的命运我们不清楚,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人。”
不存在的一个人,不存在的爱情,或者也不存在罪恶和誓言,不存在婚礼和丈夫,在欲望或者肉体里,爱情会走向怎样一个扭曲的世界?《亨利勋爵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陛下的书信》里,爱情是一个“你谦卑的臣仆和崇拜者,一个被踹开的情人”的倾诉,是“愿你万寿无疆”的祝语。而在《被出卖的女奴——致马雷克·克文图斯的书信》里,爱情是一个女奴的痛苦,是“比较舒心的也许是一柄短剑/插在脖颈或者腹股沟上”的绝望,“我的主人,你为何如此对待我”的呼喊后面是不对等的地位,当然也是不对等的爱情,像是在罪恶的世界里滑行,最后一定是在死亡的故事里留下喟叹:“可怜的、自负的埃斯泰尔。可怜的爱玛,/红褐色的头发,满脸雀斑,两条大腿之间/冒着火焰,可怜的贵族佳丽/农妇,女市民,酒店女老板,厨役丫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就像十八世纪献给阿勒·普的那封《墓碑下的书信》,当欲望熄灭,当爱情颠覆,剩下的只是“我是带着怎样的激情越轨”的自责和“六十年后有人找到了她们的裤衩”的悲悯。
扭曲的爱情充斥着欲望,“让我再一次为爱而死”像是最后的悲歌,所以在瓦夫什凯维奇构筑的感情世界里,一方面是“坐到你们中间”的渴望,一方面却是错觉和幻想,而它们最终几乎都趋向于一个死亡的终点,所以再次回到死亡中,回到生命的最后极限里,那些死亡是现实的无奈,“我以前就知道,这一切都在逝去。/但我从不相信,竟会如此。(《竟会如此》)”是爱情的破碎:“我们死了。很遗憾。你看,我们的爱情/就这样破碎——它曾像鹌鹑的心脏一样硕大无朋。(《鹌鹑的心脏》)”有无声的时间:“我的那些逝者,正慢慢木化/躺在空旷的田野里,越来越挤/绿色错过田野/直接从夜晚到深夜/只有云朵偶尔将他们照亮/冬天的记忆(《我的那些逝者》)”连山谷的父亲也沉默不语:“肮脏、可怕的死亡。我是个逃兵,/所以他在午后的睡梦中没来找我/他死了,仿佛沉入了平坦的墙。/今天我对父亲说,而他第一次/闷不做声。(《夏天》)”身体里的父亲变成了静止的东西,“是因为有那么多东西在它内心重复,是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绕行”,内心重复和无法绕行,对于死亡来说,绝非是一种浪漫,而是逼仄的无法逃避的现实,是的,那世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空房间,而每一个空房间都带有可以眺望到那墓地的窗户,而对于《给六十岁开外的男人十点建议》里,希望去坟场散步渐渐习惯的是“看看如今什么人在平静安眠”,这是一部电影短片,最后一定会拉上黑色的帷幕,关上那房间里的窗户,“软得像混凝土/轻得像石头”。
“只隔一个死”的生命是不是需要冷到只剩下混凝土和石头,只剩下骨头的声音?玫瑰样的母亲在那人生的过程中是放着一些注解,而“她活着。战争持续。/她活着。战争结束。/她从托皮尔街跑到普鲁士科瓦街”已经不但是一个老妇人的人生轨迹,在这个被书写成历史的国度里,还有那叫做战争的故事,是的,在萨拉热窝也有死亡,那个叫弗·斐迪南的奥地利皇储被刺杀,“大公被炸死。他同样可能因患流感/而死。或许照样会开战。/这跟我有何相干?/毕竟此事发生在很早以前。”被炸死,或者病死,但是历史是改变不了的,“风是合乎逻辑的,而死亡就是逻辑”,那么,那个叫加·普林西普的凶手,和“杀死我们的凶手”到底有何区别呢?历史冰冷,知名人士被抛进时代的角落,而所有的普通人也一样会有这样的命运,在死亡面前,不论是和年华里的自己,还是刺杀中的大历史,都指向死亡的逻辑,都是一种流逝:“打自那时以来/风吹裂了岩石/制度垮了台,/水使礁石化为齑粉/我已不再提及肥臀。(《流逝》)”即使在宗教中,“每个人都像城市基督/即便死去,也不能把任何人救赎/”当一年四季汇成一个季节,在死亡中发现了自己的死亡,也在别人的恐惧中发现了自己的恐惧。
“这一切反正都一样。没有救。/每条河都叫冥河。”可是毕竟在死亡之前还有记忆,还有《由记忆来的图画》,河流的水声里有我们听见的东西,在光阴的世界里有我们看见的”微光“:“这是什么?这是小小的、朦胧的、微弱的/一点儿亮光,它正要沉没到/臆想的地平线下面?/摇曳不定而若隐若现?微茫而又可怜?”而那个发出微光的正是一个叫做诗人的人,当“死亡比任何时候更快来临”,当“不把爱情称作爱情”,当作品以此次出售还“卖个不停”,当他找到异性销魂还喝烧酒,所有这一切的绝望、疼痛、世俗和欲望,只不过是诗人在寻找“和世界相逢”的方式,卑微或者粗俗,解构或者抛弃,只不过是“表达微妙的忐忑不安”,是的,诗人说,“不要让任何人为了自己挽救我们”,而“含蓄的诗人天天这么干,/为的是让任何人,他妈的!都不会想到/他的含蓄特点。(《微妙性》)”
“我们死了很久。疼痛已经到达岸边。”那么让我们从那条叫“冥河”的河流上站起来,不要任何的计算,在年近七十的生命里从隔着的那个死之前走过,以“微光”的名义找到“期望之外的、我们受之有愧的命运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