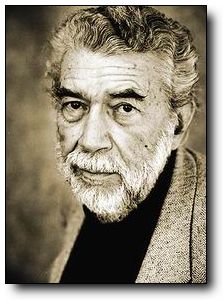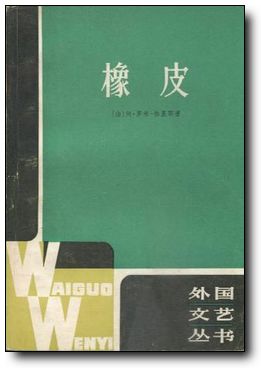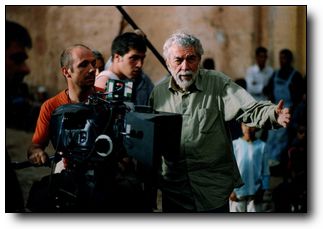2011-09-21 罗伯·格里耶:走向主观的现实主义(存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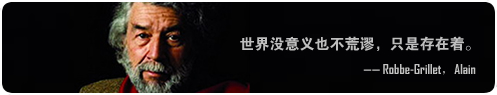
完全是一次偶然,他的文字,他的电影,他的理论,甚至他的逝世,罗伯·格里耶,这个法国“新小说”的标志人物,他的名字在我陌生的阅读世界里响起,我便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伤感。《都市周报》的最近一期《文艺手册》里有一篇文章是关于罗伯·格里耶的,这是一个曾经的时代,这是一个熟识的名字,他的《橡皮》、《嫉妒》,他的《去年在马里安巴》,他的新小说打开了世界和我们的窗口,但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早已逝世,那是2008年2月18日,这个日子距离现在已经三年半了,但是我一无所知,我以为他还活着,活在文本中,活在小说中。
想起在他逝世之前,写过一篇很功利的评论文章,是某种考试的论文,关于罗伯·格里耶,关于新小说,也关于世界和我们的关系。其实,我没有仔细认真阅读过所有罗伯-格里耶的重要作品,只是片鳞半爪地接触过他的文字,所以这篇论文只是一种纪念的存在而已,令我想起那个属于“橡皮”的变革时代。
摘要:罗伯·格里耶是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人物合实践主将,他的创作实践变革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历史性理论,从虚构和想象的世界中寻找新的叙事,在全新世界观、价值观和写作观的创作中将小说从客观现实主义带向主观现实主义。他还原了小说的独立地位,还原了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将人物的想象和虚构作为一种现实,并通过创造性的真实来阐述他的世界,具有文本变革的极大勇气。为战后现代主义、左岸派电影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罗伯·格里耶 主观现实主义 新小说
一、罗伯·格里耶的小说:被误读的文本
Robbe-Grillet,Alain(1922-2008) 罗伯·格里耶可以说是二战之后对小说形式进行革新实验的最敏锐的作家,他使小说真正成为了一门艺术、一门永远处在现在时的艺术。在他的文本中,传统的人物、细节等叙事手段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重复和悬念、跳跃和神秘,他在构建小说的多层多维的时空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他的创作在对于传统小说的颠覆中完成了对于未来小说的探求。但是从他的创作的小说中可以看出,正是他小说文本中不断出现的非客观描述,评论界曾把他踢出现实主义作家行列,这种排斥使他的文本一直处在误读中,他的时空交错、心理活动和没有线索的情节被认为是一种经典的现代派小说,特别是那种重复和想象式的虚构具备了现代主义反现实的基础。他们认为,罗伯·格利耶以及新小说作品“反对小说中有人物、情节和性格塑造”,同时“反对介入生活和现实主义”。[1]正因为他的小说解构了现实主义赖以生存的情节、人物、环境,解构了典型性和历史感,所以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反现实主义的。特别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来说,新小说凸出的形式主义特点被先锋派奉为现代主义学习的圭皋,加以模仿。
这些误解不仅是对罗伯·格里耶文本的误解,更是对法国新小说的误解。罗伯·格里耶从他创作第一部小说开始 ,就走上了独树一帜的主观现实主义道路,他革新了19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甚至对经典现实主义的所有特点进行了实践性的颠覆,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罗伯·格里耶用他的主观想象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大厦,他把人物的想象作为一种新的现实基础从而创造现实,改变传统的现实观,想象中的真实成为罗伯·格里耶心目中的现实,从而完全摆脱了人被物化的困境,赋予人和物一种新的关系。二、 罗伯·格里耶的主观现实主义
要分析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特性,就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传统现实主义?什么又是主观现实主义?
1、现实主义概述
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这个术语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种是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的观念,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另一种是狭义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历史地看,现实主义发端于与浪漫主义的论争,最终在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逐渐丧失了主流话语的位置。
现实主义经过泰纳、恩格斯、别林斯基直至20世纪卢卡契等理论家的发展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文学实践达到高潮。现实主义理论日趋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成规。它包括以下层面的涵义:
第一,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术语的最根本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的是文学对现实的忠诚和责任。早期现实主义作家企望真实地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作为浪漫主义的论辩敌手,作为社会边缘贫困小人物的代言,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披露真实,戳穿伪饰现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抵制作为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话语形态的浪漫主义,转而追求客观性,为那些堕入贫困被边缘化的弱势族群或阶层发声,显然具有素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
第二,广为人知的典型理论。典型论构成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项核心内容,概括而言,典型论欲求解决的即是文学人物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把这种个性和共性的完美结合的文学形象称为典型形象。据韦勒克的历史追溯,典型术语的最初使用者是谢林,意指一种像神话一样具有巨大普遍性的人物。浪漫派首先广泛使用这个概念,之后,典型概念从浪漫主义转移到现实主义,泰纳则频繁使用此术语讨论社会阶层人物的性格,逐渐演变成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概念。
第三,历史性的要求。在韦勒克看来,历史性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比较可行的一个准则,他认为,现实主义有历史性的维度。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也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简单地说,现实主义的历史性维度即是要求真实摹写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且反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现实主义的历史性要求,实质上是以社会分析为核心,即以摹写人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本身的结构为艺术原则。而且现实主义竭力通过人的现实矛盾去揭示人与社会的辩证法则,现实主义确认:对社会现实观察得越仔细研究得越深入,对事件及细节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获得真实的力量。
2、被变革和创新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话语占据主流位置,并逐渐衍变为一种文学不可僭越的艺术铁律:只有遵循现实主义成规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现实主义变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时,面对艺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艺术史的变动不居,现实主义陷入了尴尬的位置。如何应对新艺术的挑战?如何应对当下的历史情境?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对传统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进而在实践中大胆创新,寻找现实主义新的可能,这就是他的主观现实主义。
在传统观念中,主观往往会和现实主义产生较大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现实主义仅仅作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其实,从阅读罗伯·格里耶的小说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小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构建在他的主观想象中,对传统的现实观、典型论、历史性提出了挑战,他的小说中创新的现实主义特质主要表现在叙事的客体性和真实性。
(1)客体性
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从1953年的《橡皮》开始,就特别钟情于借助通俗题材创造艺术效果,无论是《橡皮》和《窥视者》中的侦探叙述,还是《嫉妒》中连载小说的样式,《迷宫》中的惊险小说手法,他都突出了对外在事物地描绘,而且这种描绘精确、细致,如同照相机一样,对角度,形状,光线,位置,都纯客观地准确记录下来,而且这种描述只停留在事物本身,不表现事物内部关系,,更不关注事物与小说主题及人物的关系,他的这个世界是与“不动声色”的客观现实遥相互应的,这使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质。
罗伯·格里耶的实验小说《橡皮》 罗伯·格里耶的现实观是基于文学本质的,在他看来,“对现实的回归意味着否定僵死的形式和探索继往开来的新形式,而对现实的挖掘只有扬弃旧有形式之后才能继续深入下去。”[2]。他的小说出现在战后的法国,正在寻找小说出路的新时代,革新和颠覆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而他反对当时红火的萨特等存在主义作家“介入”政治的文学理论,他所作的努力就是要还文学以本来面目,割裂作品与政治的关系,并客观地看待现实。罗伯·格里耶所努力实现的中立立场被他诠释为一种客观主义,在创作中突出表现位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仅仅对某种客体进行细致有效的描写和记叙。在《窥视者》中,岛上的居民对小女孩的死漠然置之,就连凶杀的见证人也同样表现的“无情无义”,最后“凶手”安然地离开了小岛。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抵御了作家在创作中可能泄露出的政见、信念,同时,对于“介入”文学近乎偏执的纠正,使小说找到了一种“矫枉过正”式的客观。
罗朗·巴特在评论《橡皮》时曾经指出:“(客体)在罗伯·格里耶的书里,已经不是连接的焦点、各种感觉和象征的繁衍;客体只是一个视觉上的阻力。”这种客体不是传统的物,而是叙述者在无限可能接近真实存在。他的小说根本不是社会、心理或记忆的某种深度的经验,而只是对世界表层的文学描绘,1955年他在《为新小说辨》中就指出,“我认为人所感知的一切是时时刻刻被这个世界的物质形式所支持的。一个孩子对一辆自行车地欲望就是镀镍的车轮和把手的形象。驾驶汽车的人碰上十字路口所感到的恐惧就是在急刹车的响声中眼前猛然出现的黑色车头。”[3]没有经验支配,在罗伯·格里耶小说中,许多形象以不同面目不断显示在内部空间能够容忍的变形之中,在《嫉妒》里,一切事情都是在一个内心蕴藏着某种激情的人的目光下进行的,而那墙上烂了的潮虫作为一个纠缠不清的主题又呈现出来。他的小说,从他把物当作“视觉上的阻力”来看,是客观的,特别是当他为了心理内容的具体素材而摆脱抽象的分析时更是客观的,只不过,他赋予这种客观性以新的诠释,使他的现实主义在不断的虚构下走向主观。
(2) 真实性
时代在变化,“真实性”的概念也在变化。巴尔扎克时代作家可以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诱导读者进入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世界,读者由此得到一个稳定的,严密的,连续的,具有单一意义的世界形象。19世纪的作家这样做无可厚非,因为巴尔扎克时代的真实性是冰冻时代的真实性,现实世界是已完成的,固定不变的,完全可以解释的。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小说的历次改观足以证明,真实性已经彻底改变了。从福楼拜开始,真实性已经开始有了增殖与衍生,叙述中出现了空白和漏洞,到了罗伯·格里耶这里,作家与读者面对的已是一个暂时的,飘忽的,不可捉摸的世界,巴尔扎克的方法在这个时代只能变成麻醉剂。讲故事根本不行了,如何勇敢地面对真实以及表现真实,才是作家的当务之急。罗伯·格里耶把真实理解为从未完成的始终在变化的概念,在他看来,艺术家的每一次创新都是再创造出一种真实。他把真实置于文本可能的想象中,想象创造了一切,想象又毁灭了一切,所有的真实都是一种自我感觉,一种悬在空中的俯视目光。
在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中,故事不再是小说的中心,也没有传统概念上的直线或曲线的情节发展轨迹,作品总是以放射、发散的形态展开。大量片段的穿插打断了整个故事的叙述,片段与片段的互相质疑与矛盾取消了串联整个故事的可能,故事发展中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尾,完全被解构,作品在混乱、矛盾、支离破碎的状态中向读者昭示出情节的千万种可能与不可能。1985年,他在接受法国《读书》杂志记者布罗什埃采访时说,“当作品(Text)一旦凝聚成功,真实性也就产生了。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并且永远相信。《吉娜》中的小男孩从家里出来,穿过大街时,被一块街石拌了一下,跌到了,我认为他是真的跌到了,认为这是真真实。”[4]在他看来,真是就是一种态度,对世界的认识观。20世纪60年代,罗伯·格里耶转向电影后,更加强化了他的这种真实观,他成为左岸派电影流派的一员,并撰写了《去年在马里安巴》的剧本,电影获得了成功,罗伯·格里耶认为,作家的目光如同景深镜头一样,永远是“纪录事件”,实现了“摄影的美学特征就在于它能揭示真实”的理论。罗伯·格里耶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世界,今天的读者再也不能蜷缩在虚妄的幻想中。他警告现代读者,如果你有时感到对现代小说不适应的话,那么同样,当你周围生活的陈旧结构和标准都在衰退时,你也会在当今世界中惶惶然而不知所措。
3、在主观现实中构建新的小说大厦
罗伯·格里耶展示的是一个异样的客观与真实,他的现实主义是在毁灭19世纪巴尔扎克、福楼拜的传统现实主义和左拉式的自然主义基础上的大变革,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寻求小说的独立地位,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本质。他认为“小说根本不是一种工具,它不是为一个预定的工作而设计的工具,它不是用来展示、表达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外就已经存在的事物。它不表达,它只是探索,而探索的对象正是它自己。”[5]让小说回归“自己”,就是把小说叙事置于每一个可能的主观想象中,没有经验,没有必然,所以没有答案,没有因果。
在毁灭传统小说的过程中,罗伯·格里耶创造了他的小说体系,把现实主义从经典派的客观、真实描写外部世界转向没有经验的主观现实,在这个体系中,他取消了传统现实主义中的情节和人物,取消了典型环境和客观纪录, “在写作《窥视者》的时候,海鸥通过不同方式从外部世界而来,在它们进入我的头脑中的同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真实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想象中的海鸥。”[6]
在虚构和想象的主观现实中,罗伯·格里耶建立的是一个伟大的新小说大厦。
(1) 新的世界观:
罗伯·格里耶被评论家冠以视觉小说家,写物小说家,客体小说家,表面小说家等等。这源于他在作品中对于物的描绘及其关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罗伯·格里耶在小说中所展现的世界是与马克思、卢卡契指出的社会现象——“异化”或“物化”相一致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人与物的现实世界也已经逐步改变了。作为基本现实的个人已经渐渐消失,而物的独立性却不断增强,并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独立结构的自主的世界。在这个被物物化的世界中,人只有在人表现为物的结构和属性里才能找到人的真实存在。在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中,物件总是超出我们所能及的范围,作家所要做的是记录物与人的距离,物本身的距离,物与物之间的距离,所有这些就是想确认物是客观存在的,物就是物。罗伯·格里耶走向物的本原状态,使物在第一次获得独立存在的同时,人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意识到其主观性的有限的范围及物对他们的作用,真实的世界第一次被还原了。在他的作品中,这种意图的表达是通过取消比喻的方法、拟人化的描写等多种手法来达到的,同时作品中人的存在往往是由物的存在来加以确认的。
(2)新的价值观
传统小说是一种追求深度的写作,作家总是尽力去分析,容纳描写对象。在描写外物世界时,作家会一层一层地挖掘,试图深入到最隐秘的底层,而在描写人时,则去触摸人激情的深渊或者令人难堪的秘密。作家欲通过这种描写把握世界的本质,理解人生的意义。罗伯-格里耶看到,当现象学进入所有的哲学领域,物理学发现了间断函数的重大意义,心理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我们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光滑的平面,毫无意义,毫无灵魂,毫无价值,不可捉摸。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力求不再教人以医生或上帝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而是教人以除眼前景象外别无他物的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在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中,他通过平面描写和重复描写来表达他对于无深度无意义的追求。平面描写在作品中表现为如摄影机似的对于事物的捕捉,罗伯·格里耶认为只有那限于度量、定位、限制的描写,才能够触动人们,使人经久不忘。平面描写使对象从它与人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剔除了人们对于深度的向往,对于意义的寻求,读者心灵中的神话在不知不觉中被摧毁。物就物,就是存在,而他重复描写中那些相互矛盾的混沌的东西消解着读者对于意义的建构。当读者读到第一个片段时,以为已经把握了什么的时候,与之矛盾的场景会纷至沓来,在场景的力与力的互相抵消中,深度的追求不再可能。《窥视者》中,马弟雅思到底是不是凶手,《嫉妒》中,A与弗兰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去年在马里安巴》中的“去年”是否存在,这一切让读者无从探求,并将最终放弃对于意义及深度的向往。而他取消人们以往的经验和可能的推断,就是要在主观的描写中使世界回归到自身,回归到本真状态。
(3) 新的写作观
当罗伯·格里耶归还了小说的真正面目之后,小说的目光就应该转向它自身,形式的革新成为关注的焦点。罗伯·格里耶认为当作家想创作一部作品时,总是写作首先占据他的思想,是写作在召唤着他,作家首先考虑的是句子的运用,结构,词汇等等,是形式构成了作家特有的世界。
罗伯·格里耶采用新的主观叙述视角。他认为,传统小说家的叙述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同时出现在一切地方,同时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同时掌握着人的面部表情和他内心意识的变化,他既了解一切事物的现在,又知道过去和未来。”[7]传统作家用上帝的口吻讲述着连贯而肯定的故事。在中世纪,一个作家把自己知道的一个故事讲述给同样知道这个故事的听众,但在20世纪,一个作家把不知道的故事讲述给同样不知道故事的公众。罗伯·格里耶用他的作品嘲笑着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视角。《窥视者》中,作品的叙述方式采用的是传统的第三人称,一个窥视者的口吻。而作品所展现的无非是一个窥视者有限的,不确定的经验。窥视者用他的想象、欲望操纵着叙述,而主人公行为中“一个小时”的故意遗漏,更使得叙述似是而非,无法确定,彻底摧毁了作者或叙述者要成为无所不知的上帝的欲望。在《嫉妒》中,由于对于叙述者本身的怀疑,使得他的叙述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游移,不能确定。
新的叙述视角带来了新的叙述形式。罗伯·格里耶在其小说创作中对传统小说样式进行戏谑似的模仿,从而达到建立一种新的叙述形式的目的。《橡皮》即是罗伯·格里耶对传统侦探小说的嘲弄,凶杀案在本该发生的时候没有发生,在不该发生的时候却阴差阳错地发生了,本来是侦察案件的侦探,最终却变成了凶手。《窥视者》中的案情则被作家肢解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读者理出线索的努力被作家一次次破坏,在作品中永远找不到答案。同时,罗伯·格里耶在作品中不断宣称,作品是虚构的,这与传统小说竭力弥合虚构痕迹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小说的叙述形式由此在形式主义的道路上不断迈进。三、 罗伯·格里耶小说不是现代主义小说
罗伯·格里耶的主观现实主义将人物的想象作为一种新的现实,还小说以本来的面目。在他的小说中,现实是模糊的,或者说客观环境总是模糊的,只有主观视野下的世界才是他乐此不疲的主题。他不关心那种细小具体的现实材质,经典现实主义确定的客观真实性被他丰富复杂乃至相互冲突的主观真实所瓦解,变成纷杂的心理碎片。他认为,小说作者不是记录,而是要创造,在主观想象中创造现实。
基于这样的认识,很多人在解读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时,自然将其列为现代主义小说,也使他的小说充满了争议。但是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上来分析,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并不是一种现代主义,而是变革了传统经典现实主义中人物、环境、真实的主观现实主义。
罗伯·格里耶将他的文本实验运用到电影中 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界定理论中,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根据德鲁兹瓜塔里的理论提出的“符码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詹姆逊指出,中世纪是神学话语统领一切的超符码化的时代,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是解符码化时代,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启蒙主义的理性话语和现实主义文化,而到19世纪末随着神圣感的消失、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命的碎片化,人们企图在文学艺术中以各种象征的方式创立一种新的宗教,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再符码化。进一步地,用语言学的符号理论来表述这三个阶段,就是:在解符码化即现实主义时代,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被认为是内在地一致的,且共同指向某个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指涉物);在再符码化即现代主义时代,现实主义的指涉模式受到消解,曾经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客体的参照物被弃之一旁,能指与所指结成的语言符号被认为具有一定的自足性。美国文艺理论家赖恩?麦克黑尔也指出,现代主义的主旨是认识论的,而现实主义的作品以本体论为主旨。
分析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还是一个客观世界,一个被还原成物的想象客观,参照物依然存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只不过罗伯·格里耶的现实是隐蔽的,是抛弃经验的,但所有的一切都以认识世界为线索。法国的罗兰·巴托在分析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时,认为他的小说中“时空交错、视觉的层次,对传统客观的分割,空间的描绘而非类比的描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新优点,他说,“这种现实主义把客观世界简化成纯粹的客观,终于使物摆脱了他们浪漫主义的心。” [8]罗伯·格里耶的努力就是变革传统现实主义那种全知全能身份带来的叙事可靠性,瓦解了作为物化的人在小说中的受统治地位,但是罗伯·格里耶没有走向现代主义消融一切深度的终极,他仍然在发掘世界的本体,发掘世界在人的想象中如何走向真实。可以说,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具备了现代主义的精神,但并不属于现代主义。四、 罗伯·格里耶的影响
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变革特别是他对现实主义文本形式的变革影响是巨大的,作为新小说派的主将,新小说确立的文学主张在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对欧洲文学整体走向现代主义创造了条件,他的主观性叙述使小说的情节化和深度理论受到挑战,使小说在颠覆中走向未来。
同时,由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电影创作,把新小说理论带到影像世界,丰富和发展了“左岸派”,新小说和左岸派的结合在法国掀起了一次文学高峰,《去年在马里安巴》的成功将主观现实主义的想象和虚构从文本走向电影世界。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罗伯·格里耶创造了所谓“集合”小说,他在《幽灵城市地志学》中说,“我写建构这个字,一个欺眼法的绘画,一个想象的建构,而我依此为一个未来神祗的废墟命名。” 罗伯·格里耶所以能够任意拼贴其它艺术作品,构成自己的文本,是基于挑战文本必须根据某一既有真实而创作的概念。他以欺眼法的方式,建构一个想象的真实。画布上几可乱真的细节,在刻意的拼贴之下,却凸显此空间的虚构性,“这就是欺眼法、超现实、达达、普普与罗伯·格里耶共通的符号实验,也正是后现代情境中文本断裂、指涉循环与后设文本的游戏征状。”[9]后现代主义在他的小说实践中找到了契合点。
参考文献
[1] 郭宏安 《20世纪法国小说的图景》
[2] 柳鸣九 《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第321页
[3] (法)米歇尔·莱蒙 《法国现代小说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年 第339页
[4] (法)让雅克·布罗什埃《阿兰·罗伯-格利耶》 1985
[5] 柳鸣九 《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第322页
[6] 柳鸣九 《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第323页
[7] 王忠琪 《法国作家论文学》 三联书店 1984 第399页
[8] (法)米歇尔·莱蒙 《法国现代小说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年 第337页
[9] 刘光能《法国「新小说教皇」霍格里耶》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 第24页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