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1《沉落者》:我们都是艺术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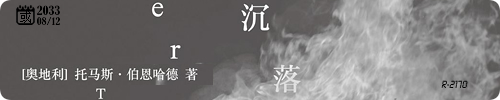
过了五十岁还活着,我们就是越界的胆小鬼,我想,那就倍加可怜。
不少人五十一岁选择自杀,还有的人在五十二岁自杀,“但五十一岁自杀的人更多”,无论是五十一岁还是五十二岁,也无论是自杀还是自然死亡,都指向了死亡,而且也都越过了五十岁,所以真正死亡的原因是他们都跨越了五十岁这个界限,因为跨越而“感到羞耻”,“如果我们超过五十岁还活着,还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就会把自己变得很卑劣。”五十岁之后还活着就是卑劣的,就是胆小的,就是可怜的,所以过了五十岁,无论是五十一岁还是五十二岁,无论像格伦·古尔德那样因脑溢血而自然死亡,还是像韦特海默选择自杀,都是他们最后不再越界的必然命运。
五十岁而成为活着还是死去的界限,其实多少是伯恩哈斯玩的一种数字游戏,因为在没有年龄的标记下,死亡也照样会发生,而且是在追逐着死亡之后的必然行动。比如我和韦特海默就曾经经常到僧侣山上,“僧侣山也被称为自杀之山,因为它比任何山都更适合自杀,每周从这里往下跳的人至少三四个。”这是一座让自杀者痴迷的山,或者攀登上去,或者乘坐电梯,然后从里希特山顶往下跳,生命就这样固定在了没有越界当然也不再是卑劣、胆小和可怜的年纪。比如韦特海默在放弃音乐之后最感兴趣的就是医药方面的书,他的习惯就是去医院和临终病院,去养老院和停尸房,“如果因种种原因无法去医院,他便读关于病人与疾病的文章和书籍;如果没有机会去临终病院,他便读关于垂危病人的文章和书籍;如果无法去养老院,他便读关于老年人的文章和书籍;如果没有机会去停尸房,他便读关于死人的文章和书籍。”
为什么选择自杀,没有人死亡是必然,因为死亡是终止生命的唯一形式,而生命意味着不幸,出生是不幸,活着是不幸,并不是说生活中只有不幸,不幸的前提也能是幸福,而是,“只有经过不幸这条弯路,我们才能幸福”,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而其实幸福各有各的幸福,只有不幸是相似的,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也具有了相似的性质,“只要我们活着,不幸就持续不断,只有死亡能将其终止。”死亡可以终止不幸,所以在过了五十岁之后,在五十一岁或五十二岁甚至更长久地活着,那就意味着你的不幸会随着生命的长度而不断被拉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都会被不幸填满,那么这样过一生还有什么意义?
格伦因为脑溢血死了,这是自然死亡,还不能称为一种自己选择的死亡,或者说不是自杀者,但是韦特海默选择了把自己吊死,这是主动的死亡,而我一直痴迷于自杀,甚至在别人看来自杀者不是韦特海默而是我,自杀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必然选择,那么我们生命中到底有哪些不幸?我学音乐读的是莫扎特音乐学院,但是我并不是喜欢音乐,也不是有音乐的天赋,去莫扎特音乐学院只是为了对抗我的父母和家庭,“不是喜欢,而是利用它来对付他们”,韦特海默也一样,他上大学学艺术和音乐,也是为了对着父亲干,“他曾经说,我上大学学钢琴,对父亲来说就是灾难。”这一点格伦也一样,“格伦说得更极端:他们憎恨我和我的钢琴。”除了和父母对抗之外,在我们的眼中,萨尔茨堡这座城市是最敌视艺术和精神的城市,就像狭隘、闭塞的山窝窝,“这里的人愚蠢,这里的墙冰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一切都将变得愚钝和麻木,无一例外。”同样,对于奥地利,我们认为这是“习惯的奴隶”,人们在习惯的泥沼里艰难行走,他们是“可怜的人民”,他们被社会主义蒙骗了,“社会主义者已非社会主义者,我说,今天的社会主义者是新的剥削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都是骗局……”
| 编号:C38·2250818·2339 |
城市狭隘而闭塞,没有艺术精神,人们是习惯的努力,他们愚钝和麻木,父母是顽固的存在,他们制约着艺术家的生成,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幸的世界,唯有死亡才能终止这一切,但是当选择音乐而对立于家庭、社会、人民和国家,音乐反过来并没有真正拯救他们,甚至是他们成为“沉落者”的主要原因。之前我和韦特海默师从钢琴大师霍洛维茨,住在利奥波德斯克龙学了整整二十八年,但是当格伦加入其中之后,虽然我们从霍格罗茨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之前在莫扎特音乐学院和维也纳艺术学院学的东西都要多,但是格伦在霍洛维茨那里进行强化训练之后,他的钢琴比霍洛维茨弹得还要好,甚至已经超过了老师,“从这一刻起,对我来说,格伦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钢琴大师,无论我从此刻起还听到过多少钢琴家演奏,都没有一个人比得过格伦,即使是我一直喜欢的鲁宾斯坦,也不能与其比肩。”格伦的确是钢琴的天才,我将他对艺术的痴迷称为“钢琴极端主义”,他超过了老师成为了首屈一指的钢琴大师,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使人敬畏的方式进行修炼,甚至自己也无法从中解脱出来,“他也不愿意脱离这样的境地”。
面对天才,面对“钢琴极端主义”,我和韦特海默放弃了钢琴演奏,因为我们无法像格伦那样达到痴迷和令人敬畏的境地,也不想让自己沉浸其中而无法解脱,于是韦特海默转向了精神科学方面,而我则进入了衰败的程序,我把心爱的钢琴送到了教师家里,把它给了教师的女儿,而且我知道新主人是一个毫无音乐感觉的人,那架最好的、最令人羡慕的、最难得到的也会死最昂贵的钢琴,只有毁坏这一最后的命运。没有了钢琴,我依靠那些警句格言成为了哲学家。于是按照格伦的说法,我们都成为了“沉落者”,不断下滑的沉落者,再不会通过努力攀爬到艺术高峰的沉落者,“韦特海默,这个沉落者,对于格伦来说,他越来越下沉,不停地下沉;对于格伦来说,我随时随地都把哲学家这个词挂在嘴边,频繁得让人无法忍受,总之,对于格伦,我们毫无疑问分别是沉落者和哲学家,我走进旅馆时想。”
放弃了音乐,摧毁了钢琴,在钢琴端主义者格伦看来,我们的确是沉落者,放弃了理想、艺术的沉落者,依靠所谓的精神学科和格言警句过活的人。但是与其说伯恩哈德用“沉落者”形容艺术理想覆灭的人,不如用“越界者”更恰当,就像跨过五十岁这个生命界限还在不幸的世界里活着的人一样,活着就是一种越界,而当在跨过之后最后选择死亡——自然死亡或者自杀,也是一种越界,一种颠覆了秩序的越界,一种自我异化的越界,一种没有定位的越界。格伦成为了钢琴大师,但是他的钢琴极端主义让他无法自拔,从萨尔茨堡返回加拿大之后迅速崩溃,他患有中风,也有肺炎,但是让他的生命终结的不是这些疾病,而是无法解脱的钢琴极端主义让他在演奏最经典的《哥德堡变奏曲》中脑溢血而身亡。而韦特海默呢,在格伦死后,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竟然能活过天才”,在他看来就像越过了五十岁还活着一样是一种耻辱,但实际上真正导致韦特海默自杀的原因不是这种羞耻,而是在他妹妹离开之后别无选择而上吊自杀,在他看来,妹妹才是他的唯一,他无法接受最亲的妹妹竟然离开自己和颓势化工企业家结婚。
韦特海默称之为“灾难性的结合”,这像是兄妹亲情的体现,但是韦特海默就是一个越界者,他和妹妹在一起二十多年,不是像哥哥那样呵护妹妹,而是像暴君一样控制着妹妹,让妹妹依附于他,这种衣服的一个形象比喻就是:“我把我妹妹只作为乐谱的翻页者来使用……”在他看来,没有人翻乐谱比她好,在他的指教下,不识乐谱的妹妹成为了“天才的翻谱者”,当她终于挣脱哥哥的束缚远嫁他人,对于韦特海默还说当然是致命的打击,自杀成为了他最后的选择。格伦有着音乐的天赋,但是在钢琴极端主义中无法自拔,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韦特海默没有呵护妹妹反而像暴君一样控制着妹妹,最后导致她的离开,也导致了自己的自杀。无论是格伦还是韦特海默,他们并不是真正活在音乐和艺术的世界里,他们并不是因为社会、家庭给了不幸而有尊严的死去,他们也不是因为遭受了不理解而成为沉落者,他们就是背叛了自我定位而变成了越界者,“韦特海默、格伦和我都是残疾人,我想。”
成为残疾人就是把合理的世界颠倒了,就是从应有的秩序越界了,或者说,由于狂妄和傲慢,“我们把自己弄成了艺术作品”,本来是驾驭艺术生产艺术品的艺术家,但是却抹除了人的特性而越界成为了艺术作品,“我们是总想逃脱自然的人,但又总是做不到,这是当然的,他说,我想,我们就停留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而当格伦死去,韦特海默自杀,最后留下的我呢?会是另一个越界者?会是另一件艺术品?“我是唯一还活着的人了!现在我孤独一人,我想,如果实话实说,我生活里只有两个人使我的人生富有意义:格伦和韦特海默。”他们的死带来的启示是:我必须正确应对这个现实,遇到造纸厂的女老板似乎是另一个启示:一个同样患过肺病的女人,一个与工人结过婚丈夫却在事故中死去的女人,一个在生活中遭遇了不幸的女人,但是她没有选择自杀,也没有越界而喜欢音乐、艺术,更没有在极端主义下寻找自己的理想,反而是在感恩韦特海默在他最无助、煎熬的日子里给她的帮助。
没有沉落,也没有沉沦,生活中的不幸还是不幸本身,所以对于曾经最可能自杀的我来说,对于格伦和韦特海默的自杀造成了极大影响的我来说,女老板是一个反面,自杀也成为了生活的反面,最后当我在韦特海默的房间,“我看到韦特海默的电唱机还敞开着,上面放着《哥德堡变奏曲》的唱片,于是我启动了电唱机。”韦特海默的房间,格伦的《哥德堡变奏曲》,当我启动电唱机,像是从他们的死亡和艺术中发现了生活真正的变奏曲,极端的爱,极端的反抗,极端的傲慢,以及极端的自我,才是真正跌落生活的沉落者,不如以一个听众和观众的身份重新开启生活,从越界中返回,过了五十岁当然还应该活着,就像伯恩哈德,1983年出版《沉落者》时他52岁,过了五十岁的年纪,活着的年纪,创作的年纪,不再沉落的年纪。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