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06 我不是潘金莲

1365页的《金瓶梅词话》,上下册精装,打开。这不是充满仪式的阅读,也不是偷偷摸摸的阅读,这只是一本普通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10月1日第1版,开本32,相关的数据还可以详细到21.8x15.4x6.2cm的尺寸和1.8Kg的重量。如此等等,只是一件普通的商品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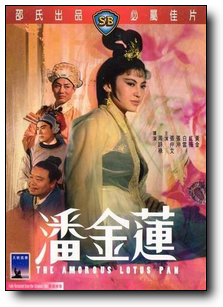 |
| 张仲文版《潘金莲》 |
 |
| 李香兰版《金瓶梅》 |
 |
| 1998央视版《水浒传》 |
 |
| 杨思敏版《金瓶梅》 |
 |
| 芭蕾舞版《金瓶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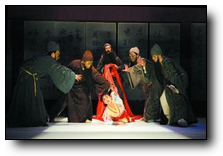 |
| 中央戏剧学院《金瓶梅》 |
 |
| 王紫瑄饰演潘金莲 |
 |
| 魏明伦的荒诞派川剧《潘金莲》 |
我的阅读从初冬的这个夜晚开始,依旧像一直以来的阅读一样,拿着扫描笔,摘录一两段句子。未曾想的是,做好作业的小五站在我的身后,突然冒出一句:“潘金莲是谁?”这一疑问一下子将我带向不安的境地,曾经阅读的时候小五从来没有看过我摘录的内容,也没有那么准确地抓住“敏感词汇”,甚至将我带向一个敏感地带:“潘金莲是谁?”这个问题的潜台词似乎是:“爸爸,你到底在看什么书啊?”
这纯粹是我的“过度诠释”,小五当然不知道有关此书的沉浮和敏感,只是那么随口一问。但问题是,我读了那么多书怎么就从来没有问过我?而且为什么会对潘金莲是谁感兴趣,那摘录的句子里似乎还有和潘金莲一起弹奏乐器的玉莲?不安来源于偶然,来源于潘金莲而不是玉莲,或者,不安仅仅来源于对这一本“禁书”的“过度想象”。
潘金莲是谁?或许也是一个文学史上以及文学研究上的命题。自从《水浒传》最早出现潘金莲,直到《金瓶梅》的演绎,“潘金莲”早就超越了一个文学形象,而给予更多文学以外的想象。施耐庵说:“女人是祸水,任我口诛笔伐,声名狼藉早已盖棺定论。”而在《金瓶梅》里,则成为另一个符号,她是情欲的最高代表及书中死亡之最惨烈者。潘金莲是情欲的化身,这情欲不仅仅只指性欲方面,也指她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书中潘金莲情欲失控,致人死者有武大郎、李瓶儿母子、宋惠莲、西门庆诸人。所以自此,潘金莲不仅代表着情欲极其毁灭,也代表着“杀人凶手”,潘金莲被钉上耻辱的十字架。
但似乎,这不是对潘金莲盖棺定论的终结,百年来,许多文人和作品对潘金莲进行了重新的演绎,除了对“金莲以奸死”的深度挖掘外,也有很多声音,给潘金莲“平反”,尤其是近现代,对潘金莲给予了更多肯定。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张宇的《潘金莲》、何小竹的《潘金莲回忆》和阎连科的《金莲,你好》,都将其塑造成反对封建制度的勇者。而随着多元化的发展,潘金莲从文本走向更广的娱乐圈,大量的电影、电视剧开始塑造和重构潘金莲形象,潘金莲影视作品举不甚举,“十大女星演绎十版潘金莲谁最风骚?”“盘点潘金莲十大版本谁更香艳?”“盘点各个时代娱乐圈中的“潘金莲””……如此等等,“潘金莲”完全成为娱乐圈中的一门“显学”。
潘金莲已经不是一个女人,而成为一个符号,淫欲的潘金莲,嗜杀的潘金莲,压抑的潘金莲,反抗的潘金莲,封建殉道者的潘金莲,追求自由的潘金莲,不是潘金莲的潘金莲,而且潘金莲也从具体有关的“水浒传”、“金瓶梅”中脱胎而出,与张三李四一样,仅仅是一个名字,衍伸到现实生活中。比如阎连科的《潘金莲逃离西门镇》,把潘金莲重新投进当代生活的漩涡,演绎了一段发生在金莲身上,充满苦辣酸涩的人生际遇和情爱故事。还有就是眼下热门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作者是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不是“欲火烧身,淫心荡漾”的潘金莲,不是“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的潘金莲,更不是“爱武松、怨武松,那边秋雨这春风”的潘金莲,不是潘金莲是李雪莲,“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个龟孙结回婚,然后再离婚。”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告状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二十年。
一个妇女的难言之隐?一个妇女的社会学样本?刘震云说,《我不是潘金莲》,听上去像是在《温故一九四二》中的那个主题,生存依靠的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近似残酷的社会环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李雪莲最后证明了这个主题,还是仅仅是一个标本,甚至还是一个牺牲品?想到电影《一九四二》,作为原著和电影编剧的刘震云在接受采访时说:电影最后和老东家在雪地里相认的“妮”才是主角,那一种走下去的坚韧是最后的温暖,是母性的最大展示。
当然,那个“妮”后来就是“我”的母亲,灾难之后的生存比什么都重要,而靠身边的人活着成为最温热的人性关怀,就如刘震云所说:“老张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的阿Q精神不是信仰,是生存的法则。但是电影似乎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人性故事,是战争、国家、元首组成的大历史,历史灾难之下的悲凉或许是刘震云的无法逃避的,而电影更加强化了这一主题,有学者甚至指出,电影中的“影射史学”的做法是拿历史说事,“是过于轻佻。”
历史无法还原,所以“一九四二”只是一个可以温故的另类“读本”。《一九四二》的最后,老东家发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为什么我要逃这个荒?”其实是无解的,更是一个伪命题。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什么?就像小五的那个问题:潘金莲是谁?没有答案,或者问题就是答案。而回到潘金莲这个符号身上,从文学形象开始,几百年来的过度诠释,也带来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我是潘金莲,我不是潘金莲。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587]
顾后: 从草场到墓场:十年一觉博客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