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03 夜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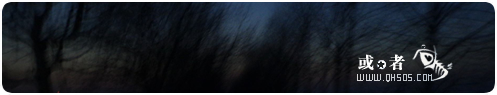
你旅居某地的经历,会在你喋喋不休的
自传里留下一个无言的空白时段。
——奥登《异地疗养》
奥登的诗歌根本不带在身边,所以一个夜晚根本不构成一部自传,根本没有说话的空白时段,它只是用一种诱惑的方式制造着可能的声音,在被黑暗包围的世界里,我之经过就是在异地的别处寻找一种喋喋不休的理由,并且把这样一种黑暗当成光,安放在我陌生的脚步里。
异地,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对于久居在这个城市生活状态的一种嘲讽,似乎离开早已变成了想象之一种,它们是鲜活的,是神秘的,但却不是触手可及的,更不是真实的。所以当有人告诉我去那个地方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在一种犹豫之后还是前行了。地方是熟悉的,连同地名,连同山水,都没有意外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异地,所以不妨把自己看成是被时间隔绝的存在,只要有一个出口,就会试探着把自己推向那里,仿佛在豁然打开的时候,满目都会是光的照耀。
可是,那里没有光,只有黑夜。光在我的身后,在人群聚集的会议室里,在有些萧条的酒店里,光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那么我独自一人行走在黑暗中,是不是反而是背光的一次逆行?“而我们,在它的微光中,一个接一个地迷失:我们,一个接一个地,与光相混。”起初那个小镇是热闹的,它在我的记忆中只要转角处就可以听见人声,但那也许已是许久以前的事了,当我带着一种没有诗歌的身体,走进它的时候,它果然成了异地,果然被黑暗隔绝了所有含混的光。
只有一条路,一条整洁的路,一条孤独的路,以及一条冷寂的路,前往另一个方向的是已经被修好的宽阔马路,当车流带着隐约的光从我身后一闪而过的时候,我其实乐意把自己带向那个鲜有人经过的旧路上。向上是一个缓坡,我的目光在黑暗中是无法越过那个缓坡的,它只能跟随我的脚步,趋向可能的方向。而当光只在身后亮起的时候,我更像是走进了比黑暗更黑暗处。但是在黑暗中,我看见了自己,没有影子的自己,不害怕的自己,陪着我一步步走向可能的异地,一步步接近一种梦呓的声音。
是的,当光不在的时候,必须有声音,它是我的脚步声,是我的喘息声,也是我“喋喋不休自传里留下一个五言的空白时段”。对着谁说话,其实无关紧要,那一条路,那座山,那个黑暗,以及那在一起的自己,都可以听到。当声音出现,其实异地早就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就像那个所谓的“环形废墟”,“微暗的电灯灯光下,酷似我们的一个替身/并不抬眼,正坐在那里写着什么。”废墟里有了替身,而且正在写着什么,是一部自传,是一首诗歌,甚至是一个透明的梦境。
“他要梦见一个人:要毫发不爽地梦见那人,使之成为现实。”和现实隔了远了,就是在异地的存在,和梦境在一起,就是另一个的经历,所以我不转身不去投向那光,所以我不停步不去寻找必然的方向,只是那样行走,那样说话,那样书写,光在身后,人在身后,山在身后,异地也在身后,在如梦境的黑暗中,反而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在可能的方向上我完全可以抵达自己的现实,而这样的现实,就是我们必然要书写的那部自传。
即使只是草稿,那又何妨?“草稿的数量越来越多;他顽强地修订,撕毁了成千上万张手稿。他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不让它们保存下来。”那里一定住着另一个自己,一定有这自己的现实,甚至一定在别人之外设置了另一种异地,被黑暗包围,其实是隔绝了自己,在草稿的世界里完整呈现着,不被人看见,不被光照见,却也不被夜所驱逐。所以镜中的世界是虚幻的,但是在一种隔绝中更像是我自己的现实:现实的身体,现实的行走,现实的道路,现实的黑暗,现实的话语,现实的经历,现实的空白。
以及现实的我。“在那做梦的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为什么必须醒来?隔绝太深了,梦境露出了破绽?而在返回的那一刻,是不是重新回到异地?重新看见光亮?重新定义夜晚?像是一种宿命的返回,越来越深幽的黑暗里,越来越冷寂的道路上,越来越空白的迷失中,必须转身?必须醒来?必须面对夜?其实在这行走中何尝能逃离现实,何尝能在隔绝中自由?何尝在诗歌中看见魅影?无非是无言之言——夜终于不说话了,夜在光亮的背面制造了不见的空白,夜在我的身边安置了沉默的替身。
“他在梦中模拟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少年,但是这少年站不起来,不能说话,也不能睁开眼睛。夜复一夜,他梦见少年在睡觉。”少年如我,在含混的光里,却已是苍老。转身那一刻,我看见自己身后被拖长的影子,一直深入到没有方向的路上,那时,一只无家可归的猫踩着我的影子,看也不看我一眼,最终以相异的方式消失在浩大无边的夜魅中。
可是,我的手背上却留下了那只猫用爪子划过的那一条印痕,作为一种旅居某地的经历,我将保留在我醒来的梦境里。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999]
思前: 《火和雨》:时间的制造业
顾后: 相见时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