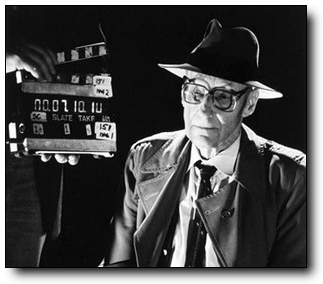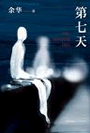 |
编号:C28·2130624·1003 |
| 作者:余华 著 | |
| 出版:新星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29.50元亚马逊22.10元 | |
| ISBN:9787513312103 | |
| 页数:232页 |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死是不是必然的归宿,死是不是比现实更为荒诞?《第七天》作为余华蛰伏之后的一部长篇,依然是关于最通彻的死亡叙述,不是肉体的安息,不是灵魂的寂灭,被预约的死里还有挣不脱的惶恐,“我感到自己像是一棵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在现实的尘埃里,一定会看见那些强拆、上访、高价墓地、离异、卖肾、爱情的故事,当然,还有iphone。这是被劫持的死亡,它不是回避个体,也无法逃避社会,余华说:“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
《第七天》:越过生死边境的余华式疼痛
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第七天》
The Seventh Day,第七天,不是复数,是序列,不是过程,是终点。那题辞上明明写着那句已经泛滥的引用:“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已经不在救赎的路上,神在安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疲倦到“歇了一切的工”,那么死亡是不是也需要用安息的方式抵达“人人死而平等”的“那里”?七天,第七天,或者无数个七天的段落,在时间的重复里是死亡的重复,它遍及每一个必须经历从生到死的生命,但是在招手、微笑和问候里,轻易抵达的死亡却从来没有逃避现实的疼痛。
如果从时间的序列中寻找到一种全新的感受,不妨将这个生与死的过程打乱,所以在阅读体验中,先从《第七天》开始,某一章节,和题目处在同样的文字里,第一句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鼠妹说,“我的身体好像透明了。”第七天的透明,是因为第七天要完全从过去的那个”斑驳陆离,虚无又真实“的隔世记忆中挣脱出来,就像对鼠妹的净身,“不是很多人,是所有的人。”然后“排着队把河水端到你的身上”,死亡的仪式完全是一种释然,望不尽的道路其实是走向最终的安息之地,像神一样,歇了现实的工,而那片死亡之后所要到达的墓地却是鼠妹活着的男友为她购买的,“我不是去嫁给伍超。我是去墓地安息。”这里隔开了现实的生和现在的死,隔开了为了爱情的生命和死亡,只不过当殓衣被当做婚纱,所谓走过去那个“人人死而平等”的地方只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挣脱的现实,只是现实的另一种投影。
第七天的投影真实而又痛苦地横亘在每一个死去的人的面前,还有我和父亲的相逢,“我和父亲永别之后竟然重逢,虽然我们没有了体温,没有了气息,可是我们重新在一起了。”原本是别离和失踪,原本是在“分开的两个世界里互相寻找”,只有在死去的时候,才会最终相逢,重新在一起是归宿,也是命运的无力反抗,其实,这不是荒诞,这是逼仄的现实,所为逃避在最后的死亡面前,依然是一种回归:
他问:“那是什么地方?”
我说:“死无葬身之地。”
死亡葬身之地又将命运连在了一起,活着的和死去的寓言都只是换了一个场景,第七天其实就是第一天,人人死而平等其实也是人人死而不等。所以即使从最后的“第七天”翻阅开始,即使用最后的“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来证明某种书写的荒诞,即使在时间的片段里已经过去了无数个第七天,但是翻过第七天的时候,又必须回到“第一天”,回到那个死亡的开始,被预约的九点半的开始:“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这是浓雾弥漫的第一天,这是空虚混沌的城市里的第一天,这是我一个人孑孓而行的第一天——死亡总是以某种虚幻的方式降临在这个已经被“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的现实。但是结束预示着新的开始,预示着没完没了、不断重复的现实,死无葬身之地的投影里其实没有净身,没有穿上殓衣,没有解脱,陈旧臃肿的棉大衣,A64号的排队序列,以及沙发那边正在“谈论自己寿衣和骨灰盒的昂贵不同”的死者,都在还原着现实的场景。还有那个市长告别仪式,“早晨烧了三个就停下了,要等市长进了炉子房,再出去后,才能轮到您们。”也依然是现实里的特权。
死亡是这里,活着已经变成了那里,这里和那里,是春天和冬天,是殓衣和婚纱,是净身和肮脏,但是这种对生与死的隔离只是一种想象,不管是记忆还是仪式,都要把这里的一切世俗化,甚至荒诞化。市长的遗体告别仪式背后就是一个被遮掩的现实,官方的解释是工作操劳过度而突发心脏病去世,而民间的流传说法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行政套房的床上,与一个嫩模共进高潮时突然心肌梗塞,嫩模吓得跑到走廊上又哭又叫,忘记自己当时是光屁股。”官方和民间,不同的话语体系代表着不同的现实,而在这死亡的世界里,现实还是在延续,只有等市长的炉子烧好之后才能轮到那些卑微的死者,甚至炉子本身,就有着尊卑的区别,两个炉子“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国产的。进口的为贵宾服务,国产的为您们服务。”
赤裸裸的现实,使这边和那边又连接在一起,所以那个“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的世界,那个“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的世界只是一个幻觉,是另一个现实,尽管里面有着我和父亲的重逢,有着鼠妹和男朋友的冰释,有着袭警者和警察相互下象棋的和谐,但是这也都是虚构,“十多年前,他们两个相隔半年来到这里,他们之间的仇恨没有越过生与死的边境线,仇恨被阻挡在了那个离去的世界里”。
而在虚构的背后,一定是一个赤裸裸无望的现实,这种用死亡的荒诞来重返现实的方式看起来是余华的一次解构,但实际上依然是迷失,是错误,是无法摆脱的先入为主。生的世界就在那边,也在痛苦无常而死去的我不能抹去的记忆里——如果这样的生是一种痛苦一种悲剧,必然是从个体开始。“一列火车在黑夜里驶去之后,我降生在两条铁轨之间。我最初的啼哭是在满天星辰之下,而不是在暴风骤雨之间。”这是出生的荒诞和痛苦,我被速度带进了黑暗中,父母远离我而去,被抛弃的出生现实让人生的意义变得曲折,养父把我养大,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但是悲剧的传染性并不只是一个个体的不幸,“我的童年像笑声一样快乐,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正在毁坏父亲的人生。”这种毁坏是将父亲的人生道路安置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婚姻世界里。也就是说,我被抛弃的出生也是养父被婚姻抛弃,这种抛弃或者是养父自愿的,甚至有过想送我去孤儿院的再次遗弃的经历,但是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我背负的那种出生时的罪孽将父亲“拋弃在站台上”。
其实,和死亡一样,出生的偶然性也是无法更改的,里面有着现实的尴尬,被拒绝出生也是另一种死亡,我出生在铁轨,父亲拒绝婚姻,都是在扼杀正常的人伦仪式,所以在我的个体生命中,和李青的结婚看起来是一种自我的超越和救赎,是对于卑微身份的挣脱,但实际上也是一个轮回:“她回家后重新服用避孕药,她说暂时不想要孩子。”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我成为李青的丈夫,这种像肥皂剧一样的故事自然只是一种媚俗,这里其实没有爱情没有对自我的超越,因为结婚之后李青在飞机上遇到让她野心有了飞翔机会的海归博士,不想要孩子的约定变成了婚姻里的一种轮回,而李青在和我离婚之后和博士的结婚,也是一个悲剧,“他在外面包二奶,还经常去夜总会找小姐,我得了性病后就和他分居了。”以至最后李青在浴缸里的自杀,完全是一出道德谴责剧,就像我对于自己亲身父母一样将我遗弃在铁轨上,都充满着道德的鞑伐——李青的死不是救赎,是惩罚,“我躺在浴缸里 血在水中像鱼一样游动,慢慢扩散,水变得越来越红”,爱情的死亡在我的心里反倒有了某种快感。
但是,自我的迷失并不仅仅只有出生的无力和无奈,那个正在离去的世界远非这样一种个体的悲剧人生,所以在余华构筑的文本里,在与我有关的记忆里,便涌出了诸多和社会有关的种种荒诞,这里有瞒报重大事故死亡人数的丑闻,有二十个被处理死婴的悲剧,有商场火灾造成无辜死亡的事件,也有袭警、强拆、卖肾买iphone的新闻,以及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当这些事件和悲剧被我连在了一起,而和事件有关的人也都走到了死亡的“这边”,“每一个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都有着不愿回首的辛酸事,每一个都是那里的孤苦伶仃者。”但是当他们都走到这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都走到了他们共同的归宿,“死无葬身之地:我惊讶地看见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有流淌的水,有青草,有树木,也有果子和树叶,还有心脏的模样和跳动节奏,仿佛是希望之所,和谐之所,但是,“我看见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只剩下骨骼是不是也是行尸走肉,是不是也是一种谎言?是的,死亡也是走不出的迷失之所,而现实也一个永无无葬身之地的存在。
爆炸而死,火灾烧死、被车撞死,自杀而死,这形形式式的死,几乎都没有“老死”,也就是说,所有的死亡都是非正常的死亡,在荒诞的现实生活里,这样的非正常死亡是不是具有最大可能的批判性?余华:“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很明显,余华想用生命的死亡来印证现实的悲剧性、荒诞感和社会的不公,以此来表达忧国之思,但是国家的疼痛是不是仅限于这样的社会困境,是不是个体必须具有这样的“国家主义”?那些被文本重新编写的新闻事件是不是能折射和代表怪异的现实?看起来过于自信的余华,其实是过于慵懒,《兄弟》之后的七年酝酿和写作,对于这本13万字的小说而言,显然只能听到在时间逝去里的一种个体疼痛,它只属于余华,只属于“我个人的疼痛”,或者它和具体的文本无关,从《兄弟》开始,余华的蜕变实际上是彻底而无望的,关注现实并不一定要牺牲写作的深度,并不一定要用平面的语言来构筑,而用平面化、碎片化的新闻事件堆砌一种社会乱象,也并不能带来文本的真正变革,简单、粗糙,甚至有些媚俗的篇章构筑的是一个迷失的余华。
《第七天》,其实是“七天”,没有终点没有归宿,只有过程和罗列,“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的神在远处,在“第七天”之外,而“七年之痒”的文本实际上是将余华曾经的神话埋葬,不是死亡葬身之地,是它自己选择了坟墓,“那边的人知亲知疏,这里没有亲疏之分。那边人殓时要由亲人净身,这里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每一个都要给她净身。那边的人用碗舀水净身,我们这里双手合拢起来就是碗。”这或许也是余华式疼痛的最后注解,而短短两个小时的翻阅,也让我对余华文本的阅读划上了最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