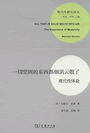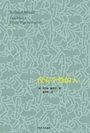|
编号:C38·2150822·1206 |
| 作者:【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29.00元亚马逊21.80元 | |
| ISBN:9787533937959 | |
| 页数:256页 |
巴黎,一种象征:幻想与现实,在寻找、探索,困惑、绝望中,“我就要重演《流动的盛宴》第一章开头的那个场景了。”《巴黎永无止境》是一部后现代版《流动的盛宴》,讲述了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故乡西班牙,为追寻成为新一代海明威的美丽梦想而蛰居巴黎,专心从事第一部小说创作的艰辛历程,以及他在巴黎与许多著名作家、知识分子、演艺圈名人、艺术家和普通老百姓接触交往的种种逸事和生活经历。在这场美味而有趣的宴会上,你会遇见杜拉斯、罗兰·巴尔特、海明威、贝克特,当然,还有马塔斯自己,本书形式新颖,以举办讲座的形式,利用闪回跳跃的手法,妙趣横生,并加入了大量对生活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点滴思考与入微分析,引人思索。
《巴黎永无止境》:讽刺就是离开自我
流放者,你将离去,没有眼泪,没有坟墓。
你将在消失的时光附近漫游,从那儿
到更远,奔向天涯。
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
方向朝着喀耳刻,死亡的美女。
你就在那儿静静地超越
没有太阳的城市,你会见到我。
我将是那艘失事的破船,
搁浅在徒有虚名的
朋友的海滩上。
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对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来说,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坟墓”的地方,是没有太阳的城市,甚至只是在一首诗歌的某个诗行里,可是当巴黎在某一个夜晚被激活的时候,那些眼泪便成为痛苦的象征,那些坟墓成为暴力的符号。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一个黑色星期五的夜晚,那罪恶的枪声和爆炸声响起在塞纳河畔,响起在球场、剧场里,100多个生命似乎就在狂欢和愉悦中,被冰冷的子弹穿透了无辜的身体,整个巴黎宛如“一艘失事的破船”,搁浅在死亡的海滩上。
一个巴黎,另一个巴黎,小说中的巴黎,新闻中的巴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书写的巴黎,我看见的巴黎,他们仿佛都在一种书写和传说中成为现实,但是在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如何对那些流放者和遇难者说起绝望,如何对那些暴力的实施者说起谴责,如何在小说和诗歌里遗忘悲剧?当巴黎的那个暴力夜晚被打开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从现实走向了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中,甚至把这一首关于告别的诗歌当成巴黎最后的文本,“我认为我写整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放进一首诗,就一首诗;那是我一生写的最后一首诗,也是出版的唯一的一首诗。”但是那不是最后的巴黎,不是关于巴黎最后的文本,当我读到“整整六天,我一直在分析形势,到了第七天,我就回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巴黎还是陌生的,当我继续读到“当父亲问起我为什么回到故乡的时候,我对他说是因为我爱上了胡利塔·格劳,另外还因为巴黎总在下雨,天气寒冷,晴天太少,雾天太多”的时候,巴黎还是一个传说,当我最后读到“而且那么平庸灰暗,母亲这时插嘴道,我猜她是在说我”的时候,巴黎在最后的句子里被合拢。
一本小说无法虚构一个陌生的巴黎,一条新闻无法还原一个暴力世界中的巴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告别巴黎,而我则打开了真实的巴黎,从文本到现实,从流浪到死亡,从绝望到恐怖,巴黎如此接近我们的生存,就像在身边,有眼泪,有坟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说:“书中隐藏的情节就是一出无声的悲剧:年轻人告别了诗歌,向粗俗的叙事低头。”但是当诗歌淹没在枪声中的时候,谁真正看见了死亡,真正看见了悲剧?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什么要把诗歌作为向美好的想象告别的符号,为什么会在《知识女杀手》中寻找到让读者死亡的方法,为什么在苦苦寻觅之后又返回到当初离开时的巴塞罗那?巴黎永无止境,巴黎就在不断地创造和解构中,巴黎永远在流亡者的想象中,“我离开这儿是为了消解、分离、崩溃,把一切未遂的人格或意识和任何对巴黎的怀念都变成碎屑。归根结底,讽刺就是离开自我。”可是离开自我,只是另一个不真实的巴黎,《知识女杀手》其实是无数个杀手,是文本里的杀手,是现实中的杀手,是新闻中的杀手。
合拢一部小说,打开一个世界,巴黎其实只是一个代名词,关于人类的悲剧,关于宗教信仰,关于种族和战争,即使不在巴黎,也会在历史的另一个时间点发生,在没有杀死知识女杀手之前,一切的解救都只是一种文本的游戏,所以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要用一首诗歌解构对巴黎的怀念时,枪声响了,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要用一部小说重建一个被书写的巴黎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我写作是为了不自杀。”那些高级法语,那些文化和知识,那些写作风格,那些和巴黎有关的作家、作品,到底会虚构一个怎样的巴黎?而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似乎也并不是那个西班牙作家,他是我,是躲到巴黎的一个流浪者,“我知道得不多,有时候只知道自己是个有两副假眼镜和一个烟斗的西班牙人,一个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生活的加泰罗尼亚青年,一个如果阅读路易斯·塞努达就变成共和派的作家,一个随遇而安、远离故乡、没有欲望的年轻人,这个人居住在一个恰恰不是流动的盛宴的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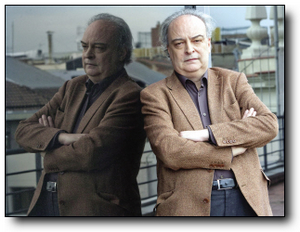 |
|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作者,也是读者 |
为什么要寻找巴黎,为什么要抵达巴黎?寻找是为了告别,抵达是为了离开,西班牙,和弗朗哥有关的西班牙,和独裁有关的西班牙,而我来到巴黎,就是为了在文本的世界里制造另一个谜语,制造一个流浪的虚构故事,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连自己都否定的人,“多年来,我一直力图成为一个最神秘、最不可预见、最深不可测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力图成为所有人眼中的一个谜。”自己编织一个谜,谜面写在小说里,而谜底永远不是为了告诉生活的真正出路,而是在绝望中讽刺自己,“我就是这类人之一,因为我不清楚生活之路在何方。”
不清楚路在何方,却选择了巴黎,这就是一个存在的悖论。我期待自己成为海明威,参加“谁最像海明烕”竞赛,不是向自己的偶像致敬,而是在偶像开启的巴黎“流动的盛宴”中解构巴黎,“结果得了个倒数第一名,说得更确切些,是被取消了资格。”这是悖论的开始,而巴黎只不过是一个贫困和不幸的地方,和妻子在巴黎呆了八个月,对于我来说,就是在永无止境的巴黎中找到一个终点,一个想象的终点,一个虚构的终点,一个流亡的终点。
“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现在我这样想。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巴黎永远不会结束,她始终在陪伴着我,追随着我,她就是我的青春。”巴黎是海明威的巴黎,是普鲁斯特的巴黎,是珍妮·还布特的巴黎,是佩雷克的巴黎,是马格利特·杜拉斯的巴黎,我或者见过他们,或者读过他们的著作,所以在那个阁楼里,在那条街上,在那个酒吧里,我似乎在还原那些作家和作品有关的巴黎,而我也慢慢进入到他们已经完成却永远有读者阅读的作品中。我是文本里的一个人,一个符号,一段文字,一个讽刺,是的,进入文本中的巴黎,和进入现实中的巴黎,到底有何区别?珍妮·海布特自杀字那条米奥特大街8号,而我在重读她的故事之后,去寻找那条大街,才发现,“这座城市到处都挂满了纪念性的金属牌,但是,在珍妮·海布特失去生命的地方却没有任何金属牌。”
只是在故事里,没有金属牌,没有标识,当然也被取消了意义,讽刺之一种,寻找只不过是一个瞬间,“过去不仅仅是一个瞬间,它其实根本不会离开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巴黎也是这样,“它从未外出旅行过,而且总是永无止境,永无终结。”不停留在某条街上,不停留在某个故事里,我对于巴黎仿佛陷入在虚无之中。而唯有这样一种悖论,这样一种讽刺,才让我更觉到保持一个没有谜底的谜面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是抵达神话的另一个高度。对于讽刺,里尔克说:“你要占据最深处,那儿讽刺不会再往下。”勒纳尔说:“讽刺是人类之廉耻。”而我则说:“讽刺乃真诚之最高形式。”
似乎只有自我讽刺,才可以看见真诚,也似乎只有自我讽刺,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永久的谜。所以从文本到文本,我开始写作,像一个作家那样,写作有关巴黎的书,写作一个讽刺的文本。从乌纳穆诺的一本书中找到了故事情节,在圣贝努瓦街5号六层的阁楼里开始创作,《知识女杀手》是一部可以用小说杀死读者的书,曾经我是他们的读者,我是巴黎的读者,而现在当我在没有任何金属牌的现实里接近讽刺的中心时,我要把更多的人当成读者,让更多的人被折磨,最后在“读完它后的几秒钟内死去”。
离开弗朗哥统治的西班牙,来到流动盛宴的巴黎,离开家乡的巴塞罗那,来到文本里的巴黎,“是过定居生活还是过移徙生活,是做个陈腐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做一个灵魂流浪人物”,而这样的选择根本不是生活的目的,甚至这样的选择也不是现实:“现实真的存在吗?真的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真实的东西吗?”就像曾经到达纽约的那个唯一的夜晚,当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饭店的房间里的时候,箱子还没有打开,窗外的摩天大楼就变成了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无非是一个梦境,我是在这样一种梦境之中抓住了所谓的真实。而这无非是另一种讽刺,一种对于现实的讽刺,对于梦境的讽刺,甚至可以说,我写作了小说,可是还只是一个读者,一个把巴黎之外观望的读者。
《知识女杀手》里的两个作家,或者正是和我有关的两个身份,一个是有社会地位的作家胡安·埃雷拉,另一个是非常糟糕的作家韦达·埃斯卡比亚,胡安·埃雷拉像是极权主义者,对于混乱无序的秩序进行着冲击,而韦达·埃斯卡比亚却生活在这样的混乱中,所以两个作家,一个是另一个的读者,一个是另一个的讽刺对象,“对于说真话而言,我看不出还有什么方法比讽刺我们自身更可靠。”我感觉自己和韦达·埃斯卡比亚是同类,却必须接受胡安·埃雷拉的极权秩序,所以在这样一个本身就带着讽刺和悖论的文本里,那些读后死去的读者就是我自己,我创造小说,我也毁灭小说。当韦达·埃斯卡比亚在小说中,死在女杀手发现的666号房间,而我从马拉加飞往巴塞罗那的时候,乘坐的飞机航班就是JKK666航班,666是一个咒语,也是一个讽刺,“他们怎么敢给飞机编一魔鬼的号码?里面有一个魔鬼相仿的年轻人”,我就在小说中被置入自己的命运中,“那我肯定以为自己是个死人了”。
绝望,迷局,小说和现实,不是巧合,而在故事的女杀手之外,我更是遇到了真正的女杀手,那个身材肥胖、酗酒成性、放弃了信仰的基姬曾经是我的最爱,但后来却变成了我的无形负担,就如塞万提斯的那句话一样:“没有一种比轻佻的女人更沉重的负担了。”把一个现实中的“女杀手”移植到小说中,成为小说的讲述者,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讽刺,所以对于这巨大的现实,我只能以一种搁笔的方式拒绝讽刺。搁笔是把文本抛向虚无,是把读者带向流亡,海明威用他那把双通猎枪结束了自己的创作,死前最后一部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有一段祈祷说:“我们的虚无存在于虚无中,虚无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也是虚无,你是虚无中的虚无,因为虚无原本就是虚无。”而阁楼上的杜拉斯,也选择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拒绝写作,据说,在弥留之际,她说死亡之后一切都变成虚无缥缈,“唯有活着的人在微笑,在互相支持。”
而对于我,剩下的是什么?是一个没有金属牌的街道,是被诅咒般的666航班,是被取消了资格的海明威模仿大赛?似乎还残留着某一个关于巴黎的梦,据说梦境是真实的,可是梦里最后是一本把我载入史册的书,而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大片目的,“大多数墓碑上,那些被五花八门的方式冷嘲热讽的名字已经模糊得无法辨认了。”还有另一个梦,“我梦见我的母亲是我非常年轻的姐姐,我跟她发生了乱伦之事。”巴黎脱离文本,成为一个梦,现实带来讽刺,却走向一种死亡,我是那些文本的读者,我也是现实的读者,巴黎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废话,巴黎是母亲“可你在巴黎到底找到什么了”的疑问,巴黎是佩特拉给我秘而不宣的刺激,巴黎是我写的那封“和阿尔蒂尔·兰波在1870年4月29日写给泰奥多尔·德邦维尔的一模一样的信”,巴黎是我和妻子以激情的方式“解放里茨饭店的酒窖”。
而《知识女杀手》呢,在那八页描写一个诗人之死之后就已经走向了结局,我放弃诗歌,走向罪恶的散文,就如我放弃讽刺,走向真实自我一样,“酒从他的双耳中流出来,他的双腿拖在地上,仿佛两根不会打弯的直挺挺的桅杆……”第八页的死亡是小说的死亡,新的文本的第一句话是:“我爱阳光、沙滩和带着咸味的海水。”死亡和暴力被终止,阳光和海水被扩散到现实里,而那些读者会重新聚集,会重新阅读。而这个被改变的文本无非是一个我早就安排好的计划,就像《巴黎永无止境》是一部小说,也是一个讲座,只是在巴黎的那个航班上,我把这一个讲座看成了别人的东西,“在我的座位第七排B座上发现了几页被人遗忘的笔记。”是的,在小说之外,那个持续三天、分三场、每场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我只是一个在座位上看见了讲稿,骂别人是傻瓜的读者。
“我是讲座还是小说?上帝呀,这是什么问题呀!”讲座和小说,都在读者的世界里成为一个讽刺,而读者当初就是应该在文本里死去的人,建构是为了解构,巴黎从来就是一个无限接近又必须离开的地方,它在那些作家和作品中,在我八个月和两年的游历中,在我成为一个作家的文本里,但如此种种,都是一种充满讽刺的“如果”:
我心想,如果我是个真正的作家,就不会有那么多棘手的问题。
我心想,如果我成为真正的作家,非洲将是我的。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将像兰波一样尝试创办所有的聚会,取得所有的成功,编写所有的剧本,试图发明新的鲜花,发现新的星球,创造新的肉类、新的语言。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将绝对是现代人;沐浴着曙光,带着火热的耐心,我将走进富丽华美的城市。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的日子将会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
巴黎在消解,巴黎被分离,巴黎在崩溃,当我“把一切未遂的人格或意识和任何对巴黎的怀念都变成碎屑”的时候,真正的讽刺就变成了离开自我,离开自我是杜拉斯的封闭,是海明威的自杀,是我回到巴塞罗那被母亲笑话,可是毕竟是离开,没有如果,没有梦境,没有读者,没有讲座,甚至没有666航班,没有警察,没有金属牌,没有阁楼,“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
可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文本意义上的告别和离开,夜晚的小说在最后一句话之后让读者活着,可是那遥远的、从未抵达的巴黎,谁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射出了冰冷的子弹,“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巴黎永远不会结束”,流动的盛宴其实是流动的罪恶,流动的讽刺,流动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