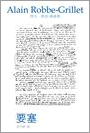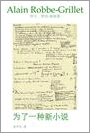 |
编号:H39·2160517·1304 |
| 作者:【法】阿兰·罗伯-格里耶 著 | |
|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06月第一版 | |
| 定价:19.00元亚马逊11.40元 | |
| ISBN:9787540449551 | |
| 页数:198页 |
“如果我故意在许多页里用了新小说这个字眼,这并不是为了指一个流派,甚至也不是指由在相同意义上工作的作家们所指定和组成的群体;它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包含了所有探寻新的小说形式、能够表达(或创造)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的人,所有决心创造小说也就是创造人的人。”阿兰·罗伯-格里耶用“新小说”作为自己构建世界的标签,仅仅是为了表达需要,而在他看来,这种“当代文学中的关键”是为了反对刻板和重复,因为,“它让我们在当前的世界里对我们的真实状况闭起眼睛,最终是阻止我们去构建明日的世界和人类。”所以为了探索和实验,“为了一种新小说”,其最终的指向是那些“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的人”,那些“创造人的人”。本书是罗伯-格里耶1963年结集出版的理论文集,收入论文8篇,分别讨论了新小说、形式与内容、人本主义等等,还分析了鲁塞尔、贝克特和潘热等人的作品。
《为了一种新小说》:它存在着,仅此而已
“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过。”哈姆说。面对着这一招认,再没有任何东西可算数了,因为,根本不可能听到他说别样的话,他只有在最一般化的形式下这样说: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在那里过。
——《一部现代文选的因素》
哈姆在说,哈姆在招认,唯一的线索,唯一的言说,而那句话里的“我”也成了唯一的人,当一切以独白的方式出现的时候,我所看见的一切,所指认的一切,都不提供任何背景,“一无是处的时刻,永远一无是处。”在一无是处的世界里,哈姆消灭的是背景,消灭的是可能,消灭的是介入——如果一个读者,一个观众以自己的思考介入这个《结局》的时候,是不是取代了哈姆的唯一性,取代了独白中的“我”?
贝克特的《结局》是关于戏剧的结局,是关于小说的结局,是关于我之存在的结局,“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过”是一种唯一的否定,而这种唯一性是另一种肯定:“没有我,一切依然发生……”也就是说,我之存在和我之不存在只是事物的两个面,它们都趋向于一种客观的表达:“所有存在着的都在这里,在舞台之外,只有空无,只有非存在。”就像贝克特的另一部作品《等待戈多》,迪迪和戈戈在舞台上等待的到底是谁?戈多是上帝?是死亡?是沉默?那一系列的问号无非是观众和读者做出的解释,而事实上,他们只是等待,他们只是在那里,“他们在舞台上”。
《萨缪尔·贝克特或舞台上的在场》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在1953年和1957年阅读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罗伯-格里耶也是作品的读者和观众,他坐在台下观看《等待戈多》,坐在房间里阅读《结局》,但是他在贝克特的文字里并没有看见戈多,而是看见了在舞台上的迪迪和戈戈,看见了“存在着”的他们,三个小时的戏剧,空洞的戏剧,空白的戏剧,以及没有停顿的戏剧,实际上只有看见的部分,而没有等待的部分,所以取消“等待戈多”的隐喻意义上,罗伯-格里耶认为,自己作为一个阅读者与贝克特一起“在场”,与迪迪、戈戈一起“在场”,和哈姆一起独白。
《一部现代文选的因素》里,罗伯-格里耶选择了雷蒙·鲁塞尔、泽诺、若埃·布斯、萨缪尔·贝克特、凯罗贝尔·潘热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解读中,他看见的是雷蒙·鲁塞尔“向着无限延伸”的浑浊性,看见了泽诺“对人的原罪的模糊讽喻”的病态意识,看见了若埃·布斯凯需要拯救的关于人自身的符号,看见了萨缪尔·贝克特在舞台上的在场,看见了罗贝尔·潘热创造出“他自身的现实”。而不管是世界的浑浊性、病态的意识、梦境里的自己,舞台上的在场、自身的现实,看见的同时,也是处在否定状态的“看不见”里,也就是说,在这些现代文选里,罗伯-格里耶在文本里否定了和传统有关的符号,却又以肯定的方式指向了另一个方向,那就是他为之实践的新小说。
“空无的疑谜,停止的时间,拒绝意义的符号,微小细节的巨幅增大,封闭于自身中的叙述,我们处在一种平面的和中断的宇宙中,在其中,任何东西都复归于它自身。”这像是罗伯-格里耶的一次宣言,当他的《橡皮》和《窥视者》出版之后,遭遇的是质疑,甚至是拒绝:为什么小说要这样写?它们的意义何在?里面的隐喻指向何处,人物起到了什么作用?而这些质疑在罗伯-格里耶看来,是因为背后有一套传统的标准,有小说的“本质”:人物、氛围、形式、内容、信息,在那些真正的小说家那里,在具有“叙述者才华”中,它们才成为真正的小说。这是一张早就织好的蜘蛛网,代表了小说现成的概念,而这样的概念在罗伯-格里耶看来,是“死的概念”,“在今天,惟一流行着的小说观,实际上还是巴尔扎克的小说观。”所以在1957年的《关于某些过时的定义》中,罗伯-格里耶梳理了关于小说人物、故事、介入方式、形式和内容上过时的定义。过去的伟大小说,人物必须一方面是唯一的,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类型的高度;小说的存在根本,就是把所讲述的故事当成内在的东西,而故事就是把“他在预先制作的草稿中、人们都习惯的东西,就是说,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既成概念,全都集中到一起”。于是,文学的介入作用是教育,是道德,是人和世界的搏斗,所以文学忌讳形式主义,它的内容必须是“有责任的”,有效用的。
而在罗伯-格里耶那里,这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在他看来,人物的个性和普遍性只是一种专一崇拜,故事并不能赋予小说家以力量,文学的教育介入方式是虚假的意识形态神话,而文字具有的责任性只是一种奴役,这些都是“过时的定义”,它需要的是一种新的阐释,所以罗伯-格里耶认为,人物具有的专一崇拜要让位于“一种更宽泛的、更非人类中心论的意识”,赋予作家力量的不是讲故事的方式,而是自由自在虚构的能力,介入的意义不是政治上的性质,而是“从内部解决它们的愿望”,而形式和内容的真正意义是“内在的必要性”:“我几乎就想写下它的不可能——就在于此:作品应该令人感到是必要的,但必要于乌有;它的建筑是没有用处白的;它的力量是一种无用的力量。”
抛弃过时的定义,建设新的小说观,就如罗伯-格里耶的小说被命名为“新小说”一样,它就是一种否定之后的肯定,一种传统之外的创新,一种解构之后的建构,“新小说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探索”,在他看来,文学本身就是活的,所以小说的新正是“跟踪小说体裁的一种持恒发展”的内在要求,福楼拜1860年的小说在当时是新小说,普鲁斯特在1910年的小说在当时也是新小说,“作家应该骄傲地接受带上他自己的日期,要知道,没有在永恒中的杰作,只有在历史中的作品;作品只有当它们把往昔留在了身后并预告了未来时,才能留存下去。”过时的定义是一种历史叙事,而小说只有在自己的日期里才能变成现在意义上的“伟大的小说”。
这是时间意义上的新,或者只是在历史序列中呈现的一种发展态势,但是罗伯-格里耶显然不只是让自己戴上属于自己的日期,而是“应该创造他特有的形式”:“作品只为它自己创造它自身的规律。写作的运动仍然应该常常引导着把这些规律带人危险,或者带入失败,使它们破裂。”把传统带入危险,带入失败,带入破裂,是为了打破规则,打破秩序,而破的下一个动作便是立:新小说只对人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感兴趣、新小说只追求一种彻底的主观性、新小说并不提出现成的意义。
新小说是新人,新小说是新的形式,新小说是新的文本,而所有的新在罗伯-格里耶那里集合在一个关键词之下,那就是客观性。客观性是什么,神学意义上是上帝的客观性,而传统意义上是和主观心灵相对应的客观性,而在通常意义上,客观性又变成一种“目光的彻底无个性”,而罗伯-格里耶的客观性是关于物的本来状态,是关于人存在的方式,是取消形而上意义的命名,“它存在着,仅此而已。”它从我们舒服的内心拉出来,它呈现在世界的舞台上,它被看见,被感知,在自己的现实里。比如在一部电影里,人们看见了椅子、手的移动、栅栏的形状,但是在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在思维的构建中,总是会想到这些东西背后的意义:“无人占据的椅子不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缺席或者一种等待;放在肩膀上的手,只是同情的标志;窗户上的栅栏条只表示外出的不可能……”而其实,这些意义是“额外的条件”,甚至是多余的,因为就在舞台上,就在小说中,它们只是物体本身,只是动作本身,只是形象“让它们恢复了它们的现实”。
那些额外的条件,那些背后的意义,罗伯-格里耶认为这是一种关于“深刻”的古老神话,这种神话总是在我们的精神和世界之间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总是希望用艺术的方式去完成它的使命,总是探寻文本背后的意义,这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观点,像是架在人与事物之间的真正的心灵之桥,首先是一种相互关联的保证。”但实际上,这样一种对世界的主观认识,选择人作为一切的证明者,只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中心,世界只不过是人类主观中的世界,所以罗伯-格里耶说,假如说出“世界,就是人”,那么就会得到赦免,假如说“事物就是事物,而人只是人”,就会立即被认为犯有“反人类罪”。
这当然是一种束缚,一种占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统治,在这样的体系里,隐喻被表达,意义被构建,人如上帝一样,把世界当成是主观创造的东西。这是深刻的古老神话,而其实,在罗伯-格里耶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甚至只是一种虚伪,“这是一种颠倒,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种伪造。”当作者写下村庄“蜷卧”在山坳里的时候,“蜷卧”一词是具有感情色彩的,也表达了人主观世界,也就是把读者带入到了村庄假设的灵魂中,它变成了人的主观性外化的一个符号,由此,观众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观众,他自己也变成了村庄,“蜷卧”在那里。这是一个隐喻的世界,村庄为什么要“蜷卧”,它是害怕还是恐惧,它是孤独还是寂寞?而当观众从这个词语介入到文本里,也就开始了另一种隐喻的构建之路:“它把威严的情感传染给了我;接着,这一情感在我的心中发展,孕育出其他的情感来:然后,又轮到我把它们安到其他的物件上,甚至那些体积更为平庸的物件上。这样,世界会变成一个容器,包容下我对伟大的所有渴望,它将永远地成为这些渴望的形象和证明。”
还有雄伟、还有壮丽,还有英勇,还有高贵,还有傲慢,也就是说,这一切在读者之前就已经预定了,而读者看见这些,只不过站在了一个等待而缺席的位置上,甚至“这一忧愁就是我命中早已注定的”,命中注定,意味着它不是暂时的,不是偶然的,它是我们的摹本,又是我们的心,也就是说,“它令我们震惊,审判我们,又拯救我们。”而这一切,就是用人本主义消灭了自然本性,那村庄本来只是一个存在,那山坳也是一个存在,它只在文本里存在,它不带感情色彩,它无法进入人的内心,当然,更不没有审判和拯救的功能。
“但是,我要说,不。”罗伯-格里耶大声说出了这句话,人本主义否定自然本性,他却要否定人本主义,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否定关于深刻的古老神话,“人看着世界,世界却并不回敬他的目光。人看到了万物,他现在发现,他可以摆脱其他人以前给他签订的形而上学的契约,他可以同时摆脱奴役与恐惧。他可以……至少,总有一天,他将可以。”也就是说,人只是简单地看见世界,人和世界是简单的关系,拒绝把它们占为己有,拒绝和它们维持暧昧关系,拒绝提出任何要求,“他的目光满足于度量它们;同样,他的激情落在它们的表面上,却并不打算深入进去,因为那里头什么都没有,也并不假装丝毫的召唤,因为,它们是不会回答的。”
世界是直观的世界,人是客观的人,在世界和人之间没有意义,只有存在,“在未来的小说建筑中,动作和物体在成为某种东西之前,都将在那里;之后,它们还将在那里,坚实,不变,永远在场,仿佛嘲笑着它们的特有意义”,甚至连人的主观性也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因为只有彻底的主观性,才能摆脱和世界的认知关系,它是属于自己的。在这样的小说结构中,所有的物体都是自己内在世界里,所有的人物都在在场的时间里,拒绝意义,拒绝深刻,拒绝悲剧。
“它存在着,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存在的世界里,在这个人只是看见的世界里,罗伯-格里耶新小说的一切目的就在于它的在场,所以有了那些电影作品,有了那些直观的视觉艺术,而这一切的最终指向是:构建一个现实。现实不是现实主义,在这里,小说不提供编年史,不同共法律证词,不提供科学报告;在这里,海鸥只是出现在头脑中的海鸥,而不是去布勒塔尼海岸作了一次短暂的冬季旅行之后描写的海鸥;在这里,一切从空无出发,它能自行站立,不需要任何东西支撑;在这里,没有隐喻,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形而上学。既然是客观的,是真实的,为什么出现在文本里的侦探故事,会有自相矛盾的证词,会有不在场的证明,会有不断涌现的新线索?为什么人们在观看和阅读的时候,会感到离真实越来越远?罗伯-格里耶其实虚构一个谜团,正是为了激发对于真实的渴望:“它们可能掩盖着一个奥秘,或者暴露出它来,这些愚弄着整体的线索只有一个严肃的、显然的品质,那就是存在于此。”
新小说是文学发展的新形式,是人与世界建立的新关系,是文本世界里的新现实,而罗伯-格里耶也创造着一个新神话,在没有上帝,没有隐喻,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的存在,“而在我的书中则相反,是一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象,一个位于空间和时间中的人,受他的激情所限制,一个像你我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