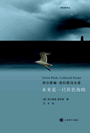 |
编号:S55·2140224·1059 |
| 作者:【美】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58.00元亚马逊45.80元 | |
| ISBN:9787532763191 | |
| 页数:416页 |
“今晚,温和的光芒如一件披肩盖着她,阴影俯身,如洗礼仪式的客人。”可是未来在哪里?在童年时父亲如鬼魅般的死亡面前,普拉斯似乎找寻到了痛苦之后的那种寄托,梦境般的飘渺,毫无顾忌地违抗所有的逻辑、因果乃至时空的束缚,解构众神与基督、圣哲与贞女,看似无可理喻,但这一幅幅荒谬、颠倒、时空倒错的画面所传达的焦虑、受挫与被压抑的欲望却是如此地令人心悸、过目难忘,这是任何悦目的色彩所无法企及的。普拉斯用诗句描绘的意象有的宏大荒寂,有的怪诞戏谑,但几乎都隐含着一种内敛的悲伤。这些悲伤是从一个悲伤的灵魂中自由流淌出的,这些悲伤也是童年故事的一次人生演绎——1963年,普拉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1981年,这位死去19年的女诗人被授予普利策诗歌奖,这在普利策奖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国内首部普拉斯诗歌全集译本,完整收录了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全部正式诗作。
一百万个新娘在泥屋子中尖叫。
有的烧一会儿,有的烧得久,
这群骄傲的女巫,全都绑在火刑柱上。
——《 名利场》
一场危险的通灵,一个嫉妒的眼角,不是从天上而来的女巫是不是看不见天堂,也不是撒旦之妻?只有燃烧能够触摸到火焰,触摸到黑暗王国里最邋遢的女人,只是在这尘世间,在打霜的阴霾天气里,女巫只是用一场持续的火焰照亮那些女人的肉体。这是一个消灭了肉欲和祷告的世界,她们是新娘,她们是处女,她们却在教堂的幻想中制造“一条条充满歧途的爱欲的面包”,甚至“愿意为一件小玩意/在蕨条床上浪费良宵”,而“肉体毫不忏悔”。而在这一场和宗教和救赎无关的爱欲表演中,“女巫放置足够多的镜子/以对抗处女的祷告,/使美人心意烦乱”,这是欲念驱使的虚荣,这是被俘虏的竞争,那屋子里只有尖叫,只有燃烧,只有女巫的骄傲,在火刑柱上变成女人的悲喜剧。
那些足够多的镜子是不是能照见一万个新娘的肉体,是不是能找到与天堂的连接?第一首情歌属于虚荣的女孩,而那只不过是邋遢的女人的最后幻想,但是那世界里是有垃圾堆的脑袋,是有长毛的空气,是有没有刀子的目光,还有偷走天空色彩的乌鸦——只有黑暗,只有聒噪,而在火刑柱上燃烧的时候,一切的幻想都成为祭奠,都成为不可逃避的灾难。女巫和女人,其实在一个镜子里,在燃烧着的黑夜里,她看见她,或者她看见她,就像地狱看见天堂,肉体看见圣洁。
这是1956年的《名利场》,这是西尔维娅·普拉斯光亮的起点,就在这一年,她与天才诗人泰德在教堂举行了婚礼,那是甜蜜的爱情,那是幸福的婚姻,“云朵驾驶抛光的气流;云雀升起,你追我赶/飞来赞美我的爱人。(《夏日之歌》)”浪漫的爱情是不是会像那些新娘一样在肉欲中遇见女巫,在火刑柱上听到尖叫?普拉斯似乎并没有幻想到七年之后的裂变和死亡,对于她来说,似乎在用诗歌回敬那只乌鸦,回敬一个垃圾堆的现实,回敬充满欲念的“名利场”,而在她面前的就是那一只只可以飞向未来的灰色海鸥。
这是一只“灰暗地盘旋于飞升的钢铁影子之下”的海鸥,叫声单薄,却可以用“亏损抵消了收益”;这是一只“驾着风的浪潮”一丝不苟的海鸥,在码头上完成一次伟大的登陆;这是一只在“最绿的光芒中沉思”的海鸥,像隐士一样“岩石脸与螃蟹爪紧靠绿色边缘”;这是一只“翅膀在冬季里击鼓”的海鸥,让我们在叫声中漫步于迷宫……是的,未来的灰色海鸥,“以猫的嗓音闲谈着离别,离别。/年龄与恐惧像护士一样看顾她,/一个溺水的人,抱怨这巨大的寒冷,/从大海中爬起。(《一生》)”看顾他的时间和消除掉的恐惧,一个溺水的人如何在巨大寒冷中从大海中爬起,是海鸥的叫声,是海鸥飞翔,是海鸥的希望,这构筑了“一生”的景象似乎在那无限的未来飞翔。可是,在《议会山郊外》,却有一个古老的难题,而那海鸥“在多风的弱光中守夜,寒冷而僵硬”,那种飞翔去了哪里,那种希望去了哪里,以及那一生的故事又在何处终结?而当“我走进点灯的房子”的时候,海鸥的世界其实是被无奈地舍弃了,寒冷而僵硬是不是那即刻到来的黑暗,是不可避免的灾难?
在普拉斯的意象里,不只有未来的灰色海鸥,还有“在冬夜的降临中忧思”的秃鼻鸦,有“刺穿并吸光/逃逸之心的最后一滴血”的伯劳鸟,有“女巫之布做的翅膀”的夜鹰,他们都是“名字好,名声不好,狡诈的夜鸟”,当然还有那反复出现的“乌鸦”,那“没有报出未来,/就飞走了”的乌鸦在未来之外,它只是在我的身旁,消除了对于天使的向往,用黑色的羽毛“攫住我的感官,拉开/我的眼皮,让我//从全然的中立性的恐惧中/获得短暂的解脱。(《雨天的黑鸦》)”我察觉不到天使的降临,一只乌鸦,一只在雨天的乌鸦侵入了我的世界,而我“等待那罕见的偶然的降临”却找不到了。
 |
| “我们走了这么远,结束了” |
这是一只乌鸦的寓言,这是一群鸟的寓言,而那海鸥在别处,在1956年的别处,在普拉斯浪漫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之外。对于普拉斯这样的敏感女人来说,对于爱情,对于女人自身总是充满着某种感怀,那是渴望的燃烧:“勇敢的爱人,别梦想/止住这般严厉的火焰,来吧,/紧靠我的伤口;燃烧吧,燃烧吧。(《火之歌》)”;那是婚礼上的花环:“说着这诺言,/让肉体交织吧,让每一步名声远扬。(《婚礼上的花环》)”那是被啃成了白骨依然有着“没有了法庭高于/人的一颗红心。(《幽魂与神父的对话》)”的向往……而这些美好的事物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却并非是火焰,并非是激情,并非是花环,两个恋人躺了一个下午,却在各自的路上行走:“现在他偏离了正确的道路,/荣誉要求他此刻离开;/而她站着,灼烧着,浑身流淌着毒液,/等待尖锐的剧痛消退。(《田园诗》)”两个人的对立已经不是在田园诗的世界里,他和她,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
他俩整天躺在带刺荨麻的隐蔽处,
剪过的草带着愉悦攻击每个
感官;如此结合乃忠诚的典范,
双方战争中,他俩寻求一致状态。
现在口说誓言,打消疑虑,
在爱的教堂内造就婚姻。
——《另外两人》
他是想伸出手去靠近她,但是她却避开他的触摸,他们站着,“伤感如古老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并非只属于两个人,并非只属于他们,在他们之外还有我们,还有可以拥抱的我们,还有成了幽灵的我们,“仿佛我们超脱了爱的废墟/成为他俩在绝望中梦想的天堂。”是的,我们站在他们对面,用超脱爱的废墟的方式营造一个梦想的天堂,可是这是最终的归宿,还是只是在他俩的绝望中的臆想?他们躺了一个下午,他们各自走开,爱情没有标本,也没有想象,即使她是“傲慢地召唤所有的强悍男人”的皇后,也依然找不到与她的睡梦相吻合的形状,依然没有配得上她闪亮的王冠的男人,只有怨言,只有标本,就像那一具在剑桥考古博物馆石棺里的女尸一样,在变成了一个符号,伴随着老鼠,“女人的踝骨被轻微地咬坏”,符号后面却是所有女人的集体征象:“所有逝去已久的爱人:他们/回来了,尽管,一会儿/就一会儿:借着守灵,婚礼,/生孩子或家庭烧烤:/任何触摸,味道,气味/足以让那些法外之徒纵马返家,/回到庇护所(《所有死去的爱人》)”男人们回来了,守着魂灵、婚礼和生孩子的生活,回到了庇护所,但是爱人却已经死去,她们是母亲、祖母、曾祖母,而她们也“伸出女巫之手欲将我拖人”,使我也变成其中一员,变成逝去的女人。在这样的肉体死亡面前,男人们称颂的女皇也变成了腐臭的尸体,变成淫荡的死亡女皇,“虫子般的信使开始啃他骨头。/他仍赞颂她的汁液,火热的蜜桃。(《占卜板》)”
不管是女皇式的死亡,还是爱情中“他们”的冷漠,在普拉斯的诗歌世界里,永远有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是一群女人,是她们,是“每个男人,/红润、苍白或黑肤,/皆转向懒散的”的妓女,是“竖立/这般带钩的防御工事”的未婚女子,是“将其肢体与嘴唇献给/贞洁的事业”的树上的处女,是“想象自己有一大批观众”的不孕的女人,是“消耗自身——身体”的寡妇……而每一个女人的背后都有着有关肉体与救赎,爱情与背叛的道德命题,妓女对应于“贞洁的双眼”,未婚女子对应于造反的男人,处女对应于爱欲之箭,寡妇对应于“迟钝的器官”,在一个女人世界里,她们被放逐被评判被当成男人的征服者,肉体和精神也被截然分开成两个世界,在《耳塞福涅两姐妹》里,一个是自愿成为太阳的新娘:“迅速孕育种子。/骄傲地分娩,躺卧草丛中,/她生下一个帝王。”而另一个,则是“直到最后还是苦涩的处女”:“向坟墓走去,肉体被浪费,/嫁给蛆虫,仍算不上女人。”如何算作女人,如何是自己成为女人?分娩或者帝王的荣光,还是坟墓里的死亡,肉体嫁给蛆虫,荣耀者或者腐烂者,对于女人来说,这是命运的两面,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女人的某种和身份有关的宿命:“据村里传说,埃拉从前/活蹦乱跳,一个瘦削而傲慢的风骚女郎,/一个时髦美女,/用碧色眼神杀死纨绔公子;/现在,她发胖成老处女,关门闭户,/只放猫出入。(《埃拉·梅森和她的十一只猫》)”
从风骚女郎、时髦美女,变成老处女,变成养猫的孤独女人,埃拉的象征意义就是女人在时间、在生命过程中的悲剧意义,而这样的悲剧对于普拉斯来说,则完全是对于自身命运的关注,自我是什么?从爱情或者婚姻的假想和生活中退居到自我的关照,普拉斯依旧用她黑色的意象、诡异的语言来构筑一个陌生的世界,“我看不见未来与过去。/我梦见我是俄狄浦斯。”那里面分明是一种渎神,一种毁灭般的激情:“我想要找回的,/是病床与手术刀之前的我,/是胸针与药膏将我固定入/这个括号之前的我;/风中飘扬的群马,/一个记忆之外的地点与时间。(《眼里的尘埃》)”找回自我,却已经是动了手术的我,是被消除了括号的我,我自己成为猥琐、悲伤的人,成了“在一堆骷髅中感觉自在”的我,成了是“根,石头,打猫头鹰的弹丸,/什么梦也没有。”的我,在这个有着阴暗的房子、酒神的女祭司,有着野兽、来自芦苇池塘的笛声,有着焚烧女巫和石头的生日里,“我正变成另一个人”,但却不是死,而是“更完全的事情”,因为“翅膀的神话再也不拉扯我们了”,因为在“地狱过后:我看见了光”,在疼痛和迷失之后是独自修补,“十根手指形成一个盛阴影的碗。/我的缝补处发痒。无事可做。/我将完好如新。”
完好如新的自己如何可能?在这个有着“荒唐而离奇”的纯粹主义者,有着“证明肉体的真实”的唯我论者,有着“食物橱被洗劫得只剩骨头”的贪吃者,有着“要有蛇!/于是就有蛇”的耍蛇人,甚至还有着“以一种背信弃义的生命力/使怜悯的黑眼睛困惑”的乞丐,在这个没有英雄,没有神话的世界里,只有卑微的存在,只有肉体的泯灭:“死者或某位神灵的代言人。/三十年了,现在我费力地/清理你喉咙里的淤泥。/我没有变得更高明。(《巨像》)”那只不过是一种和女皇一样的仪式,一种更加悲剧的符号,而实际上,“你也许自以为是神谕者”,这个世界只是“码头了叫停/我们短暂的史诗,我们拿起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行李;/一切债务随抵达终止;我们与陌生人同下船板。(《穿越海峡》)”从这边到那边,从史诗到现实,从神谕者到自己的名字,一切都是一个“与陌生人同下船板”的过程,人生的大海,宛如一只巨大的浴缸,“浴缸在我们身后存在:/它闪光的表面空泛而真实”,而在这样的现实里,看见真实的世界多么难能可贵,“凭借信仰/我们登上想象的船,狂野地航行在/疯子的神圣岛屿之间,直到死亡/击碎传说中的星星,让我们回归真实。(《浴缸的故事》)”
渴望真实,真实的浴缸,真实的大海,以及真实的女人,真实的爱情,这是1956年《浴缸的故事》,但是大海也淹死一个少女,淹死那些鱼和海鸥,淹死真实,隐喻的世界已经慢慢打开:
我是一个九音节的谜语,
一头大象,一座笨重房子,
散步的甜瓜,两条卷须腿。
哦,红果子,象牙,好木材!
这面包被酵母搞大了。
这鼓胀钱包中,钱币是新铸的。
我是一个手段,舞台,奶牛犊。
我吃了一袋青苹果,
上了不能下站的列车。
——《隐喻》
九音节的谜语已经将我赶下了列车,赶下了船板,1962年的普拉斯从《达特穆尔的新年》开始,那里有罩着障碍物的玻璃,“那盲目、可怕、不可接近的白色斜坡。/你无法用熟悉的词攀登它。/无法借大象、轮子或鞋子来攀登。/我们只是来看看。你初来乍到/无法索取玻璃帽里的世界。”这个封闭的世界,只是来看看,而对于初来乍到者来说,却是一个不可接近的世界,圣徒的假嗓子在歌唱,而1962年的故事早就已经划入了可怕的深渊。普拉斯听到了妇产科医院里的那三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声音是“我已准备好。/我只对自己说话”,一个声音是“我正坐着死去。我失去一个维度。”第三个声音是“我早该谋杀那谋杀我的。”她,她,和她,组成了她们,疾病和死亡正在蔓延,那些伤口的绷带,那些冰冷的天使,那些脚下的影子,都在一个日渐封闭的世界里行走:“将我是一个妻子。/是在等待,疼痛。小草/石缝中进出,充满绿色的生机。”而这样的影子妻子却遭受着“被下了药,被强奸”的命运,却在想象着“上吊,饿死,焚烧,钩挂”等多种多样的死亡,面临着“我说我也许会回来。/你知道谎言的用处。”的现实。曾经是一个微笑的女人,现在是年仅三十的女人,曾经有过一场意外,现在仍是同一个女人,但最后却是“我披着红发/灰烬中复活/像吃空气一样吃人”的“拉撒路夫人”。那么爱情呢?那么婚姻呢?“一个白色小灵魂在摇晃,白色小蛆虫。/我的四肢也离我而去。/谁肢解了我们?”谁肢解了我们,谁又把我们带向一座封闭的玻璃?“我的风景是只没有纹路的手掌,/道路束成一个结,/这结就是我,//我的葬礼,/还有这山岗,和这/与尸体的嘴巴一起闪烁的东西。(《没有孩子的女人》)”没有纹路的手掌,是没有分叉的出路,还是没有具体的命运?葬礼已经在着身边,普拉斯一定听到了那喧闹的声音,那和尸体一样闪烁的东西,那是死亡,那是“没有星,没有父,黑暗的水”,那是坠落在水中的一只眼睛,而这只眼睛再也看不到这个温柔的世界,看不到这个心满意足的生活,“人一旦目睹上帝,还有何补救?/人一旦被抓走//什么也不剩,/没有脚趾,没有指头,用尽了,/完全用尽,在太阳的大火中,污点/从古老的大教堂延伸,/还有何补救?(《神秘主义者》)”
如何补救,其实普拉斯已经不想补救,那是寒冷的冬天,那是没有上帝的冬天,在菲茨罗伊路23号的公寓里,她听到了夜晚的声音,像以往每一首诗歌一样在召唤着没有回归的灵魂,或者像那一只灰色的海鸥,在无法抵达的未来飞翔。孩子在熟睡,而那个曾经亲爱的丈夫——英国桂冠诗人、同样才华横溢的泰德·休斯,却与另外一个女人共枕。分居4个月是普拉斯生命中最黑暗的诗,她将头放在煤气炉里,扭动那自杀的开关……而在这个黑色的死亡日子到来之前,普拉斯写下了她最后一首诗《边缘》:
这女人完美了。
她已死的躯体穿着完满的笑容,
希腊必然性的幻觉流淌在她长袍的卷涡中,
她赤裸的双脚似乎在说:
我们走了这么远,结束了。
走了这么远,结束了。这是生命的边缘哀叹,“她的身体如玫瑰的/花瓣合拢,当花园僵硬,/香气如血流出/自夜花那甜蜜而幽深的喉咙。”是啊,月亮没什么好悲哀的,死亡也没有什么好悲哀的,因为“她已习惯这种事。/她的黑色碎裂并拖曳。”远处没有海鸥的飞翔,天空是一个巨大的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