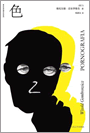 |
编号:C38·2140224·1061 |
| 作者:【波兰】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27.00元亚马逊18.80元 | |
| ISBN:9787020095025 | |
| 页数:274页 |
青春之美代表的是色欲还是爱情?或者所谓的爱情是不是可以通过设计而实现?两位年长的知识分子对于少女少男性吸引力的关注,使得他们尝试去唤醒他们,让他们彼此相爱,但是少男少女并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情感,为了让美好的情感变成现实,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深入窥探,与少年接近,并计划以共同完成的罪孽使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于是他们谋划了一场谋杀行动。“写作就是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个性和荣誉跟大众进行的—场战斗。”这是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写作观,而这场与色有关的战斗变成了一种戏谑搞笑的滑稽戏。时空设置在1943年,而这样的战争期间无关革命、国家、民族、斗争与牺牲,被米兰·昆德拉誉为“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的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或者只是想在小说里设置一场关于青春之美的战斗。
《色》:放在括号里的男孩和女孩
意思是要把这个姑娘卷进罪恶,卷进谋杀……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提议又是“令人迷醉、令人兴奋的”,因为要让他俩“在一起”……
——《色》第二部
一封信的计划,一出小岛的戏剧,一个人造的爱情,只是被冠以罪恶和谋杀的定语,必定是在她之外的,也必定在他之外,而这个姑娘和少年只是被我们看见,从此就被拉到“在一起”的世界里,卷进罪恶,卷进谋杀,然后看着那些关于,关于年轻,关于欲望的计划变得“令人迷醉、令人兴奋”,而当那把刀捅进身体里的时候,人造的领袖和人造的爱情之死就变成了一九四三年那个“既成事实的底层”被彻底肢解,只留下两具尸体的悲剧性残酷,留下血腥的事实,还留下两个杀手,两个把男孩和女孩放进括号里的轻率的行为。
这是不是战争的极端主义,这是不是疯狂的无神论行为,这是不是肮脏和癫疯的革命行动的一部分?“弗雷德里克、我、海妮亚、卡罗尔——像是一个奇异的、情色的组合,某种神秘而性感的四重奏。”不是自然而然的组合,是浸润着奇异和欲望的组合,在神秘和性感的特殊时期上演的一出悲剧,但这却是“最命中注定的一次”。“当时是一九四三年,我在昔日的波兰逗留,在昔日的华沙,在既成事实的底层。”这是我的故事,第一人称开始的故事,那个一九四三年的波兰只不过是想象中的波兰,和那些想象的情色,想象的欲望,想象的谋杀一样,故意放在一个适合战争氛围里展开的故事中,“在他们的胸襟中还蕴藏着其他的冲突、戏剧、思想。”他们是战争的主体,他们在我之外,却用另外一种冲突的方式压迫我,“而他人的躯体,蛮横的、侵袭成性的、压挤过来的躯体则加深了我和他躯体的接近”,所以在我的身边,有一个他,那个叫弗雷德里克的无神论者,接近,接近,最后成为一体,成为神秘而性感“四重奏”里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像一出反抗的戏剧,最后却以一把刀的方式让所有身边的人流血和死亡。
弗雷德里克也在脱离“他们”的集体戏剧,脱离关于民族、上帝、无产阶级、艺术的讨论,所以他是一个独自玩着自己游戏的人,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是安静却骨子里透着激进和疯狂思想的人,“是的,是个极端主义者!到了疯狂地步的极端!不不不,这不是普通的存在物,而是某种更具掠杀性的东西,而且浸透了我迄今毫不知晓的极端性!”在这个被扭曲的战争年代,在这个看上去暂时平安无事的地方,有一种无以摆脱的恐惧所笼罩,正如一起到达陌生地方时,希波利特说的那样:“先生,那就是杀人、作乱、抢劫!抢劫!”最糟糕的是,没有地方逃跑,所以弗雷德里克不是普通的存在物,极端而疯狂,而我也在这样的时代里感觉到救赎是一件无效的事,神甫会把抓走,弥撒只不过是某个人的一只手的含义,“而祭坛的侍应男孩们摇铃,燃香的轻烟升起,但是内容从中消失,就像气球里面的气跑光了一样,弥撒失散在可怕的阳痿之中……”没有救赎,只有恐慌和不安,似乎这个世界就只有自己一个人,极端的一个人,在绝对的黑暗中的一个人,所有的仪式只是走向一个苦涩的终点。所以当我和弗雷德里克到达希波利特的地方时,满脑子都是“令人不安、肮脏、有点疯癫,甚至富有挑战性、纠缠不清、有破坏作用”的思想,像是从弗雷德里克那儿传来,又像是一九四三年的“既成事实的底层”涌出的战争、革命、敌人的占领。
所以这地方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个制造和策划人生戏剧的地方。而那在括号里的男孩和女孩让我和弗雷德里克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美、年轻和欲望,深深触动了我们,以致在不停地想象中走向“令人迷醉、令人兴奋”的那一刻,走向要让他们在一起的结局。男孩是管家的儿子卡罗尔,女孩是希波利特的女儿海尼娅,当我进入希波利特的地方,“瞧着这盏灯和昆虫打圈子的王国”,我便小心翼翼地说:“多么好的一对啊!”卡罗尔参加过地下活动,在卢布林透过东西,还对着人开了枪,打了人,后来回家之后有和父亲作对,这种种的行为也是极端,也是疯狂,但是却注定带着“年轻”的特色:“他谦恭,因为年轻。他自卑,因为年轻。他感性,因为年轻。注重肉体,因为年轻。有破坏倾向,因为年轻。就因为年轻,所以受到藐视。”而这种种的年轻的破坏力正是我和弗雷德里克没有的,所以当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就在心里掠过那种相配的感觉,“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这好像是她的(女孩的)脖子奔跑出去和那个(男孩的)脖子会合了,这个脖子作为脖子被那个脖子抓住,而且是抓住了脖子!这些隐喻笨拙,恭请原谅。”括号里的男孩,括号里的女孩,仅仅是奔跑出去,便用脖子的那一块肉体会合在一起,笨拙的比喻全是想象,以致在我的观察中,他们完全是一对,完全可以在一起:“他是为了她,她是为了他,即使彼此离得很远,互相并不感兴趣——这一点也是十分强烈,以致他的嘴不仅和她的嘴相配,而且和她整个的肉体相配——而她的肉体是和他的双腿相配的。”
海妮亚竟然会给卡罗尔卷卷裤脚,这样的行为比我想象中的那种肉体的相配更具有诱惑力,仿佛是某种美,轻易抵达,而在这个许多污秽、压抑、羸弱、灰色和被疯狂地歪曲的年代里,只有尸体的气味,我几乎忘记了什么是美,是他们的偶然相配激活了我心中的美,以致那草丛和水沟成为我们“这个侦探故事的道具”,从而开始构筑他们在一起的爱情。而在美之外,是欲望,卡罗尔竟然跑过去掀起一个老婆子的裤子,看里面的东西,“一个扑向老婆子的半大小子的奇异魅力,这种魅力在我眼里还正在变得高大,虽然我还理解不了这股魅力。对老婆子的无礼行为怎么会给他披上这样的光鲜魅力呢?”这恶俗卑鄙的行为被我定义为充满了光鲜魅力的行为,是欲望的呈现,是赤裸裸地追求欲望。
年轻、美和欲望,这是我对于括号里的男孩和女孩的定义,而在这样的定义中,他们也必须从括号里走出来,在肉体和肉体的会合中在一起,实现令人迷醉和令人兴奋的目标,但是,他们是在自己封闭的圈子之内,“那种美只在相互的欲求和欣喜中”,也就是说,这是其他任何人没有权利参与其中的,他们是封闭的,是自足的。所以“把他俩拉进我们的欲望、我们对他们的幻想的范围之内”便成了我的欲望,弗雷德里克的欲望。但是这样的欲望显得一厢情愿,“你喜欢海妮亚吗?”问卡罗尔的答案是:“当然,我喜欢。”但是却是对爱情的否定,“不是……我们从小就认识……”而问海妮亚,“卡罗尔爱您。”她的回答是:“他?他不爱我,也不爱其他的女孩……他一心巴望的就是……找个人一块儿睡觉……”从小就认识是一种年轻有关的生活而已,“上帝把这个男孩和女人混淆起来了,所以他的‘太小’在我听起来奇怪,像一个警告似的。”是的,他没有成年,太年轻,对于海妮亚和已经生成的一切,是因为“太年轻”,对于我和弗雷德里克,也是“太年轻”,而这种稚嫩的年龄是不是只意味着去掀开老婆子的裤子寻找欲望?而海妮亚呢,说卡罗尔只是想找个人一块儿睡觉,而她也肯定不止和一个男孩水果,她不是圣女,而事实是去年她和留宿在家的国家军士兵有过经历。所有的种种似乎离我和弗雷德里克的想象越来越远,而剩下的只是我们对于年轻的阴暗和怪异的念头,卡罗尔和海妮亚共同踩死的只是一条蚯蚓,“我们踩死过多少虫子啊?不是啊,这算什么残酷嘛,更可以说是无意,无意中以儿童的眼睛看待小虫子在可笑的蜷曲中死了,感觉不到疼痛。真是琐事。”只不过是童年的游戏,无关疼痛,但是在弗雷德里克看来,却变成了“巨大的流血事件”,甚至变成了一种隐喻:“弗雷德里克的看法大概没有错:两个人一起踩碎瓦茨拉夫,通过瓦茨拉夫变得放荡,使他们大胆放开!他们为了瓦茨拉夫变成情人……为了自己变成情人。”
瓦茨拉夫是谁?是海妮亚的未婚夫,一个举止得体、颇有风度、不张扬、和蔼可亲、受过完美教育的律师,希波利特已经同意了他们的婚事,海妮亚也曾说过:“至少在嫁给他以后,我不会太随便的。”这是自我约束,而当她依偎在瓦茨列夫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冒出来的想法是“背叛”,下流的背叛,因为她“应该得到她忠诚的(男孩),却被抛到九霄云外”,这是如何一种颠覆,“这个景象折磨了我,似乎我的世界里最后一点的美都遭到践踏,受到死亡、折磨和暴力的摧毁。”被摧毁的想象,被摧毁的美、年轻和欲望,被摧毁的“在一起”,而卡罗尔也根本不在乎这个,“一切都沉没在他们年轻人视而不见的昏蒙里。这是我们美梦留下的废墟。”而对于瓦茨列夫呢,完全坚守着道德,履行着他的义务:“他全部的肉体文化完全不是产生于软弱,而只是某种原则,而且大概是道德原则的表现,所以他把这一文化当作自己对于他人的义务。”种种将我们抛到了成年人的地带,抛到了怪异而危险的世界。而更为怪异的是,瓦茨列夫的母亲阿梅丽亚竟然和弗雷德里克之间产生了相互接触的气息,“他仅仅注目于阿梅丽亚,确认她就是她那个样子。正是在她温暖的光线之中,这才变得僵尸般软弱无力。而他的无神论在她有神论的影响下正在生长,所以他俩已经被搅在这致命的矛盾中。”
无神论和有神论,极端和温暖,这到底是年轻世界的感染,还是成年欲望的激活?只是这不是爱情的接触在那场卢达凶杀案中变成了最后的审判,阿梅丽亚被尤泽科用刀捅伤,在垂死的时候,阿梅丽亚竟然避开的是十字架,而紧紧盯着弗雷德里克,而且在目光中集聚了力量,“但这不是爱情,这里涉及的是更具个人性质的因素,这个女人把他看成了审判者。”为什么要审判,是情欲带来的道德审判,还是对于无神论的审判,那个黑暗屋子里的凶杀案谁也不在场,尤泽科是不是没有拿起刀,而她却用手指摸到了那把刀,然后她扑过去,是反抗还是主动的疯狂?“她?凭她的圣徒气质?以她这一把年纪?她这样德高望重的?这是在厨娘和小长工那昏迷脑瓜里头滋生出来的幻想。”仿佛又是一次想象,那握在手上的十字架在刀子、死亡和鲜血在面前显得那么脆弱,“一个小房问的黑暗因为这些混入想象里的黑暗而加倍”,而剩下的也并非是弗雷德里克的难过,“她的死亡是在暧昧的状况下发生的,比乍看上去要暧昧得多……”而对于母亲的死,瓦茨拉夫的惧怕仅仅在于自己的平庸,而不是弗雷德里克的无神论,“因为这样的平庸把他变成了‘带着精致梳子’的律师。”律师不是在死亡面前的审判,审判只有自己的道德,所以瓦茨拉夫只是想要一个生活的解释:“您知道,实际上我是不信上帝的。我母亲信,我不信。但是我希望上帝存在。我希望——这比我深信上帝存在更重要。”
母亲死了,对于瓦茨拉夫来说,上帝也在慢慢地远去,而对于海妮亚的那场充满着欲望和道德矛盾的爱情,也在他心中逐渐远去。因为弗雷德里克在阿梅丽亚暧昧的死亡中彻底感受到了救赎的无能,成年的痛苦,以及被时代扭曲的极端在他身上变成了疯狂的实验,那条蚯蚓是一个巨大的流血事件,甚至在他看来变成了一场情色故事中的牺牲品:“那条蚯蚓就是瓦茨拉夫!他们在这条蚯蚓身上结合了。现在又在瓦茨拉夫身上结合。踩碎了瓦茨拉夫。”他的目标是,把瓦茨拉夫变成一张床,让卡罗尔和海妮亚在这张床上交配,用年轻、欲望和那种不存在的美亵渎童年的乐趣。
这是弗雷德里克的戏剧,他要和我一起导演这一出戏,因为在两个人的疯狂中他才感到踏实,再给我写信中,他用他的疯狂,用他神经质的欲望,用他的情色癫狂症来制造那人造的爱情,小岛、肉体、欲望,而这一切又要让瓦茨拉夫看见,要创造悲惨地搅和进去的另一种青春,“咱们,亲爱的维托尔德先生,咱们。他们必须通过咱们。所以他们才跟咱们调情!”而知道了小岛上事件的瓦茨拉夫找到了我,他说海妮亚爱他,而我反问:“爱您?这没有疑问。但是,您不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肤浅的吗?她需要您的爱情,不是他的。”我的答案是:肉体,而这无疑是打击了瓦茨拉夫:“我在思想上重建了他俩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他俩之间关系的整体。这真的是……亮丽的情色,我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扑在上面的!好像梦境!是他们俩谁想出来的?是他呢,还是她?如果是她的话,那她真是一个艺术家了!”这是绝望,这是讽刺的绝望,在这个人造的爱情面前,作为律师的瓦茨拉夫完全丧失了判断,“她不仅背叛了我。她背叛了男性。总体的男性。她对我不忠实,不把我当成年男人。那么,她是不是女人呢?嘿,我告诉您吧,她是在利用她还不是女人这个事实。”把这样的背叛也上升到了对于总体的男性,实际上他心中的那个拯救的上帝真的被毁灭了,不忠、背叛,其实只是一条蚯蚓被踩死的游戏而已,弗雷德里克和我放大了这个游戏,变成了一出无法逃逸的戏剧。
而这戏剧并非仅仅是情色的癫狂症,并非是人造的爱情,还有人造的领袖,这或许才是真正对于一九四三年的波兰,一个充满着革命、战争和占领时代的反抗,而那个骑兵队军官谢缅对这里所有人来说都带来了危险,而这种危险是我所熟悉的:“行动、地下活动、领袖、密谋——都好像来自一本拙劣的小说,像低俗的青年梦想得到了迟到的实现”,他常下命令,指挥众人,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那句“我可以要一小片柠檬吗”听上去和蔼悦耳,但是带着波兰东部的口音,“甚至有点俄罗斯语言的意味”,软中透硬的话剧实际上“标示出对他人之存在的不尊重”。谢缅作为骑兵对军官,他的话语他的行为完全带着战争的味道,带着侵略、谋杀的属性,所以在那场戏剧实验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谢缅的刺杀行为,谢缅这个威风凛凛的军官正转向已经丧失的权威,已经变成“危险的”形象,而最后刺杀谢缅落在了卡罗尔的身上:“这个少年藐视一切的性格和个领袖阴沉而威权的冷漠态度不谋而合——他们互相承认,因为都不怕死、不怕苦,前者因此是少年,后者因此是领袖。”少年也是反叛,也是冷漠,而与海妮亚的人造爱情恰好可以寻找到结合点:“热力渗人——死亡已经变得蕴含了爱情。一切——包括这次的死亡,我们的恐惧和厌恶,我们的无奈——之所以在那儿显现,都是为了让一只年轻且太年轻的手去抓住它……我已经浸沉其中,不是把它当作一次谋杀,而是浸沉在他们未成熟的、没有声音的肉体的某种自由奔放里。真是欢畅!”
这是成年人对年轻欲望的干涉,这是无神论者对于救赎的游戏,这是逃避者对于战争时代的反抗,“突然之间,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奔跑,弗雷德里克、我、希波利特,都奔向这个少年,好像奔跑着去夺取某种解除负担的神密炼金术似的。”神秘的炼金术,要踩死的那条蚯蚓变成了谢缅,或者变成了瓦茨拉夫和谢缅的结合体,“也一样是肉体的,罪恶的,因爱情而炽热,还有,他们的侵袭也是同样的紧张……”当整个计划在卡罗尔的手上变成现实,当那把刀捅向那个肉体的时候,人造的爱情和人造的领袖都同样被置于毁灭之中,只是最后的结局是反游戏的:“这不是谢缅……几秒钟之后大家才看出来,这是:瓦茨拉夫!”卡罗尔说“完了”的时候,那把刀其实在向着另一个方向刺下去,谢缅是被瓦茨拉夫刺杀的,而卡罗尔却刺死了过着头巾的瓦茨拉夫。
那把刀挑开了那个在括号里的男孩和女孩,那场死亡消灭了苦心经营的人造爱情和人造领袖,卷进罪恶,卷进谋杀的计划最后是律师之死,是未婚夫之死,想象的故事终于被轻率的行为刺穿,用一个鬼气十足的结局完成了战争中的实验戏剧:“我瞧了一眼我们这年轻的一对。他俩正在微笑。像很难摆脱某种困境的年轻人常见的那样。瞬间之内,在这一厄运中,他们和我们互相对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