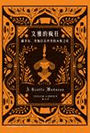 |
编号:E95·2141219·1139 |
| 作者:【美】尼古拉斯·A. 巴斯贝恩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69.00元亚马逊52.50元 | |
| ISBN:9787208124868 | |
| 页数:588页 |
副标题:“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这是关于20世纪西方书话的经典,是西方书话权威、殿堂级大师巴斯贝恩关于藏书的代表作,权威的《善本、写本的图书馆学》杂志1998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曾把它同曼古埃尔《阅读史》一起列为图书馆员必备书。古典时期《文雅的疯狂》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回顾历史上的著名藏书和书痴事迹,第二部分是用新闻纪实的体裁写的当代著名藏书家和书痴的访谈。在这部内容宏博、横跨古今、篇幅浩大、格局恢弘的作品中,巴斯贝恩讲述了2500年来100多位藏书雅痞,对书籍这一个世间最文雅精贵前赴后继的执意追逐,惊心动魄的珍本拍卖,叹为观止的奇闻怪谈,缠绵隽永的书情人事……激情与沧桑同行,文雅与疯狂共舞,只因人类对书籍永恒的爱恋。
《文雅的疯狂》:他本人就是一座藏书楼
“书癖太难以觉察,太容易感染,在让一个人完全着魔之前,他几乎不会知道其存在。”
——尤金·菲尔德
不论是英国贵族埃尔斯米尔男爵家族收藏的一四一〇年的《坎特伯雷故事》,还是被收藏家六万六千美元拍得的一七五五年版塞缪尔·约翰逊编著的《英语词典》,无论是一九九〇年以一百五十九万美元价格拍卖、由H.布拉德利·马丁收藏的《独立宣言》,还是由加州圣巴巴拉市戴维·卡佩莱斯收藏的南部联邦宪法写本,它们是古籍,是孤本,是纸页,是藏书,以影印或者照片的方式呈现在《文雅的疯狂》正文之前,或者说,这些被收藏家津津乐道并希望属于自己拥有的珍本构筑了书藏世界的一道最贵重的风景线,但是对于翻阅者来说,它们仅仅是世界的一种存在,或者说,藏书世界的“文雅的疯狂”只是被看见,而不是拥有,而在这种过眼式的被看见甚至阅读之外,则是另一个延续了两千五百年的属于拥有者的世界,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引用德国目录学家汉斯·伯哈特的观点,将这样的拥有世界命名为“文雅的疯狂”,它是独立于阅读之外的,是一种“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这种爱是文雅的爱,也是疯狂的爱,是看见的爱,也一定是拥有的爱。
但是,爱之深,或者也是疯狂之烈,“雅好积书者是书之主,爱书成癖者乃书之奴。”汉斯·伯哈特其实并没有去区分“雅好积书者”和“爱书成癖者”,或者并不能清晰界定哪一种藏书家是“书之主”,哪一种书痴是“书之奴”,他们都表现为对书的痴迷和热爱,表现出一生致力于收集、购买和保存那些珍贵的书籍,如果只是从对书耽爱的深浅程度加以区分,当然也容易落入个人财富寡众悬殊的客观原因里,而在旧金山精神病专家哈斯克尔·诺曼那里,这种“文雅的疯狂”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好奇式的毕生工作,它和书之奴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只是一种玩耍,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书籍,而不是其他收藏品,这样的一种工作需求在诺曼看来,就是一种好奇心:“我想,藏书的人多少都有智力上的好奇心,对书籍好奇,对时代好奇,也好奇于书籍对他们象征了什么。”书成为一种象征,而不仅仅是普通的物,所以藏书不是一种随意的玩耍。
对书籍和时代的好奇使得藏书变成了一种工作,使得图书变成了一种象征,而在这象征的背后,则是书籍所承载的巨大意义。无论是托马斯·杰斐逊一八一五年在《约翰·亚当斯信》中所说的“无书作伴,生有何欢?”,还是迈克尔·萨德利尔所说:“在自然界,起得最早的鸟,捉虫最多。但在藏书界,见‘虫’即知的‘鸟’,才能夺得珍品。”或者如拉里·麦克默特里在小说中写道:“宝无定相,随处皆有。”它们是人生的追求,是获得的力量,是宝贵的财富,所以这些句子都阐释了书籍作为一种物具有的价值,但并非是将它定义为一种文雅的象征,而在物的世界里,无论是“雅好积书者”还是“爱书成癖者”,其实都陷入了某种疯狂之中,都发展成一种癖病。
被看见的书,甚至不被阅读的书,如何才能成为自己的物,如何才能在自己的书架上?这其实变成了另外一个争论的议题,也就是,一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为藏书家?“如果一个人在买某本书之前,已预先料定自己绝不会读这本书,从那一刻起,他就是藏书家了。”这是一种观点,把购买图书和阅读图书隔离开来,在两种行为的微妙关系中放大了图书作为物的意义,也就是说,藏书撇除了阅读,在书籍的本体性面前,阅读在某种程度上会破坏藏书者的“永恒之爱”,这种观点显然还是太过于刻薄,而一百年前尤金·菲尔德的观点相对来说就显得平和:“书癖太难以觉察,太容易感染,在让一个人完全着魔之前,他几乎不会知道其存在。”
书痴是因为感染而着魔的,也就是书籍本身具有的物特性是一种诱惑,它影响继而支配着人在购买图书之后成为藏书者,但是这样的藏书并不排斥阅读,这或许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书痴,尽管在感染之前他也是不会知道自己内心有着强烈的占有欲,但是一旦发现了书籍具有的价值,他就投入到无法停止的“永恒之爱”中,在完全着魔中将每一本需要的书购入到自己的书架上,放入到自己的图书馆里。“着魔”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永恒的爱”,背离了“文雅的疯狂”,甚至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病症,有可能跌入到“书之奴”的危险境地。
《藏书癖,又名藏书狂;含该不治之症之历史、病征及药方之说明》,这是托马斯·弗罗格纳尔·迪布丁牧师写的一本书名,他为这种名叫“藏书癖”的病症命名,虽然有所谓的药方,但它却是一种不治之症,迪布丁不无幽默地将“藏书癖”诊断为“致命疾病”,他认为,很多十九世纪藏家都患了此“病”,而就在这种命名之后,“藏书癖”一词逐渐成为日常用语,而马克斯·桑德在一九四三年更将爱书成癖者描述成是患了“病态的、不可抗拒的精神强迫症”,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冲动,甚至“已经造成了不止一起的犯罪,离奇得让人无法忘记。”相同的观点还有费城的心理分析学者诺曼·S.韦纳医生,他在一九六六年把有藏书癖的人描述成“过度渴求”书籍,在他看来,这种过度性表现在:“主动购书,或受诱惑而购书;他会起盗心去偷窃;他会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他会做环球旅行,他甚至会与别人结婚,都是为了获得一本垂涎已久的书籍”。
当藏书变成一种疾病,甚至变成一种犯罪行为,是不是放大了物对人的役使能力,而偏离了对书的文雅之爱?十九世纪的著名博物学家、探险家埃米尔·贝塞尔斯有一次遭遇沉船,丢失了很多书籍和手稿,不久房子又失火,仅存的书籍被烧毁殆尽,在这祸不单行的现实面前,他无法释怀,便在一八八八年自己结束了生命;十九世纪法国钢琴家、作曲家摩亨奇,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那天,他因为伸手去取一本希伯来文书,结果负载过重的书架轰然倒塌,这位曾经人称“钢琴界柏辽兹”的音乐家在七十五岁的时候被一生钟爱的图书砸死了;而历史上因书而犯案者,最罪恶昭彰的应是西班牙的唐·文森特,他以前是一名僧侣,对书痴迷入骨,为了那部孤本《巴伦西亚法令集》,导致他在一八三〇年代犯下了逾八宗谋杀案;而在德国作家卡内蒂的《信仰审判》中,有一个叫基恩的人,知道自己末日已到,他从架上抽出藏书在书房中间堆叠,就像火葬时的柴堆,然后他爬上书梯的第六级等待。“火焰终于烧着了他,他纵声狂笑,是有生以来笑得最响亮的一次。”
而在当代,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被称为“古物救星”的斯蒂芬·布隆伯格,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这位“窃书大盗”:斯蒂芬·卡里·布隆伯格出于无法控制的收藏欲,从多家北美图书馆和机构盗窃了各类古书,他窃书的总数达两万三千六百本,涉及美国四十五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还有两个加拿大的省份,共计二百六十八家图书馆,所窃书籍的总价高达两千万美元。一九八八年,布隆伯格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限制区内被捕。而在他被捕时,身上带着明尼苏达大学的员工卡,还有一袋锐口牙刮匙、砂纸和其他工具,还有一小袋重约一磅的黄金,后来布隆伯格跟罗兹说,被捕前的几个瞬间,他疯狂地在“吃一个橡皮图章”,这也是盗窃工具之一。斯蒂芬·布隆伯格被美国政府提起公诉,当时陪审团要么裁定他有罪,要么以精神失常为由裁定他无罪——若判为无罪,布隆伯格会由法官哈罗德·D.菲托尔还押候审,并由他把布隆伯格送往精神病院。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在布隆伯格看来,都是一种折磨:“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如果我输,就会在监狱待一辈子;如果我赢了,就会在疯人院里待一辈子,他们会让你下半辈子都待在里面。如果我赢了,那也就是说我是疯的,我对社会有危险。”但是最后这一案子成为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案子,因为在美国的法庭之上,第一次出现了“不以精神错乱为由裁定控方无罪”,以此解释因为藏书癖而犯罪,迄今仅有一例。
“它们成了他妄想观念的延伸,成了他的自我价值感觉。他越是抑郁越是心烦,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就越觉得气愤,所以就越是去拿书或者占有书,以此为报复而得到发泄,他也变得更痴迷和更沉溺于这些念头里,去追逐去占有这些东西”。在洛根医生看来,布隆伯格偷书行为是因为被一种报复社会的心态所控制,但是这个被称为“有史以来的最大偷书贼”却认为自己是一个雅贼,“我一本书也不卖,是想收藏的。”而他这种收藏在自己看来意义是一种馆际互借,也就是从这一图书馆偷来放到另一图书馆,虽然他说他想把所有的书归还给原主,但是最后,这“另一图书馆”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人图书馆,“我不悔把这些藏品聚集在一起,但我有点后悔自己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尽管有着典型的“书痴病理学”的病例,但是布隆伯格并不仅仅是一个窃贼,他对于图书有着自己的“永恒之爱”,据布隆伯格的律师之一堂·C.尼克森回忆,当庭审时,他站在证物桌旁边,拿着一杯咖啡,有人提醒他要小心,不要泼洒任何东西在书上,而当他装作吓了一大跳,眼光飞快地瞄了一下被告席的时候,“我的天,斯蒂芬会杀了我的。”他发现布隆伯格没有离开法庭,静静地坐在被告席凳子上,而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他的那些书。
或许在布隆伯格内心,那些图书的重要性超过了法庭对自己的判决,或者说,在自己有着偷窃的羞耻面前,只有那些书是不容被玷污的,是需要保持清白的。是的,即使在中世纪,当那些书籍上被栓之以链条,被施以咒语,也只是为了震慑盗心暗起的窃贼。“纵观古今,对于拥有藏书者,书可令其体会无穷乐趣,令其耽玩痴迷,亦可令其痛苦不堪。”所以在藏书家和书痴之间,在“雅好积书者”和“爱书成癖者”之间,在“书之主”和“书之奴”之间,共有的是对于书的永恒之爱,温斯顿·丘吉尔更将文雅的表现看成是一种态度:“即使你不知道它们的内容,至少你知道它们摆放在哪里。如果这些书籍成不了你的朋友,无论如何也要让它们成为你的熟人。如果它们不能进入你的生活圈子,至少也不要拒绝向它们点点头。”而其实不管是无情乐趣,还是无限痛苦,书的终极意义还是在超越物之上的保存、流通和传播,只有当书从物变成文化,才是这种永恒之爱最大的意义。
“在不收藏的人看来,这些收藏家看上去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近乎疯癫,而收藏家通常都是如此。不过他们也会开明慷慨、造福社会,而他们也愿意如此自视。疯狂也好,明智也罢,他们毕竟抢救了文化。”威尔马思·谢尔登·刘易斯的这句话和加州巨头铁路亨利·E.亨廷顿表达的意思异曲同工:“世人生生灭灭,书籍却可永存。要盛名不朽,集藏一批珍秘善本正是无上的稳妥捷径。”也就是图书不是一种简单的商品,不是死去的物品,而是一种文化,正如十七世纪佛罗伦萨人安东尼奥·马利亚贝基把自己的名字拉丁文Antonius MagLiabechius的字母位置进行了置换,变换后可组成新词Is unus bibliotheca magna,意为“他本人就是一座大藏书楼”。是的,当一个藏书家或者书痴变成自我的藏书楼,他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永恒的文化。
“他本人就是一座大藏书楼”,在文雅的疯狂里,有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在“三十年战争”中,她手下的将领攻城略地,抢掠了不少书籍,她就先从整理这些书籍开始。之后她又批准购置珍贵的手稿,买下了好些私人藏家的藏书,“排列于四个大厅,印本藏书多不胜数,所藏手稿,数量亦逾八千部,涉及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在文雅的疯狂里,也有圣保罗教堂庭园开着“玫瑰与王冠”店铺的乔治·托马森,他白天经营店里的生意,晚上则收集种类繁多的激进小册子和临时传单。历经二十二年,他共收集了两万两干二百五十五件藏品,集成两千零八部巨册。在文雅的疯狂里,还有美国新一代收藏家詹姆斯·伦诺克斯与约翰·卡特·布朗为代表,两人都在一八四〇年继承了巨额财富,两人都是人到中年时开始经营搜讨藏书,两人的兴趣都是以坐拥书城成为乐事,此外他们也乐意在英国人的地盘按照他们的规则与英国书林的当权人物争夺,并开创了延至下一代人的先例。在文雅的疯狂里,还有亨利·克雷·福尔杰和他的妻子艾米丽·乔丹·福尔杰,两人志趣相投,皆嗜藏书,合力在首都华盛顿创建了福尔杰莎士比亚藏书楼,福尔杰夫妇身故之后,骨灰存放在离主阅览室不远处的一个石桩后面,而他们的遗产“长存天地间”。
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的收藏和保存,更在于挖掘和整理,阿伦·兰斯基认定自己一生的使命是要拯救书籍,保存一种濒灭绝的文化。作为一名犹太人,面对“意第绪语是一种死语言,何必浪费时间呢?回学校吧。去以色列吧。”的告诫,他从碎纸机和垃圾堆填区抢救出了众多意第绪语书籍,还荣获二十二万五千美元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1978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一直用意第绪语写作,他说:“意第绪语是流亡者的语言,没有国土,没有边疆,不受任何政府支持;意第绪语中没有武器、弹药、军事演习、战略等词汇;意第绪语受到非犹太教徒和已放的犹太人蔑视。”他强调,意第绪语“还没有死亡”,它“蕴藏着世人还未看到的财富”。而兰斯基显然在拯救书籍的道路上更为执着,也收获更大,他在一九七九年成立国立意第绪书籍交易所,次年又组建国立意第绪图书中心,还招募了一批志愿者进行搜集和整理,而对于这些文化书籍的挖掘和整理,也被看成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信仰:“我生长在一个爱书惜书的家庭,妈妈和祖母都酷爱读书。犹太文化中,书籍一向是很重要的。要是书掉了,就要捡起来,亲吻一下。刚开始时这么做,是因为那些书都是祈祷书,后来逐渐变成对每本书都同样尊敬,不管内容是什么。”
“藏书将会告诉主人,昔日银行与文明均已灰飞烟灭;各届政府亦曾濒临破裂,世世代代之人类不过是群愚而已;不过又是何等有趣啊。诸神应在笑看如此人间闹剧,我辈岂可不与诸神齐笑?”不管是国王还是平民,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神秘的拍卖者,也不管是对图书保存收藏还是挖掘拯救,不管是私藏于自己的个人图书馆,还是捐献于公共图书馆,只有让书超越物的属性,赋予书的象征意义,才是一种文雅的疯狂,所以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将人类拥有书籍的二千五百年看成是“永恒的爱书之情”,他在二〇一二年新版序言中说:“我的终极目标是要显示,如果没有这些卓越人士的奉献和毅力,我们珍视的文学、文化和历史,就会出现无可挽回的损失。”
书并非是和藏书者割裂开来,他们是一个整体,书因人而成为永恒之物,人也因书而成为个人的图书馆,弥尔顿失明后口授作书,女儿黛博拉代为笔录,文明变成了固定、物化的书籍,而拥有这本《失乐园》的北卡罗来纳州作家雷诺兹·普赖斯说:“在我看来,这就像基督教中的宗徒传承。上帝之手触碰过弥尔顿的手,弥尔顿的手触碰过黛博拉的手,黛博拉的手触碰过此书。而我触碰此书的那一刻,有如触碰了黛博拉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