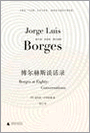 |
编号:E63·2141219·1140 |
|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49.00元亚马逊36.30元 | |
| ISBN:9787549557806 | |
| 页数:385页 |
“我无法一睹纽约,不是因为我双目失明,而是因为纽约使我失明,与此同时我又爱着它。”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失明成为他解读曼哈顿,解读纽约,乃至解读美国的一种特殊方式,1976年和1980年的两次美国之行,让他在游走四方中开始了一种特殊的口头文学的写作,而在这些访谈里,无不展示了博尔赫斯对时代、宗教、哲学、文学和写作的诸多观点。“在我的小说中,我以为唯一的人物就是我自己。”或者在访谈中,他也看见了另一个走进迷宫的自己。本书为博尔赫斯、巴恩斯通、西川三位诗人一次跨越时空和语言的诗艺合作。
几年前,我曾想将他摆脱,于是我放弃了城外的神话,而转向时间和永恒的游戏,但是那些游戏如今也归了博尔赫斯,我只好再去构思些别的东西。就这样,我的生命在流逝,我失去了一切,而一切都属于忘却,或者属于那另一个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与我》
“事情都发生在那另一个叫做博尔赫斯的人身上。”引文里最后不是逗号,是句号,却引向了无穷和无限的可能,一个写在教授名单上的名字,一个被收录在词典里的名字,一个写过几页好文章的人,一个继续在搞文学的人,他叫博尔赫斯,却不是我,我见过他的名字,我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他,我把游戏都归了他,甚至我想将他摆脱。但是那个叫博尔赫斯的人和我,却有着同样的爱好,喜爱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格式、咖啡的味道和斯蒂文森的散文,“但是他虚荣地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演员的特征。”当我不是博尔赫斯,当博尔赫斯不是我,所有的故事都只是一个关于遗忘和否定,关于替代和抹去的记忆。
博尔赫斯和另一个博尔赫斯,其实是我和另一个我,当博尔赫斯写下《博尔赫斯与我》的时候,其实在困境里已经无法逃脱,那最后的命运变成了一个疑问:“我不知道我们两人之间是谁写下了这段文字。”是的,另一个博尔赫斯在文字里,在小说里,在时间里,在游戏里,甚至博尔赫斯还对着另一个博尔赫斯进行着无法割舍地解读:“博尔赫斯代表着我所嫌恶的一切。他意味着声誉,意味着被拍照,被采访,意味着政治、观点——我要说,所有的观点都是卑鄙的。他还意味着失败与成功这两个无足轻重的东西,这两个骗人的东西,或如他对它们的看法:失败又蕴含着胜利,成功又蕴含着灾难,而这胜利与灾难同样也是骗人的。”被分割的博尔赫斯,其实是合一的博尔赫斯,另一个博尔赫斯是被命名的博尔赫斯,而自称我的博尔赫斯则是返回自身的博尔赫斯。
仿佛是一个无限循环的绕口令,是的,当博尔赫斯念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像是在进入一个急于逃脱的自我世界,“我何必要在我自己的名字上费心呢?它实在拗口: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很像豪尔赫·路易斯·豪尔赫斯,或者博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个绕口令,连我自己都说不利落。”那是1980年的5月,那是远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纽约,在迪克·卡维特的节目里,博尔赫斯说着自己绕口令的名字,那一刻,博尔赫斯就像是一个《博尔赫斯与我》中那个虚荣地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个演员特征的人,充满了戏谑。
1980年5月的博尔赫斯,一定看见了“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在一个充满表演特征的节目里,他说到了自己失明的眼睛,那发着光的朦胧一片最后变成了一幅定格的黄昏图像,再没有变化,再没有惊奇,“那时我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开始发现我被包围在没有文字的书籍之中。然后我朋友们的面孔消失了。然后我发现镜子里已空无一人。再以后东西开始模糊不清了。”这是1955年的博尔赫斯,开始了阅读和写作的博尔赫斯,作为一种家族遗传,双目失明的故事传到博尔赫斯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代了,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在双目失明之后微笑着死去,亲眼看着祖母在双目失明之后微笑着死去,而他的曾祖父在死的时候也是双目失明,“但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也曾微笑过。”双目失明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更像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但是曾经他看见祖母和父亲双目失明,看见他们微笑着死去,却注定无法看见自己双目失明——看见的对象必定是一个脱离自己的存在,就像那个“虚荣地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演员的特征”的叫博尔赫斯的人,所以当不再看见,博尔赫斯才成为那个急于逃离的我——在逃离中,他才能把世界当做对象,把博尔赫斯当做对象。
“眼睛设计得十分笨拙,但它们带给我们愉快,很抱歉,它们也带给我们地狱,带给我们痛苦。肉体的痛苦实在很难忍受。”这当然是关于身体疾病的一种解读,从此他无法看见,看不见活着的自己,看不见被书写的文字,甚至看不见照顾他、和他一起翻译作品的女人玛丽亚·儿玉,这个博尔赫斯的日裔女秘书,这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其实最后也变成了一种象征。他曾经问过威利斯·巴恩斯通,玛丽亚·儿玉的面容是什么样的,“因为她总是说,她的脸是丑陋的”。他曾经触摸过她的脸,但是不看见的现实让他无法确定,而威利斯·巴恩斯通对他说,她是美丽的,她看谁一眼,那人就当心存感激。但是这样的美丽和感激永远无法变成可以看见的面容,博尔赫斯希望看到这个将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的脸,但是最后“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的朦胧也没有了,周遭的黑暗甚至让他无法辨认自己在镜子中的脸,关于身体的自我消失了,他只能在弥尔顿纪念亡妻的那首《关于他的失明》的诗中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失明的人”:
这镜子里的那张脸,
瞅着我的是谁的脸;
知道谁是那反映出来的老人,
早已疲惫的愠怒,默不作声。
我变成了谁,我其实变成了博尔赫斯,变成了那个无法看见却只能被命名的博尔赫斯,变成了曾经想要逃避和摆脱的另一个博尔赫斯。看起来像是一种无奈的代替,是一种对于身体缺失的痛苦,但是这“疲惫的愠怒”,这“默不作声”并非全部是失明所造成的,或者把博尔赫斯和另一个博尔赫斯分离开来,并不应该在失明这个时间节点上画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其实在博尔赫斯的一生中,他总是在否定自己,遗忘自己,一直在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不在名誉、声望、国家和现实里的自己。
 |
| 博尔赫斯:镜子与交媾是一回事 |
他说:“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但是现在却远远地避开我们。只有历史学家们,或那些自诩为历史学家的小说家们才能了解现在。至于今天所发生的事,那是宇宙全部神秘的一部分。”这是对于时间的遗忘,时间包含了自我,可是在意味着自我的过去之外,那些即将来临的时间,那些对于未来的预期,都成为不解之谜,“而我们很高兴它们永无解开之时,我们就能永远解下去。”他说:“我认为诗歌应当是匿名之作。比如说,如果我能选择,我会乐于让他人加工、重写我的一行诗、一篇小说,以便让它们流传下去,我希望我个人的名字会被忘掉,正如在适当的时候会是这样。”这是对于文字的遗忘,那些已经写下的句子、诗歌和小说,都在一种已经存在的状态下,它不通往未来,也不在现实里。他说:“依我看,找到正确词语的惟一办法,是不去寻找它。一个人应当活在此刻,此后,那些词语会不寻自来,或根本不来。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毛病百出地生活下去。”这是对于希望的遗忘,万事万物都可以转化为诗歌,我们只是在这个完成的过程中,而永远无法抵达结束的那一刻。
否定和遗忘,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不仅是因为不再看见,更是因为不想看见,绕口令的名字,演员一般的生活,“我写的总是同一个老博尔赫斯,只是做了点儿手脚。”那个叫博尔赫斯的人不是我,那是被命名的人,是被想象的人,甚至是一个复数的人,他是一个群集,是一个带来幻觉的人群,“我们是孤单的,你和我。意味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那并不存在,当然是这样。甚至我自己也或许根本不存在。”所以在人群之外的自我,完全变成了被割裂的个体,就像“创造的神话”的惠特曼一样,他一辈子没有在德克萨斯带过,却说“我要讲述我青年时代在得克萨斯知道的事情,”他说:“当我在阿拉巴马的清晨漫步。”但是他从未去过阿拉巴马。所以惠特曼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一个诗人,一个个体,而是一种符号,他是作为人的惠特曼、作为神话的惠特曼和作为读者的惠特曼化合而成的人,所以当读者问他:“你看到了什么,沃尔特·惠特曼?你听到了什么,沃尔特·惠特曼?”惠特曼的回答是:“我听到了美洲。”
美洲是群集,美洲是人群,美洲是神话,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他也听到了自己的回答,他也看见了代表美洲巨大声誉的博尔赫斯,这是一种象征,一种包裹自己的象征,一种消除了个体意义的符号。所以在博尔赫斯身上,否定早就开始了,早于失明的那一刻。在巨大的美洲神话里,在国家意义上,博尔赫斯站在了逃离者的位置,“今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乎不存在。这样说我很抱歉。我的国家正在垮掉。我对世事感到悲哀。”是的,曾经是家禽检查员的博尔赫斯听到了国家的一道命令,作为激进的阿根廷联盟党中重要的民主派,他反对过执政的大农场主阶级。而在庇隆政权的时代,站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边的阿根廷成为博尔赫斯一个噩梦,“我热爱意大利,热爱德国,而正因为如此,我厌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以厌恶阿根廷,厌恶国家,厌恶政治,他说,国家是一个错误,是一种迷信,所以他把自己称作是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是一种对于政治的逃避,而其实他的注解是:个人主义者。
阿根廷消失了,眼前的世界消失了,不信奉国家,不再看见,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却在遗忘和否定的世界里看见了恶梦,这像是一个“梦见自己醒着”的隐喻,返回自身不是清除一切,而是更敏感地看见地狱和死亡。恶梦是夜的寓言,是失明者的寓言,是否定者的寓言,爱伦·坡看见过恶梦里的幽灵,卡夫卡看见过恶梦中的荒谬,而博尔赫斯看见的是噩梦中的记忆,它像末日审判一样压着博尔赫斯,“我们可以说,就在我们做事有错对的时候,末日审判始终在进行着。末日审判并非要等到最后才开始。它始终在进行着。”始终进行着审判,始终在噩梦里,博尔赫斯说,他的噩梦有三种,一个是迷宫,迷宫是找不到出路的恐惧;一个是写作,“这是一个我想读书而又读不成的噩梦:我会梦见那些文字全活了,我会梦见每一字字母都变成了别的字母。”另一个则是镜子,在镜子的世界里,总是和交媾合在一起,“镜子与交媾是一回事。它们都创造形象,而不创造现实。”
迷宫的噩梦是对现实遗忘而又重新陷入,写作的噩梦是对失明的逃离而又无法自救,镜子的噩梦是对形象的丧失而变成虚幻,噩梦带来了神秘感,带来了恐惧感,它是“梦之虎”,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不是否定和遗忘,却是要永远记住,就像死亡,本来是一种逃避,却一定是必然,所以在这巨大的噩梦包围的世界里,在失明而越加清晰看见的世界里,博尔赫斯反倒找到了一种安慰,甚至最后变成了一个“新经验的开始”:“我们何必还要从一座地狱走向另一座地狱,受更多更大的罪!”就像面对死亡,反倒是一种解脱,一种告别现实无意义的期盼,“可以说我贪图一死,我不想每天早晨爬起来发现:哦,我还活着,我还得做博尔赫斯。”当那个现实中的窃贼真的威胁博尔赫斯“给钱还是给命”的时候,博尔赫斯坚定地回答:”“给命。”将窃贼吓得逃跑了。多次想过自杀,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死亡反倒充满了戏谑的味道,甚至变成活着的一种强大武器:“我告诉自己,有什么好忧虑的呢,既然我有自杀这件强大的武器,而同时我又从未使用过它,至少我觉得我从未使用过它。”
噩梦而带来的恐惧,死亡而带来的解脱,对于博尔赫斯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经验的开始”,不再纠缠于绕口令一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他写下了一首关于毕尔格的诗:“如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说谎也听别人说谎,/他背叛别人也被别人所背叛”,他就是其他人,他就是别人,“毕尔格孤独一人,现在/就是现在,他修改着几行诗。”就在那里改了几行诗的是博尔赫斯:把博尔赫斯(Borges)变成“有声音”(burger),再把“有声音”变成毕尔格(Birger),这是博尔赫斯的一个“文学圈套”,而对于他来说,仿佛也脱离了“另一个博尔赫斯”。隐喻、自我命名,甚至匿名,博尔赫斯完成了另一种关于命运的返回游戏,于是在阅读世界里,从没有读过一份报纸的他开始专注于古英文,“我认为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地依靠‘过去’那个巨大的集市。”寻找通向那个集市的道路,博尔赫斯把对生命的切身体验投入其中。在国家意义上,他离开阿根廷,喜欢神秘的岛屿,喜欢有着西方文化和自己文化以及“笼罩其上的中国文化的灿烂阴影”的日本,喜欢“使我失明”、立刻想起沃尔特·惠特曼的纽约,希望产生过吉卜林和《道德经》的印度和中国。而在文学创作中,他把所有一切的错误都当成是诗人的工具:“错误的女人、错误的行为、错误的事件,所有这一切都是诗人的工具。一个诗人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不幸,视为对他的馈赠。不幸、挫折、耻辱、失败,这都是我们的工具。”在惠特曼、爱默生、爱伦·坡、马克·吐温、弗罗斯特、但丁、莎士比亚的文字里,营造另一个梦:“我必须把某些东西添加到这个梦中去。我必须赋予梦以形式。”
不活在过去活在现在,不虚构小说描写现实,不创造人物却把自己扮成所有人物,博尔赫斯的新经验其实又返回到一个自我的世界,遗忘是为了记住,否定是为了新生,匿名是为了命名,“世界运行,没完没了,永无尽头。”所以不管是1955年的失明,不管是1980年的演讲,对于博尔赫斯来说,都是世界的一个过程,都是在过去中找到自我,“如果你彻底接受了唯我论,那么我这样拍一下桌子就可以是世界的开始。不,世界不是这样开始的,因为世界早就开始了,开始于很久很久以前打一个响指的瞬间,或像我拍桌子的这一秒钟。”
世界自以为是,诗人只是把错误变成工具,那错误的世界里总是有一只噩梦般的老虎,这是一只出现在“广大而繁忙的图书馆”的老虎,是一只“反抗那真实的热血”的老虎,也是一只“由我的梦幻/赋形,成为言词一组/而不会由脊骨支撑/超越于一切神话之外,/漫步世界”的老虎,在迷宫里,在镜子前,在写作中,而当博尔赫斯转身,用失明的眼睛看见噩梦的时候,三只老虎各自找到了身体、语言和名字,而最后的故事是,那个看不清自己的老人开始“思索一条无限的老虎之链”:
我在
午后的时光中继续搜寻
另一只老虎,不在这诗中。
——博尔赫斯《另一只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