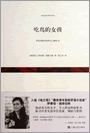 |
编号:C63·2160820·1322 |
| 作者:【阿根廷】萨曼塔·施维伯林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18.00元亚马逊7.10元 | |
| ISBN:9787532150618 | |
| 页数:114页 |
“我开车去了那家兽医院,告诉店员我要买一只小鸟,越小越好。售货员打开一本带图片的目录,开始给我介绍每个品种的不同价格和所需饲料。我猛的一掌拍在柜面上。柜台上的东西都弹跳起来;店员吓得不敢再作声,只默默地看着我。”女孩和小鸟的关系里,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美,那是一种暴力式的占有,还是一种死亡的丰富意象?哈维尔·帕耶拉斯说:“萨曼塔·施维伯林的《吃鸟的女孩》就像是任何一座城市郊外的高速公路:旅客的叙述,土地,如电缆般蜿蜒游动的蛇,远处的风情,精准的耗损。这一切组成了西班牙语叙事文学中最值得赞赏的一部杰作。作品集收入了她的短篇小说共14篇,其中包括影响较大的《愤怒的瘟疫蔓延》、《吃鸟的女孩》等。
《吃鸟的女孩》:如今真不是一个好时代
人们互相碰杯祝酒,燃放的烟火照亮了整个夜空。大家鼓掌爆发出一阵欢呼。这时我感觉到了:一切看起来更模糊、更黯淡,我忍不住想知道他们怎么了,这可怕的场面到底是怎么了。
——《我的兄弟瓦尔特》
碰杯祝酒是快乐,燃放烟花是美好,当所有人的聚会发出欢呼,当整个夜空呈现出喜庆,似乎一切都以圆满的方式被书写,是的,大家成双成对,大家和谐共处,再不存在什么困难。可是这只是被看见的场景,这只是外部世界的表象,当克拉丽丝和农场总管约会,当医生答应免费为瓦尔特治疗,当我们都在周末看望瓦尔特,却恰恰忽视了另一种潜在的困境,一个身患忧郁症的人,一个不和别人交谈的人,一个无法走进他人心灵的人,如何在这样的聚会、治疗、照顾中找到自己?如何在爆发的欢呼、照亮的夜空之外被人关注?
世界恰恰被分隔成两半,一半在那热闹的聚会上,一半在那犹豫的心里,而所有的庆祝会、单身派对和新婚宴席,对于瓦尔特来说,不是慢慢接近别人,而是越来越疏离——他就在这些场合从头到尾呆坐着,热闹衬托着冷清,欢呼衬托着病态,成双成对衬托着孤独寂寞,他人衬托着个人,所以一切在相聚中走向分离,一切在璀璨中走向黯淡,甚至,一切在美好中走向更深的病态,所以最后的世界是更可怕的存在。
但是,谁能看见这背后的可怕?一切仿佛都被掩盖了,一切仿佛都被异化了,一切在自己的路上走向毁灭。“我的兄弟瓦尔特”,瓦尔特是我的兄弟,却像是普通世界之外的敌人,不是我们把他当成敌人,而是外部的世界把内心世界当成了敌人。敌人是被叫做“我的兄弟”的瓦尔特,是一只折翅的蝴蝶,是被棍子打倒的狗,是吃鸟的女儿,是那一双高跟鞋制造的恐惧,是四周尽是干枯灌木丛的荒原……仿佛如动物般的存在,注定是无法和他人一样碰杯祝酒,注定无法抬头看见燃放的烟火。
忧郁如瓦尔特,怪异如瓦尔特,荒诞如瓦尔特,更模糊、更黯淡如瓦尔特,世界像荒原一样存在,“要在荒原上过日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去哪里都得花上好几个小时,举目望去,四周尽是干枯的灌木丛。”这本身就是一种隔离,即使保尔每周去镇上三次,即使和农业杂志社保持联系,即使我在家里举行仪式增强生育能力,即使碰到和我们一样的一对夫妻,但是这个“荒原”的存在方式永远找不到最后的目标,永远不是通向成功,戴着手套,背着书包,拿着手电筒,还有一张网,甚至还有猎枪,但是在黑暗中,那个“丰沃多产的事物”到底在哪里?这是一重困境,藏身在荒原上,隐匿在看见的世界里,所以“丰沃多产的事物”本身就指向另外一个隐喻世界,而我和保尔,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要让它成为某一种猎物。
猎物是为了捕获,捕获是为了消灭,但是看起来,“丰沃多产的事物”是一种没有实现的理想,“他漂亮吗?”“难道他整天都在睡觉吗?”而当保尔在另一对夫妇那里去看的时候,遭遇到的便是一种可怕的爆发,保尔在尖叫,东西被砸碎,终于逃出了恐怖世界的时候,保尔的身上都是伤痕,都是血迹,但是即使可怕的一幕发生了,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没有放弃努力,甚至想到会有一个属于我们的“丰沃多产的事物”,在保尔恐惧的眼神中,猛踩油门的动作中,那个不被捕获的猎物依然在荒原上,而我们依然寻找,依然要找到我们自己的东西。
“属于我们的那一个”是一种归属,就像瓦尔特是我的兄弟一样,这是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唯一保持联系的地方,而这种归属带来的是可怕的占有。就像“杀死一条狗”一样,占有意味着可以进入组织,意味着可以赚钱,所以唯一突破两个世界的办法便是测试:“测试的内容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用棍子打死一条狗。”从别人那里拿来了棍子,在狗群中狠狠砸向了一条狗,而放进后备箱的狗为什么没有立即死去,甚至在去往码头的路上还在挣扎?最后是别人,“这一次,棍子划过空气,砸在了那条狗头上。它倒在地上,惨叫着,抽搐了好一会儿,最后一切归于平静。”打倒而没有死去,是不是一种占有?是不是通过了测试?而像那人一样毫不犹豫地将垂死挣扎的狗打死,是不是意味着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但是为什么我回头环顾的时候,那个广场中央,那个喷泉旁边,却还有一群狗拱起身子,“向我望来。”
 |
| 萨曼塔·施维伯林:我靠近了“丰沃多产的事物” |
半死不活的狗,半死不活的任务,半死不活的测试,半死不活的占有,实际上在两个世界一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距离,看上去一切都死去,都消灭,都占有,但是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走向另一个极致。卡尔德隆的肩膀上停着一只蝴蝶,漂亮的蝴蝶,和女儿的衣服一样花纹的蝴蝶,他抓住了蝴蝶,拎起翅尖,希望女儿能够喜欢它——占有开始了,而且占有还在继续,蝴蝶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为“女儿喜欢的蝴蝶”,也就是要让它找到一种归属。但是蝴蝶却折断了翅膀,跌落在地上,“它笨拙地在地上扭动,试图重新飞起来,但无济于事。最后蝴蝶终于放弃了;它躺在地上动不动,只有一边的翅膀每隔一阵子会抽搐一下。”飞起来是回到它自己的世界,而其实这个世界早就被一双手破坏了,所以当蝴蝶变成被占有的蝴蝶,变成有了归属的蝴蝶,它的世界就已经被改变了,于是,卡尔德隆为了让它得到解脱,一脚踩了下去,而当校门打开,女儿会像蝴蝶一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再也不敢从刚踩死的蝴蝶身上抬起脚,因为,“他生怕也许,在那只死去的蝴蝶的翅膀上,会看见自家女儿身上衣服的颜色。”
蝴蝶变成了女儿喜欢的蝴蝶,却最后是被踩在脚上的命运,所以那种占有、那种归属指向的是一种毁灭——不是蝴蝶的毁灭,是女儿的毁灭,也是自己想象的毁灭,“成百上千只色彩缤纷、大小各异的蝴蝶朝着等待中的家长们飞扑过来”,不是他占有了世界,是世界占有了他,“他甚至想到了死。”蝴蝶之死,女儿之死,自己之死,第一种是现象,第二种是幻觉,第三种是本质,在这个被呈现出的怪异、荒诞的世界里,到底谁是捕获者,谁是猎物,谁是打狗的人,谁又是死去的自己?
其实,荒原、瓦尔特、蝴蝶、狗,所构成的是一个地上的世界,它们的冷寂、忧郁、死亡和毁灭,是一种怪异,是一种荒诞,是动物般的存在,而在地下呢?那个酒吧里的老头讲述的故事,都在地下世界里,孩子们在空地上发现了一处隆起,然后用手扒土,然后开始挖洞,这是孩子们自己的地下世界,而大人们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当灾难发生的那一天,地下世界才以可怕的方式出现在大人的世界里,一位母亲听到了来自地下的异响,丈夫开始翻箱倒柜,并且呼喊孩子的名字,之后所有的家长都在呼唤,但是没有孩子的回应,甚至当掀起井盖,盖子底下也没有井,于是大人开始挖掘,从地上到地下,但是每日每夜地挖,也找不到任何东西。
孩子去了哪里?他们被遗忘在地下世界,他们也从地上世界逃离,所以大人们在地上世界的呼喊、挖掘,根本无法改变那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也无法发现那里的所有孩子,所以地下和地上,孩子和大人,以这样一种隔绝的方式呈现着对立,没有占有,没有归属,甚至没有发现,没有打开,而即使被隔绝,也分明是一种投射,而讲故事的老人拿着作为报酬的五比索,在故事讲完之后说了一句:“我在那儿工作。我们是矿工。”
矿工,也是掘洞者,也是为了打通地上和地下,而作为讲述着,似乎要打通的是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他人世界和个人世界,寓言世界和现实世界。但是这两个世界的存在,为什么会隔阂?真的能打通吗?地上世界的怪异和荒诞,其实是地下世界在背后造成的疏离、孤独、冷漠和暴力,也就是说,地上只是地下的一种投射。那个边境村庄,那个贫穷落后的村庄,那个没有人交谈的村庄,吉斯蒙蒂的拜访和统计,是闯入了他们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他感到的是“一种彻骨的不安”,感到窗户和门背后都有人,当那袋糖果递给他们的时候,吉斯蒙蒂感觉到的是“一阵轻微的动静”,一个小男孩在众人中拿到了糖果,却在吉斯蒙蒂的视野之外,他看不见男孩的眼睛,看不见男孩的手,终于也看不见那些糖果:“他跪倒在地,手中的糖撒了一地。重新被忆起的饥饿感伴随着一种愤怒的情绪,如瘟疫般在山谷中蔓延。”
“愤怒如瘟疫蔓延”,地下世界投射到地上世界的是愤怒,闯入之后是退出,而这种退出对于地上世界来说,便是跪倒在地的死亡。对于恩里克来说,不是跪倒,却是摔倒,那家玩具店本来是拒绝他,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将玩具整理好,并且吸引了许多顾客的时候,他闯入这个玩具店意味着带来更好的生意,但是后来他放弃了创意的摆放,放弃了整理,生意又下滑,而对于恩里克来说,寄宿在玩具店里,呈现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秩序,但是这种生活随时会被打破,正如吉斯蒙蒂跪倒在地的村庄一样,他的背后永远站在一双恐惧的高跟鞋,一个凶恶的声音传来,他终于跌倒在地,“我看见他伸出手,他细瘦的手指挣扎着,试图从他母亲向他伸来的魔掌中逃离。”
母亲的魔掌,就如那糖果一样,是原本甜蜜的爱,却是邪恶的化身,从地下,从背后出来,然后控制着地上世界的他们,让他们变得怪异,变得荒诞,变成了“丰沃多产的事物”,甚至变成了吃鸟的女孩。一个女儿,一个甜心的女儿,一个可爱的女儿,却最后打开了鸟的笼子,张开嘴,吃起了鸟。“她的嘴上、鼻子上、下巴上和手上都沾满了鲜血。她害羞地笑着,嘴唇弯出一个大大的弧度。”吃鸟还带着笑,显然是一种享受,当我恐惧,我恶心,我呕吐,女儿萨拉却说了一句:“您也一样啊。”也就是说,大人也是吃鸟的人。为什么吃鸟?其实在这个地下世界里,家庭面临着危机,母亲塞尔维亚显然和他们父女已经离婚,婚姻之死,家庭之死,女儿像鸟一样,被吞噬了,所以她变成了吃鸟的女孩,就是像大人一样毁灭一种存在,而且津津有味,所以当最后我在养鸟指南上看到,“在温热的气候下这种鸟必须成对抚养,并要尽量减少监禁的时间。”似乎将这种危机带向了一种可以解决的可能里,“我知道,之后我总有办法,对付着过下去。”
其实这样一种可能只是自我安慰,当背后永远有疏离,有孤独,有冷漠,有暴力,吃鸟的女孩就会一直存在,如瘟疫的愤怒就会一直蔓延,那种被破坏的生活就会永无止境。《伊尔曼》里那个空荡荡馆子里的男人,是矮小的男人,是被压抑的男人,但是当主宰一切的女店主死了之后,他用枪威胁顾客:“你们要走?不,别走!我不想单独跟她待在一起!”为什么要用暴力,无非是自己是暴力的牺牲品,“我会付你钱”传递的另一种暴力,而在若干年前他就是这样成为那个死去女人的男人,而当我们从他的枪底下逃跑的时候,是把那一个盒子一起带了出来,以为里面是金银财宝,却原来是一张照片,几封信,以及已化为尘埃的薄荷糖、一块“年度最佳诗歌”的塑料奖牌。珍藏在那里,是记忆,是荣誉,是过去的自己,但是当我们拿走了这一切,并不是在无用的状态下归还,而是扔出了窗外。
伊尔曼是谁?刻在盒子上的名字?失去了女人的男人?显然,这两种身份是截然分开的,而分开的身份,让世界也截然分成地下和地上,诗歌、爱情以及荣誉,全部在女人的压抑和统治下,而一旦女人死去,他的枪以及威胁,以及欺骗,似乎又传递着另一个暴力游戏。而《圣诞老人上门来》呢?妈妈似乎也像“我的兄弟瓦尔特”一样,生活在病态的世界里,一直坐在电视机前,不停地切换频道,总是对我们说:“谢谢你,亲爱的。当心别着凉了。”在病态的家庭里,父亲和邻居玛塞拉一起,“他们成了好朋友,玛塞拉经常会在下午来我们家。她一来就会为我们烧饭,收信,收拾屋子。”实际上这是一种暧昧的取代,也就是把病态的母亲死亡化了,但是那扇门开启的时候,门口却是一个圣诞老人,母亲上前抱住他,并且说:“布鲁诺,我不能离开你,没有你我快要活不下去了!”
圣诞老人不是圣诞老人,不是爸爸带着我寄信给他的圣诞老人,不是在圣诞节虚拟的祈福对象,他是布鲁诺,是一个重新让母亲活着的人,“既然爸爸跟他的朋友过得这么愜意,她又为何不能跟圣诞老人做朋友呢?”像是一种温情的回归,圣诞老人进来,圣诞老人和母亲在一起,圣诞老人今晚睡在我们家,可是,圣诞老人的脖子在流血,“明年一定会更好”的背后却是无可逃避的破坏力,爸爸和玛塞拉,母亲和布鲁诺,他们最后在一个平行世界里,维持着怪异、荒诞的存在,维持着冷漠和疏离的关系。而在《储存》里,胖了的我要吃药,不是因为要变瘦,而实际上是肚子里的特雷西塔让我陷入到一种被改变的生活里,曼努埃尔对我说的话也越来越少,爱情和婚姻似乎正在走向冷漠,所以我的吃药行为只是为了挽救这本已经死去的感情,最后,在“自主呼吸”治疗中,我的肚子开始缩小,于是父母把给特雷西特准备的床单、礼物都拿走了,而在“曼努埃尔对我好得不能再好了”讽刺中,我走向的是一种彻底的毁灭:“我把手放在肚子的女人的肚上。我的腹部如今平平的,就像任何一个女人,我是说,没有怀孕的女人的肚子。相反,威斯曼说过治疗的手段有点激烈。我如今有点贫血,而且反而比吓上特雷西塔之前瘦许多。”
这是成功的治疗,挽救婚姻和爱情,却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向了病态,“我看着曼努埃尔:他耐心地等着我,直到我靠近那个杯子。最后,终于,我轻柔地把她吐了出来。”吐出来的是肚子里存在的最后希望,却也变成了被摧毁世界的物证,焦虑没有了,害怕没有了,冷漠没有了,但是失去特雷西塔,世界依然是被摧毁的,依然是怪异的,依然是荒诞的。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他人世界和自我世界,他们没有打通,却以映射的方式变成了一个世界,愤怒在蔓延,暴力在延续,冷漠在传染,孤独在变异,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世界,只是以隐秘和藏匿的方式,锁上了那扇门,关上了那扇窗,盖上了那口井。
“我只做必须做的事,我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一头撞地》中的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不管受害的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就一定要把那人往地上砸,让他头部流血,让他痛苦不堪,这是彻底的毁灭,没有两个世界,只有一个黑白分明的标准,而这样的世界拒绝女人,拒绝暧昧,拒绝友善,拒绝国际主义,三次把人脑袋撞开了花,是三次强化了自己世界的独一无二。但是为什么世界只有一个标准,为什么我会成为一切的主宰?“我开始思索妈妈常说的话。她说这个世界严重缺乏爱,而且,不管怎么说,对敏感的人来说,如今真不是一个好时代。”正是因为世界缺乏爱,所以只能用暴力代替,正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好时代,所以人人都可以把坏人砸向地面,用一种唯一的标准取代另一种唯一的标准,这是一种毁灭——用毁灭来毁灭没有爱的世界,毁灭本身就是一种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