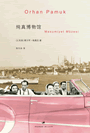 |
编号:C39·2170419·1382 |
|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39.80元亚马逊30.60元 | |
| ISBN:9787208089884 | |
| 页数:567页 |
色欲沉迷开始的故事里有44次的做爱,但是当离去变成主题,2864天、409个星期、去了他们家1593次,以及4213个烟头,都在数字的隐喻里走近那种回忆。“我建成了一座‘纯真博物馆’。这里就是我的家,能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帕慕克多年前曾在伊斯坦布尔购置一处房产,所在地正是书中所写芙颂家的住址——楚库尔主麻的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此地会以本书命名并改建为特色博物馆,藏品主要反映伊斯坦布尔当地的文化和城市生活。纯真博物馆计划于2010年起接待游客,凭书中所附门票可得到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纯真博物馆’中所有物件的故事,就是我对芙颂的爱情故事。”
《纯真博物馆》:我结婚了但依然是处女
三十年后,当我在组织这些句子时,我要说,现在我认为这些人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跳舞时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吸引她,我相信她会对我感兴趣的,我也不会那么无奈地看着她从我的怀里溜走。
——《幸福》
第83章的幸福,是最后的幸福,第三人称的幸福,是纯真的幸福,“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作为一个假设,在最后的幸福里,它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后悔?当奥尔罕·帕慕克如此讲述自己和芙颂有关的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早就注定了最后一次,而不了解人生恰好是把那个口口声声说爱着芙颂的凯末尔抽离出了那八年的时光里,当我从经历者和讲述者变成了一本书的作者,其实就像那个假设一样,走向了一种纯真的可能状态:我们在别人的订婚仪式上相遇,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树下接吻,最后,“我们结婚了!”
一条沿着“如果”的道路走下去,是纯真的相遇,纯真的相爱,以及纯真的结婚,那么不了解人生就是一种纯真的状态,而那个作者的我也将在最终的幸福里。只有把凯末尔抽离出那段经历的故事,只有把奥尔罕变成第一人称的“我”,纯真的博物馆才有意义,但是,“在书上,您用‘我’来讲述您的故事。我在用您的口吻叙述。这些天,为了把自己放到您的位置上,为了成为您,我费了很大劲。”这样一种抽离和替换,仅仅只是名字的改写,仅仅只是人称的转变,或者仅仅只是一次“假如”?“我不怀疑,故事将是我的故事,他将对此表示尊重,只是我觉得发出我的声音很别扭。”当凯末尔如此定义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抽离和替换根本没有发生,其实文本只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即使用八年的时间收集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即使15年里参观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即使把所有的人物都索引在故事的末尾,即使有地图和纪念的门票让人们记住,纯真博物馆也像是一个失去之后,“用他的声音来取代我的声音”的虚无伊甸园。
“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第1章的《我一生中组幸福的时刻》回应着第83章的《幸福》,或者是最后的幸福在检视着最初的纯真,但是这从开始到最后的幸福轨迹里,依然是一个“如果”,如果知道这就是幸福,如果从换包开始芙颂没有眼泪,如果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做爱没有那只被忽视的耳环,如果订婚仪式上不被戳穿我的谎言,如果在芙颂结婚之后能能实现作为一个演员的梦想,如果最后的爱不掺杂更多的虚伪——如果都没有这些如果,那么从起初的幸福就会走向最后的幸福,那么凯末尔将不再是成为作者的帕慕克,就像在自己告别这个世界之前,满怀爱恋地亲吻芙颂的照片,然后放进自己的西服口袋,并在喜悦的微笑中说:“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
最后的幸福,是死亡前的幸福,回首而感慨,一生的时光凝聚成一个点,其实就是回到了纯真的时刻,经历者的凯末尔和假设者的帕慕克合二为一,两个男人一起看见的是芙颂那张照片,那时她穿着绣有9号字样的黑色泳装照,有着蜜色的胳膊、忧伤的脸和曼妙的身材,“即便在照片拍摄三十四年后,她那充满了人性的热情又多愁善感的面容依然令我们为之心动。”让人心动就是纯真,带着自己的身体,走向自己的理想,一个女人在被人带着惊讶、爱恋和敬意中,才成为纯真的象征。但是这个象征却像那个假设句一样,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对于现实来说,它代表的却是欲望、歧视和所谓阶层不同带来的观念禁锢。
这种观念的禁锢来自凯末尔的父母,作为他们的远方亲戚,芙颂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只是谱系上的差距,而是观念,“她的衣着过于开放。六个月里她从一个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女人,就像南瓜花那样开放了。如果她在短时间里不和一个正经男人结婚,她会被人议论,以后会不幸福的。”凯末尔的母亲就对芙颂当初参加选美比赛耿耿于怀,这种骨子里的鄙视不是来自于一个少女的开放,不是被人看见而激发的欲望,也不是出入那些场合的不正经,而是阶层之间先天的对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耳其,正处在观念的碰撞期,中西方的文化和宗教造成的冲突已经变成了一种烙印。凯末尔的父亲创建了伊斯坦布尔萨特沙特公司,所以他们一家代表着有钱的上层,他们穿的是最昂贵的裁缝丝绸·伊斯梅特那里定制的礼服,用餐在富人们最喜欢的欧式饭店之一的福阿耶,那幢象征着“仁慈”的迈哈迈特公寓楼就是二战期间倒卖食糖的老头盖起来的,而最后两个儿子把父亲扔进了救济院扣押了房子再售给了凯末尔的父亲。
所以他们对于他人的目光总是俯视,他们看不起那些穷人,甚至对于可怜女人的葬礼都抱着娱乐的方式,客厅和阳台正对着举行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所以当仪式举行的时候,站在阳台上的一家似乎在观看一场死亡的演出,“儿时在阳台上观看葬礼,是我们认识神秘死亡的一项有趣和不可或缺的游戏。”当那个贝尔琪丝的葬礼举行的时候,母亲在阳台上却在奚落死者:“可怜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贫穷,后是男人。很多,很多。”在他们看来,葬礼不是为了吸取死亡的教训,也不是对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而是为了观看乐趣和仪式情趣而举办的。凯末尔和茜贝尔恋爱,母亲认为茜贝尔在索邦念过书,就是对她身份的一种肯定,因为那时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只要说起在巴黎读书的女孩,也都会说“在索邦念的”,而当凯末尔因为芙颂最终解除了婚约,对于茜贝尔来说,绝对是一种在灾难,因为在别人看来,年轻女孩的“童贞”非常重要,是婚前必须保护好的珍贵宝藏,但是一旦被男方取消了婚约,那就是亵渎了规矩,破坏了礼制,就会在大家面前抬不起头,永远被鄙视的目光所淹没,而凯末尔的母亲却不无讽刺地认为是茜贝尔自身所酿的悲剧:“她是一个非常贪婪、非常骄傲、非常自负女孩。知道她不喜欢猫时,我开始怀疑了。”
而身为上流社会精英的凯末尔父亲,却有着一段难以启齿的感情,当初了相差27岁的女孩相恋,却始终没有勇气和她在一起,而在说起这段往事时,却告诉凯末尔:“因为我没有离开你母亲和你们门,她抛弃了我。”把责任推给了她,而自己却占领道德制高点。当最后听说她在癌症的折磨中孤独死去的时候,他却告诉凯末尔:“儿子,一定要懂得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及时地善待一个女人。”那副珍贵的耳环永远无法给她戴上,当他把它送给凯末尔的时候,还表现得像一个受害者:“她戴耳坠很漂亮。这对珍珠耳坠很珍贵。多年来我一直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
自私、虚伪,以及自上而下的俯视,这就是凯末尔父母所在阶层对待世界的态度,而对于在美国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凯末尔来说,似乎应该成为一种破旧革新的中坚力量,但是凯末尔似乎也像他的父母一样陷入在这样的“中产阶级”的陷阱里,在这里似乎只有自我,只有谎言,只有他人的错,当芙颂这个象征着纯真的女人出现的时候,这种观念的交错却把她带向了死亡。“改变我一生的那些事件和巧遇是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75年4月27日,我和茜贝尔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一只杰尼·科隆品牌包时开始的。”这是改变的时间和地点,而那只杰尼·科隆品牌的包无疑具有象征意义,他在香舍丽榭精品店里,价格是1500里拉,相当于一个年轻公务员半年的薪水。这是我送给茜贝尔的一件礼物,但是最后发现,这个代表身份的礼物竟然是假的,就像茜贝尔对凯末尔的评价一样:“亲爱的,你是个那么有知识、有文化、聪明的人,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女人们会如何骗你。”
正是去还包,曾经的远方穷亲戚芙颂出现在凯末尔眼前,一个是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是卖包的售货员,一个是三十岁有身份的男人,一个是十八岁无着落的女孩,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打破他们的界限而命名为“幸福”的话,那就是欲望,一种征服的欲望,一种占有的欲望,“触碰着她那细长、美丽的胳膊和身体,感觉着她的乳房,就这样突然拥抱她让我感觉眩晕。”虽然对于欲望感觉到一种恐惧,但是所谓的幸福又支配他去接近并且拥有这个身体,迈哈迈特公寓楼成为他们约会的场所,甚至变成了纯做爱的地方,但是这种做爱总是夹杂着从身份开始的鄙视,凯末尔从母亲对她参加选美比赛的歧视中认为芙颂就是一个满足男人欲望的工具,他认为芙颂不可能是处女,甚至嫉妒地觉得,之前她一定在别的床上、沙发上,或者汽车的座椅上,“也这样看过别的男人。”
而在公寓楼里的相恋的一个半月差两天时间里,他们做爱44次,而这种数字将欲望放大,甚至纯粹变成了一种身体上的满足,而凯末尔面对芙颂,他依然以俯视的方式占领制高点,“如果我们把男人最明显的性器官放在一边的话,其实最让芙颂感兴趣的东西,既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广义上的‘男人的身体’。她真正的好奇和兴奋是针对她自己的,是她自己的身体和快感。”芙颂是为了自己得到满足,所以这不是占有,不是征服,而是双方共同的满足。但是对于已经和茜贝尔好上了的凯末尔来说,这样一种欲望的满足带来的是某种不安,当芙颂问他是不是也和茜贝尔做爱的时候,凯末尔的回答却是:“没有。”那些和茜贝尔在办公室沙发上的做爱经历被他一笔勾销,自私而说谎,却在凯末尔那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它表示茜贝尔有多爱我,多信任我。但是婚前做爱的想法依然让她感到不安……对此我也理解。”甚至他还为芙颂的行为找到了另一种解释:“但却没有你那么勇敢和现代……”——芙颂因为“勇气和现代”和我做爱,所以我将不会对她产生一种特别的责任和依赖感。”
一种逃避,却为自己寻找借口,而当这种欲望成为芙颂的爱,当她说出“我爱上你了。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你了”的时候,在凯末尔看来,更是变成了博弈中的输家,“是她先表白的。因为我是在芙颂之后说的,所以我那真实的爱情表白里渗透着一种安慰、礼貌和模仿。”当芙颂在做爱时掉下了耳环,当她说出“我的整个人生和你的连在了一起”,在凯末尔看来,仅仅是为自己寻找到了躲避的理由,因为芙颂这样做,在道德上先入为主就已经输了。所以在和茜贝尔订婚仪式上,凯末尔还是那么肆无忌惮,还是为自己寻找借口,还是期待着在道德之外满足欲望,但是订婚仪式上,芙颂终于知道了凯末尔和茜贝尔做爱的现实,这一种现实把她置于了被玩弄者的角色中,她不是订婚后的妻子,她是情人,却也是不是和爱人连在一起的女人,所以芙颂在这个夜晚之后消失了。
对于凯末尔来说,其实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只有在芙颂的肉体中才能获得欲望的满足,却已经和茜贝尔订婚,必须承担世俗的压力,但是最后在“等待的痛苦”中凯末尔选择了解除婚约,这对茜贝尔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而凯末尔却找不到芙颂,对他来说,只能在公寓里躺在床上寻找芙颂的味道,智能在伊斯坦布尔的地图上标注芙颂去过的地方,只能在收集芙颂相关的物品中回忆那一段香艳时光。但是,芙颂还是出现了,当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那对耳环去找芙颂的时候,她却告诉我,她已经和费利敦结婚。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凯末尔第一反应是自己被人嘲笑,被人鄙视了,而丝毫没有顾忌被爱欺骗的芙颂那些日子经历了什么。
凯末尔悔婚,芙颂结婚,他们似乎被婚姻隔开了距离,但是凯末尔却以拍电影的理由出入芙颂的家里,而其实,电影又成为两个人联系的纽带,对于芙颂来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成为演员,在“艺术电影”里演绎自己的人生。而凯末尔无论如何都含着功利目地,甚至芙颂的丈夫也以写剧本为理由,在声色世界里堕落。一边是理想主义的芙颂,一边是功利主义的凯末尔,其实两人之间的分歧就是土耳其现实中的隔阂,西方的文化对于当时的土耳其来说,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并没有带来自由和民主,甚至最后都变成了禁锢,剧本必须审查,身份必须核实,而这样一种被隔阂的现状无疑在摧残那种纯真的本性,摧毁理想主义和“艺术电影”。
他们的婚姻和爱情也一样,芙颂的丈夫费利敦在拍摄电影时和女人帕帕特亚混在一起,最后芙颂提出了离婚,而当芙颂终于回到了凯末尔的怀抱,当她期盼着自己回到纯真世界,凯末尔的想法却是:“一切都很好。我将要和芙颂结婚。我会带着她重新回到上流社会……当然,如果我能原谅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什么是上流社会?是在阳台上像游戏一样观看一场葬礼?还是把堕落强加给一个女人身上并成为解除婚约的理由?是把珍贵的耳环仅仅当成是纪念物而牺牲那段被世俗鄙视的感情?或者是带着芙颂以得体的方式去往欧洲?但是多有种种都渗透着欲望,权力的欲望,金钱的欲望,地位的欲望,甚至身体的欲望,而芙颂,一个跌入到爱欲世界,又陷入到婚姻世界里的女人,却保持着最后的理想,在她看来,就宛如自己还是处女,“在我的整个婚姻期间,我和费利敦之间没发生过夫妻关系。你必须相信这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处女。此生我也只会和你在一起。”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自我救赎,在这个物欲世界里,在这个谎言编织的故事里,她似乎从来没有破坏那种纯真,而将她推向世俗,甚至是反道德境地的是那些自私的人,那些充满谎言的制度,那些满足身体的欲望,“人生也就像爱情一样”,人生也像那部电影,在被放映之前,有过多少的欺骗,有过多少的虚伪,有过多少的妥协,所以当凯末尔和芙颂正走向她理想主义的最后终点时,芙颂却突然说,不去欧洲了,“他问了我的整个一生。他甚至还问我为什么离婚了。他还问,如果我没有工作又离了婚,那么我靠什么来生存。”审查无处不在,而所有的审查都站在一个基本原点,那就是面前的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而这种预设对于芙颂来说,就是整个纯真爱情走向失落的原因,公寓里的一个半月差两天,或者是最接近纯真世界的,做爱44次却已经掏空了她,所以当最后凯末尔要和她结婚带它走向上流社会的时候,芙颂选择了自杀。
“她在用105公里的时速,把车子交付给一棵105年树龄的枫树。我明白这是我们人生的终点。”这是死亡的速度,却是美丽的瞬间,一种死对于芙颂来说,却也是纯真的最后表白,“除了胸骨上的骨折和额头上的玻璃划伤,她美丽的身体,忧郁的眼睛,美妙的嘴唇,粉色的大舌头,天鹅绒般的脸颊,健康的肩膀,乳房,颈部,肚子上丝绸般的肌肤,修长的双腿;每次看见都会让我发笑的双脚,蜜色、修长的胳膊,丝绸般肌肤上面的黑痣,棕色的汗毛,圆润的臀部以及我任何时候都想在她身边的灵魂,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芙颂没有被破坏的肉体保持着纯真,而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用牺牲的方式保留了内心的纯真,就像年幼的时候在宰牲节上听到的那个先知易卜拉欣的故事,为了证明自己信奉真主,先知可以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儿子,而且不求回报,“牺牲意味着,为了真主,我们可以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芙颂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献出自己,自己的纯真,自己的爱,自己的所有。
而芙颂的死,无疑对于凯末尔来说,是一种警醒,当他终于发现曾经做爱时再也找不到的耳环竟然是芙颂藏起来了,“她说过,到巴黎后要戴上一对耳坠让你惊喜的,但我不知道是哪对耳坠。我亲爱的芙颂是很想去巴黎的。”一对耳环,是身体和身体交融的象征,是理想和理想汇合的符号,是爱与爱不分离的见证,而芙颂用谎言还击了凯末尔的谎言,只是被藏起来的意义就是最后对于纯真的守护,就像结婚而仍然是处女一样,就像死亡而保持完整的身体一样,只有纯真的东西才是不被破坏的,才是永恒的。
凯末尔踏上了建造纯真博物馆之路,可以说是他最后的醒悟,十五年走遍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8年保存了4213个烟头,那些梳子,那些小狗玩具,那些钟表,那些内裤,所有的一切都试图还原一个人,还原一种感情,同时也向人们展示纯真的意义,“看着物品,用敬畏和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芙颂和凯末尔之间爱情的参观者,也将明白,我们的故事和雷拉和麦基农·侯颂和阿什克一样,不仅是情侣们的故事,也是整个世界,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故事。”而对于这个纯真博物馆来说,抽离那个自私、虚伪的凯末尔,或许也是一种最彻底的办法:从最初的相识开始,从最真的相拥开始,凯末尔变成了奥尔罕,没有经历公寓楼里做爱时的谎言,没有那漫长八年的等待,没有为了返回上流社会的婚姻,甚至没有那只香舍丽榭精品店里的假包,一切都只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走到了上面的酒吧,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前面的树下接吻,我们结婚了!”